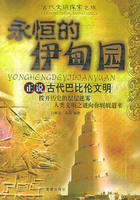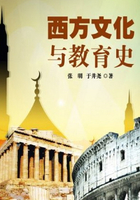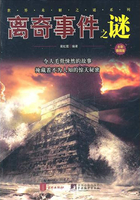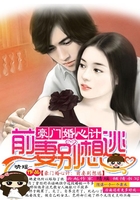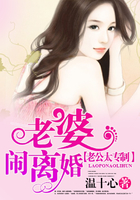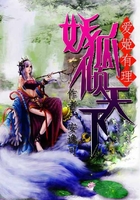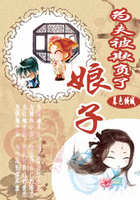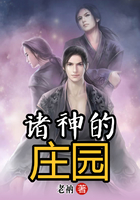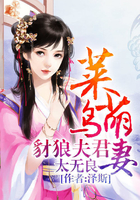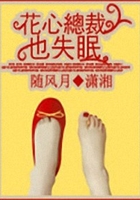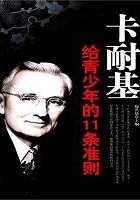在秦一统六国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我国古老的自然科学和文化艺术一直在稳步发展。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领先水平。《诗经》、《楚辞》是我国文学艺术的瑰宝。而在音乐、雕刻等领域更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天文历法
我国传世的第一部历法是相传出于夏代的《夏小正》,它记录了一年12个月中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人们在该月中所应从事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因此,它可以说是一部自然历的历法。孔子说:“行夏之时。”春秋鲁国天文学家梓慎称赞“夏数得天”,说明春秋时仍是应用夏代的历法。人们至今把农历也称为夏历,显然是有原因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当时在房宿位置发生了日食,人们不了解原因,以为灾祸,所以击鼓奔走。夏代已有天干记日的方法,夏代后期的几个帝王名孔甲、胤甲、履癸(夏桀)就是证明。天干是十进位制的,这时已有了十天为一旬的概念。
从殷墟卜辞看,商人已习于立表测影,用以定方向,定季节。他们对日月的观测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卜辞中有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有日期(干支)的文字记录;他们已能用预卜的方式大致测定日食;已初步有了“日月交食”的观念;二十八宿的“火”、“心”、“尾”、“毕”,其名已见于卜辞;人们把二十八宿按4个方位分为4组,即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四象”。“四象”在卜辞中已见其二,可见“四象”的建立可能远在殷商以前。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说七日这一天的晚上,天空中有一颗新星接近大火(心宿二),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记录。商人开始使用干支纪日,把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与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配合,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用它来记日,六十日一个循环。月有大小,小月29日,大月30或31日;年有平闰,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表明商人采用“阴阳合历”。武丁时期,大量采用“年终置闰”,也有“年中置闰”;祖庚、祖甲之后,“年中置闰”成为主要方法。这种阴阳合历在我国一直沿用了几千年,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历法制度体系。
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很多的月相记录,名称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是对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盈亏变化的描述,表明西周时人们对月亮盈亏变化的规律性有了一定的认识。西周已用十二地支来计时,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且,至少在西周已有了漏壶这一计时工具。还用圭表测影,确定冬至和夏至等节气。《诗·小雅·十月之交》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是我国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朔日”的记载,也是我国古籍中有明确日期记载的日食的最早记录,据推算应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可见西周时我国的历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春秋时期,我国已能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精确测定冬至时刻,较准确地推求回归年长度。《左传》中有两次冬至时刻(当时叫日南至)的记录。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前655年),一次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这是我国观测冬至时刻的最早记录。春秋中期以后,推定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一个朔望月为29.53085日,19个回归年正好为235个朔望月。于是发明了19年插入7个闰月的方法。《左传》记载的133年中设置了49个闰月就是证明。战国时期,是我国历法的确立时期。各诸侯国实行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6种历法,史称“古六历”。“古六历”都是“四分历”,只是所规定的历法起算年份(历元)和每年开始的月份(岁首)有所不同;其中《颛顼历》的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360年左右,岁实(回归年)为36.25日,闰法为19年7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而闰月放在九月之后。从《睡虎地秦简》可知,秦国至少从秦昭王在位时(前306~前251年)起就已采用《颛顼历》。
为了更精确地反映季节的变化,古人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即把一年平均分为24等分,平均过15天多设置一个节气,它反映了太阳一年内在黄道上运动的24个特定位置。记载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的较早的文献有《逸周书》的《周月》和《时训》、《淮南子·天文训》。比较之下,《逸周书·时训》的记载当早于《淮南子·天文训)。《逸周书·时训》最晚也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此,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有可能会早到春秋时期,最迟也当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只不过早期的二十四节气,雨水原在启蛰(惊蛰)后,后来才被改到惊蛰前。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世界上实行阴阳合历的国家不少,但只有我国创立了二十四节气。
在天象观测方面,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珍贵记录。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242年中,仅《春秋》一书就记录了37次日食。这37次日食记录,至少有31次是确定无疑的。《春秋》一书的记录是在当时条件下相当完整的大食分的观测记录。例如,鲁昭公在位32年,曲阜可见的日食,《春秋》基本上全有记载。《春秋》还有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有最早的陨石记录,有最早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的观测则更为精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29幅图,画着各种形状的彗星。彗尾有宽窄、长短、直弯各种不同的形态,彗尾的条数多有少;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有的圆圈的中心又有一个圆圈或小圆点,可见人们已认识到彗发和彗核两个部分,而且也有不同的类型它们当出自战国时楚人之手,可称为世界上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著作。
在行星和恒星的观测上,战国时期的成就尤为惊人。在当时的天象观测家中,影响最大的是甘德和石申夫两家。甘德,又称甘公,约生活于公元前360年时,当为楚人,著有《天文星占》8卷。石申夫,又作石申,魏国的司星,约在惠施为魏相时著《天文》8卷。他们的原著虽早已遗失,但从《史记》、《汉书》和《开元占经》等书的称引中,还能了解其大致内容。
甘德、石申夫发现了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简明、形象地把行星逆行弧线描绘成“已”字。从《开元占经》的引文可知,甘、石测得水星的会合周期为126日,现今测定值为115.8日;他们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为620日和732日,现今测定值为583.92日;甘氏测定木星的会合周期为400日,现今测定值为398.88日。他们测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现今测定值为1.88年;木星的周期为12年,现今测定值为11.86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运行的观测记录。它所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土星的会合周期是377日,现今测定值为375.91日;木星的会合周期为395.44日。《甘石星经》的测算,以“度”为基本单位,度以下的奇零用“半”、“太”、“少”、“强”、“弱”来表示,而《五星占》已采用一度等于240分的进位制度。这说明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人们对行星的观测推算,已经日趋精密。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初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箱,箱盖上绘有青龙白虎,中间书写一个斗字,围绕斗字的28个字正是二十八宿的名称。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包含完整的二十八宿的最早文字记载。这种描绘在日常生活用具上的图案表明,早在战国初年,四象和二十八宿相配已成为常识。所以,在我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应该可以上推到春秋时期。除二十八宿体系外,还指明了各星宫的星数以及相邻星宫之间的相对位置。据《开元占经》所引,甘、石以及巫咸三家均有中、外宫(星座)的划分法,甘德、石申夫在战国中期(约前360年)精密地记录了120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入宿度和去极度)。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甘德测定恒星118座,计511颗星;石申夫测定恒星138座,计810颗星。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将甘德、石申夫、巫咸三家所著星经综合在一起,编成一张包括283个星座、1464颗恒星的星表,并绘成星图,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
古代数学
商代的陶文和卜辞中都有不少的记数文字。甲骨卜辞中一、二、三、四等数字多用横画,陶文中则用竖写。商人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13个自然数记10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十、百、千、万的倍数在甲骨文中用合文书写。现已发现的甲骨文中的最大数字是3万,复位数已记到4位,如2656。商人记数常在百位与十位、十位与个位之间加一个“又”字,如五十六写作“五十又六”。西周记数法和商代相同,只是有些字形不同而已。商和西周的记数法是遵循十进制的,含有明显的位值制意义,只要把千、百、十和“又”的字样去掉,便与位值记数法基本一致。与古罗马、古埃及的记数法比较,这一记数法更先进、更科学。还有一些卜辞反映出商代已有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初步的运算技能。
万以上的大数计数,这时已经出现,进位制有十进和万进两种。《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亥极。”这里的万、亿、兆、经、亥都从十进。《管子·海王》说:“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口开千万也。”则从万进。
四则运算方法春秋时已趋于完备。古代的乘法口诀,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至“二二如四”止,共36句。因开头两字是“九九”,故“九九”作乘法口诀的简称。《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时人们就已认为“九九”是不足为奇的“薄能”,说明当时乘除运算已开始流传。《左传》又记载,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晋国有人问某老人的年龄,老人不直接回答,只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问者不懂,去问诸卿大夫。师旷说,这老人“七十三年矣”。史赵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说,“然则二万六千六百七六旬也”。此老人和师旷、史赵、士文伯显然都能熟练地进行乘除法的运算。战国初年李悝《法经》中有关于一个“农夫”一家五口的收支情况的计算,其中已讲到了减法、乘法和除法,还出现了“不足”之数,为“负数”概念的出现提供了来源。
筹算是我国独特的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一种计算方法。它的产生应在春秋战国以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臻于成熟。《老子》第二十七章说:“善算,不用筹策。”可见春秋晚期筹算已经相当普遍。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中,不但有算筹的实物,而且还有算筹记写的数目。算筹记数用极简单的竹筹纵横布置,就可完全实现十进位值制记数法,能够表示出任何自然数。我国古代数学在数字计算方面的卓越成就,当归功于遵守位值制的算筹记数法。
分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常被使用。如古四分历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都不是整日数,其奇零部分是用分数表示的。《考工记》不但大量使用了分数,而且有了分数运算。《管子·地员》篇提出了“三分损益法”的乐律计算法,说明当时已有了指数的初步概念。
《周髀算经》卷上记载周公与商高的一段谈话,商高说:“故折矩以为句(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这是说至迟到西周初年人们已有了“勾三股四径(弦)五”这个勾股定理的特例的知识。《周髀算经》卷上还记载了荣方和陈子的对话,陈子说:“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这是明确的勾平方加股平方等于弦平方的表述。陈子为春秋陈宣公时公族,为公元前7世纪中叶人。因此,我国发现勾股弦定理至少比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前560~前500年)早一个世纪。《考工记》一书则具体应用了勾股弦定理。它说:“冶氏为杀矢,……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酹。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酹”;这是说如果三角形的三边的比例是2:3:4,那么4的对角大于90度,故称“倨句外博”;如果三边的比例是3:4:5,那么5的对角等于90度,故称“倨句中矩”。
《墨经》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最晚可能到战国后期。它们记载了墨家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问题的论述,对“平”、“同长”、“中(中心点)”、“厚(体积)”、“直(直线)”、“圜(圆形)”、“方(方形)”、“倍(倍数)”等概念作了定义说明,可以说是理论几何学的萌芽。
古代医学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传说神农曾教民尝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汤液是中医用水煎煮药物为人治病的一种水药剂型,传说是商代的右相伊尹发明的。《吕氏春秋》记载伊尹与商王的对话中曾以医为喻,说:“用其新,去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可见伊尹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孟子·滕文公上》引《书》曰:“‘若药不瞑眩,阙疾不疗’。”说药物如果服用后不使人昏晕,就不可能治好疾病。可见商人用药物治疗已很有经验了。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曾发现植物种子30多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这两种果仁都有润燥、通便、化淤血的功效。这一遗址中还发现一漆盒内放有一件石质镰形工具,医史专家认为是医疗器具砭镰。砭镰是砭石中形似石镰的一种,利用其锋利的刃口可切割痈肿、排除脓血,也可以用它来刺激体表某些部位,以解除疾病痛苦。商代出土的小件青铜器中,针锥不少,有的可能是针灸工具。
殷墟出土的卜辞与医学有关的约300多片,400多辞。内容主要记录王室成员的疾病情况,涉及30多种病名,如疾首、疾天(头顶)、疾目、疾耳、疾自(鼻)、疾口、疾舌、疾言、疾齿、疾身、疾臀、疾趾、疾骨、疾心、疾旋、疾软、祸风、疾疫、蛊、虐、疾蛔、小儿病等等。卜辞里殷人对付疾病的主要手段是祭祀祈祷,但也对疾病进行各种治疗,甚至还能测定预产期。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巫咸和巫彭等十巫,由于他们可以和“大荒山”上的神灵相通,所以“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又说巫彭等“皆操不死之药”。《世本》说“巫咸作医”。巫咸和巫彭之名屡见于卜辞,可能是真事其人。古时巫医不分,一些神巫也掌握了一定的药物知识和一定的治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