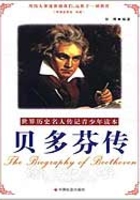宋朝的官员迁转频率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王安石于1057年七月到常州任职,1058年二月就调任新职,在常州只干了八个月左右,由于任期的短暂,致使王安石开凿运河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王安石心有不甘,亦不想半途而废,但他也无能为力。为此他亲笔给参知政事曾公亮写了一封信,请求能在常州任满一届,但没有获得批准。所以就在嘉祐三年四月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常州。
王安石不愿意离开常州是有众多原因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年老多病的母亲。提点刑狱需要他长时间在外奔波,居无定所,他自己对此倒是无所谓,但是却苦了他的老母亲。此时母亲正需要王安石在身边照顾,王安石是个有名的孝子,他实在不愿意看见母亲在风烛残年之际还孤单一人。
但是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王安石深知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又风尘仆仆地就任新职了。据《长编》载,1058年二月,“诏新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沈康知常州,知常州王安石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巧的是,这里所提到的沈康,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跟陈执中要官的沈康,此时他的职位正好和王安石互换了一下。这个沈康,由于他的能言善辩和善于钻营,他升官的速度比王安石还快,在江南东路刑狱任上时,此人断案愚蠢,欺上瞒下,声名狼藉,谏官陈旭直接上书,请求朝廷将沈康与王安石对调。
提点刑狱这个官职,说的直白一点,已经是一路(宋时将全国分为若干路)比较重要的领导人了。凡涉及鸡鸣狗盗,坑蒙劫掠等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都归提点刑狱所管辖。此外还要监察部下官吏,勤政为民的官员,还要负责向朝廷推荐,职权算是相当大了。提点刑狱往往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要在属下各州县四处巡视,看到哪里有冤案错案,立马处理,若碰见有贪赃枉法的官员,提点刑狱也可以将其革职查办。
任命王安石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并不是因为王安石的文采,而是王安石早有明断慎查的名声。早在鄞县任职时,王安石办案就小有名气。他从来都是秉公执法,严格按照大宋律法办事。由于他的严谨固执,有时还有点钻牛角尖之嫌。然而,他的逻辑思维比较强,对律法也非常的熟悉,因此办案的时候,总能让案件水落石出。邻县县令有难案无解的,往往会请王安石帮忙决断。余姚县就有一个疑难案件经过县、州、转运使三级审理,都难以决断,当时的提点刑狱特意请王安石前往裁定,王安石毫不费力,裁决一出,上下皆服其精妙,因此王安石更是名声大振。
古时断案,有一个原则,叫《春秋》决狱,意思就是有什么案子拿不准的,可以把孔子的《春秋》拿过来仔细研读,或者根据董仲舒依《春秋》作出的判例,进行一定的比对,依此来对案件进行宣判。至于法律文书,倒是排到了第二位。这种做法虽然到唐朝就已结束,但宋朝的法律基本上已经做到了“礼法合一”,所以,宋朝仍然受到了春秋决狱的影响,对同一个案子的断决,不同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水平,往往会给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判决。
王安石断过的好几个案子,都曾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有的直接惊动了朝廷,其中尤以后来的登州阿云案最为有名,说起这个案子,其实也与司马光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光年轻时“砸缸救人”的故事妇孺皆知,但他用“礼教杀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清朝著名学者沈家本在其名著《历代刑法考》中重点记录了中国古代法理学的重要案例“登州阿云案”。公元1068年,登州妇女阿云因不满未婚夫相貌丑陋,就趁未婚夫在田里休息时,用剪刀连捅未婚夫三十多刀,但未婚夫未死。事后,阿云向官府自首。案情并不复杂,但却因党争的关系,层层上报,最后这么一个普通民女的刑事案件竟然要当朝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亲自参与审理,要当朝皇帝宋神宗亲自加以裁决。改革派王安石等人认为阿云谋杀未遂,又有自首情节,应判30年以上有期徒刑。保守派司马光等人忽视客观案情,匪夷所思的将阿云这个平民女子的生死同国家社稷的存亡联系起来,认为如果不杀阿云,“夫为妻纲”的天道伦常就要崩溃,而伦常的崩溃将直接导致国家的混乱和灭亡。宋神宗最后支持了王安石一派,亲自判决阿云37年有期徒刑。不过,这事还没完,16年后,宋神宗去世,哲宗年幼,高太后启用司马光总理朝政。没想到,多年来司马光竟一直对“阿云案”耿耿于怀,上台后,立刻翻案,将阿云以“大逆”的罪名处死。司马光这么做完全就是挟怨报复,草菅人命。而且,此恶例一开,以后历代,只要是妻子谋杀丈夫,不论动机什么,成功与否,有无自首情节,都几乎必死;相反,丈夫谋杀妻子,则往往被从轻发落(如明大画家徐渭杀了妻子,只被判刑七年)。毫无疑问,阿云和其他数不清的女性便因为司马光的顽固和蛮横,成为了所谓礼教的无辜牺牲品,而此时的司马光也由一个“砸缸救人”的小英雄,蜕变为一个用“礼教杀人”的“魔头”。
令人尤为沉痛的是,司马光的名言虽然为“开卷有益”,但司马光的行为却与这句话南辕北辙。司马光在没有读书前,尚且知道变通,知道应该把缸砸坏,人命更为重要;但他在饱读史书典籍后,却变得如此顽固不化,为了自己一个非常片面的看法,竟一定要将一个柔弱女子置于死地。他似乎就是“开卷吃人”的一个典型。
再者,司马光虽然饱读史书并编著《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成就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他本人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却奉行“亲小人,远君子”的原则。他上台后,立刻重用变节投靠他的蔡京,而疏远此前一直支持他的苏轼。“蔡京、苏轼”谁是小人,谁是君子,饱读史书,深谙事故的司马光,不可能分辨不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此此时他需要的只是卑鄙下流的政治打手,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仁人君子。司马光竟然为了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启用奸佞,疏远贤臣。蔡京这个“六贼”之首,直接导致后来的北宋亡国和“靖康之难”的大奸臣,最早竟发迹于司马光这个以严谨闻名的史学家之手。从这个角度上说,动不动就拿国家社稷压人的司马光,实际上却是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其判决争议一直持续千年,中国的近代法学启蒙人清朝的沈家本也插手其中,可见其影响之远。但王安石所判的这些案子,如果以现代法律思想来裁决的话,可以说,他的裁决是完全正确的。平心而论,在当时,很少能有人像王安石那样,在鸿博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下,还兼有严谨的法家思想,所以,王安石断案,应该说是有理有据,入情入性,情理兼一。
宋时江南属富庶之地,经济发达,人情也较为复杂。王安石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些比较难断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斗鹑案。
因为风气使然,所以,在当时的城市里极其盛行斗鹑。玩得起这些东西的也多是一些纨绔子弟。如果有谁拿着一只上好的斗鹑从街上走,那应当是一件相当抢眼的事情。
一天,有个富家子弟,弄到了一只绝好的斗鹑,于是整天提着自己的斗鹑在街上到处乱晃,见人就说:“此乃上好之斗鹑!”此时正好被他的一个好朋友撞见了,要求他把这只斗鹑卖给自己。这个富家子弟对这只斗鹑视如珍宝,说什么也不肯给他,他的好朋友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拿跑了。这个富家子弟十分生气,拿着一把刀就追到了门外,两个人一时起了口角,由于年少气盛,这个富家子弟当街就把他的这位好朋友给杀死了。
此事发生以后,当地的官府判这个富家子弟故意杀人,依律,杀人偿命,应该斩首示众。被斩之家当然不愿意,就上诉,正好王安石巡回视察,拿到了这个案子。王安石仔细分析了案情,又了解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对案子进行了改判。
王安石认为,抢斗鶉之人不经富家子弟的同意,强行拿走别人的东西,“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他的行为已经构成“盗”,而根据律法,“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把富家子弟定名为“捕盗”,依律不应该判死刑。不但如此,王安石还弹劾该案主审官犯“失入罪”,也就是说把无罪错判有罪,或轻罪错判为重罪,需要处分。
王安石的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常人都认为二人平时是好朋友,这件事的行为只能算是开玩笑过了头,不能算是“盗”,因此主审官也不服,案子遂闹到了开封大理寺,大理寺最后判定以主审官所判为准。这个大理寺的官员就是少有神童之名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他认定王安石判决有误,要求改回原判,富家子弟的罪名仍为杀人,应将处斩,并且责令王安石写书面检查。要求他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是例行公事,但王安石却拒不认错,声辩到:“我本无罪,故不当谢罪。”于是韩晋卿便指责王安石改判和弹劾官员错误,上书朝廷,说王安石应该受到降级处份,并要求以朝廷名义责令王安石进行检讨。
仁宗作为一国之君本来事情就多,再加上立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仁宗也没心思管这些事,就下诏免了王安石的罪。皇帝免罪,官员理应上表谢恩,但王安石却拒不上表谢恩,他对其他官员说:“我本来就没错,为什么要谢恩?”估计在宋朝,拒不上表谢恩的,也就只有王安石一人了吧。
此事最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王安石在江南路的日子过的并不得意,由于不是主官,他自己又不愿意和当地的官僚同流合污,所以关系处得并不融洽。由此很多人对王安石产生了一些误解,认为王安石做事刚愎自用,听不见意见。这一说法传到了曾巩耳朵里,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劝王安石要随俗一些,莫不可太过于独断专行,否则很不利于仕途的发展。王安石看后立即回信道:
江东得毁于流俗之士,吾心不为之变。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而不能合流俗也。
倔强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王安石在提点刑狱任上做得尽心尽责,并且不为流俗所动,但王安石本人对这一工作很不感兴趣,所以,在给好朋友王令的信中,就曾提到他一直在请朝廷调往他地任职。
曾巩曾写信给王安石,劝他先把工作干好再说,不要坚持调动,只有王令支持王安石,让他一再上书请调,“要得郡而后止耳”。就是说,王令鼓励王安石,应该向朝廷申请一个地方长官的官职,而不要在乎官位高下。这不但因为王令和王安石之间确实情谊非同一般,而且王令也十分了解王安石。对同一个问题,他们常常能够不谋而合,达成共识。
说起这个王令,他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而且比王安石小了十一岁,但王安石与王令自相识以后,便书信往来,无话不说,两人的诗书唱和,使得王令的文学和政治见解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并得以流传后世。王安石并且亲自做媒,把妻妹嫁给了王令。
王令对时政的看法有时甚至比王安石还要激进,他自己终生不仕,并且还力劝王安石也退隐山林,如他的《寄介甫》一诗:明确提醒王安石,“天下滔滔昔已非”,也就是说任何改革都已不可能挽救大宋的命运了,王安石纵然有心济世,但无力回天。
王令此诗被后人誉为“识度之远,又过荆公”,当然,可能言过其实。但王安石与王令在性格上却迥然不同,王令选择逃避,王安石则是选择迎激流而上,要击水三千。
所以,王安石在给王令的回信中说:我王安石治学,一是为自己,二是为天下,现在我自己的生活已趋于稳定,现在就要找机会为天下百姓做点事情,至于我能否有机会,则“系吾得志与否耳”。如果我有机会而不去做,则“吾耻之也”;而如果我想去做而没有机会,“吾不恤也,尽吾性而已”。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王安石的为官之道,对于官位,王安石并不强求,只愿能为百姓做事,所以,王安石对一些不能做实事的无聊官位的一辞再辞,是有其深刻的心理渊源的。
王安石是个出了名的倔脾气,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便会排除万难,义无反顾,也因为他的刚正不阿,很多有求于他的人都不敢直接找王安石,便去找王令做中间人。王令烦不胜烦,在自家门上贴了一个字条:“来则令我烦,去则我不思”。再也没人好意思上门求王令引见王安石了。
可惜的是,王令身体一直不好,1059年便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不到三十岁。王安石对王令的英年早逝感到非常痛惜,不但亲自为王令写墓志铭,而且在王令死后一再写诗怀念他,前后计有十多首,即使在退休江宁以后,也没忘了给王令的遗腹女找个好婆家。
王安石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只干了半年左右,朝廷又一次下达政令,要求王安石于嘉祐三年十月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在离开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所饶州时,王安石写下一首《旅思》,其中有两句:
看云心共远,步月影同孤。
在这两句意境幽远、对仗工整漂亮的诗句下,掩藏着王安石一颗孤独而坚毅的心。
接到入京这一消息,王安石喜忧各半,喜得是他可以离开江南东路,不再做这个无聊的提点刑狱了;忧的是,他又得进京,做终日无所事事的京官了。为此,他给富弼写了一封信,要求“裁赐一小州,处幽闲之区,寂寞之滨,其于治民,非敢谓有能也,庶几地闲事少,夙夜尽心力,易以塞责而免于官谤也”。
三司是国家财政总理单位,度支判官是财政部门的官员,尽管王安石一直想在外做官,但王安石明白身处京师,能够对天下利弊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进而探明国家的困弊所在。所以,王安石虽然仍想到外郡任职,却也没有推辞此一任命。
纵观王安石前期为官的历程,此时的他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似乎一直都是充当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尽管他胸怀天下,满腔热忱,却始终未遇到一个真正的伯乐,来给王安石提供一个施展抱负的空间,以至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但王安石依旧在等待,他相信终究有一天他会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此时他的境遇不正和当年姜太公的境遇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