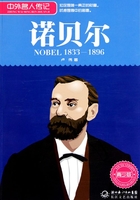§§§第一节荆公与司马光
荆公与司马光都应该算是神宗朝一代名臣。当变法进行得轰轰烈烈之时,司马光看到韩琦的上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心情异常悲愤,自叹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颓然之心昭然可知。但是司马光却不甘心,为了能彻底推翻王安石变法,终日奔走于满朝上下。他知道他只有挺起胸膛,鼓起满腔勇气,他还要继续战斗。而司马光战斗的方式,就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当时的职务是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差知审官院。听着职位虽然很多,但却没有什么实权。而久任官场,官却低于王安石,司马光多少有点不平衡,而且加之对变法的反对,两人很早就分道扬镳了。
荆公与司马光因为政见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在对新法的态度上,两人更是视对方为劲敌,颇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一心梦想着富国强兵的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与安石走的越近,忽视司马光也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他是一个彻底的新法反对者。无论如何,司马光也受不了这口气。他虽然已经借神宗的口气训斥过王安石,勒令王安石“祗复官常,无用辞费”!虽然当时讲得很好。但那也就是说说而已,神宗亲自向王安石道歉以后,反而把他搞的里外不是人,最可气的是,好不容易做到一枢密副使,但还没当几天,就又被罢免了。
司马光坐在书桌边,理了理胡子,秉笔直书,写了一篇《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陈述变法的种种弊端,请求神宗尽罢新法,撤除条例司,收回常平使。
神宗没有理司马光的奏疏,但有一天,神宗找了个机会,要和司马光谈谈。为了能顺利推行新法,神宗下了决心要为变法的道路扫清障碍。于是直问司马光:“朝廷每当变更一事,举朝士大夫吵吵嚷嚷的皆以为不可”,这倒罢了,但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有哪些不便,又不能指出来,这算是什么事啊,就这样讲来讲去的,我看不好!
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神宗非常不满,说:“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堂辩论,如果真的不能实行,就按不能的原因来处理。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们不上奏呢?如果先前上奏了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此法有何不便?到底哪里有问题?请你清楚地告诉我!”
司马光道:“我已经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里写清楚了。”
神宗说:“可似懂非懂。”
吕惠卿在一边接了一句:“司马大人天天讲话,但没有几句是有用的,我看司马大人不如辞职算了。”
无奈,司马光知道自己理论不过神宗,只好无可奈何地踱步回到家里。费尽心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这就是后来的《与王介甫书》。在文中,司马光把自己所有对新法的看法全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语言之犀利不觉让人略感丝丝寒意。最为对司马光的回答,王安石立刻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的《答司马谏议书》,句句中肯,强调自己变法的目的。
熙宁三年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开谕苦切,书信来回往复了三次。
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司马光采取的措施是和王安石谈往事,套家常,大讲昔日友情,希望王安石能听他一句话,不要变法。
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司马光先是感叹道:“我没有什么大事,不敢亲自登门造访,很久没有和安石兄在一起聊聊了。我没有什么本事,不敢说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们也在一起共事了十有余年,而且常在一起共事,关系也还是不错的。既然如此,我就想和你讲几句直话。
“你我都算是君子,‘君子之道,出处语默’,不能只说好话,但我们的志向是相同的,都准备‘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所以我们议论朝廷事,虽然意见不一,很多次我们的意见都大相径庭,但都还没有撕破脸。
“不论王安石你是否相信,其实我对你一直是非常佩服的。介甫你独自担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识的,都说介甫你不起则已,起则天下可立刻太平,人民都能感受到你的恩泽。”
司马光继续调理王安石,说:“陛下知道你的名声,他也很佩服你,所以硬是把你推上了前台。但是王安石你刚干了一年,却吃力不讨好,朝廷里的群臣及四面八方的人,都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人们把所有的失败都归罪于你。不知安石你听到过没有,是不是考虑过其中的原因呢?”
司马光对王安石说:“既然问题很大,怨言很多,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一声呢?因为你手下的人,不敢跟你讲;不是你手下的人,又不愿跟你讲,他们都怕得罪你,所以都坐而待之,等着你不过二三年将自败。这都不是对你王老弟好,也不是对朝廷好。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讲,任你推而行之,不出两三年,国事就会被糟蹋得不可救药了。
“现在看在你我友情的份子上,不怕你对我怨恨,想跟你啰嗦几句,为你一一解答其中的缘由。”
接着,司马光开始细细对王安石,说:“今天下之人,讨厌你的人非常多,他们对你的诋毁无所不至。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安石你了,你本身是很有才情的,你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你操心太过于细碎,自信太过于实际。
司马光继续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而已。可是介甫你以为这些全都是腐儒之常谈,根本不当回事,于是‘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孔圣人是很瞧不起这种人的,有人想学种庄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你现在竟然讲商贾之末利,更是错上加错,不能再错了。
“我现在已经把根源给你讲清楚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所说的这些,你要是不相信,后果自负。介甫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侵官乱政,就是贷息钱这种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的事情。但是你却干的一身是劲,这些事情,就连一般的平民都认为不可的事情,唯独你认为是可以的。这并不是说你智不及常人,而是你想要求非常之功,而忽视了一些常人都懂得的道理。介甫你智慧与贤达都超过了其他人,但是你做过了头,这就是用心太过。“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这两位圣人也经常向别人学习。王老弟你比这两个人,恐怕还是有点差距的吧,但是你却“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独讲一家之言,简直就是罪莫大焉。”
的确,作为王安石的朋友,司马光接下来讲了很多历史上“不受忠谏而亡”的故事,用以劝导王安石要从谏纳善。
在分析下属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利害之时,司马光指出所谓的宾客僚属见了王安石,只知“希意迎合,曲从如流,但安石你却对这些人却“亲而礼之”。如果谁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要大加批评,甚至赶出京城,你再这样下去,就会变成奸臣,这都是因为你太过于自信了。
司马光并未把王安石的所有努力一笔抺杀,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新法,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尽管日日尽心,夜夜忙碌,但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没有一个人能过安稳日子。这和“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原则大相违背,为什么你从小读书,到现在“白头秉政”,却“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自古立功立事,都不能违背人民的愿望,而你王安石偏偏只听信个别人的意见,放弃圣人之道,违背天下百姓之心,这样下去肯定有人要反抗,到时候再去治理,那岂不是会很麻烦吗?”
接着,司马光试图解释一下自己给王安石写的那封诏书,以平息一下两人之间的怨气。
近来有大臣上书,说散发青苗钱所带来的不利,陛下让我们讨论,你却因此为闷闷不乐,气的跑回家,借口生病呆在家里不上朝。我受命为批答,因为看到大家都因青苗钱而感到不安,而你却想在此时甩手不干,你这样做是很对不起陛下的。所以我直叙其事,批评了你几句,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让你早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改正错误,以造福天下。我讲的虽然难听了点,但是却没有一个字不是实话。听说你看了我写的文字,非常生气,上书给皇帝为自己辩解,以至神宗都亲自写信给你赔礼道歉,又让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你才出来工作。
你为社稷着想当然是好事,但我仍然希望你迅速的改正以前法令里不合适的地方,以安慰百姓,报答陛下的隆恩。接着又陈述说,我看你“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而且不复顾义理之是非,人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我认为你完全错了!陛下想让我做枢密副使,我因为无功,所以不敢居高位,陛下给我如此待遇,我不可以不报,所以才“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一切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无可在意。
现在陛下轻重缓急之事一律信任你王安石,无人能及,大事小情的取舍,也唯独信你王安石的。如果你说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如果你说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现在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都系于你一身,若你能进一言于陛下,请求罢除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你也有一个“改过从善”的好名声,这种好事,你为什么不做呢?
这是司马光为王安石指明的出路。
司马光看重的,是从政的名声。王安石看重的,是治国的效果。
司马光终于开始结束第一封信了,他说:我知道,今天讲的话,正好和你的想法相反,知道我说的这些都不合你意,但是我和你兴趣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你得位以行其道,惠泽天下之民;我也要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都是为了老百姓好,这就是所谓的目的相同而途径不同。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说,使我们的友情更上一层楼。至于听不听,是你的事。
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没有扔在地上,而是和官员们讨论一下是不是有道理,那我就千恩万谢了。但请你不要和你们条例司的那些官员讨论。因为那些人都是依附于你,唯你之命是从的人,只有变法,他们才有机会高升。“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他们就没戏唱了,所以,那些人一定会鼓动你继续变法,你千万不能因为这些小人而不思国家之大计!
讲到最后,司马光说道:“我们这些忠信之士,或许在你执政的时候讲几句坏话,听着不舒服,但是等你下台以后,我们仍然会帮助你,但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背叛你,踩在你的肩膀上继续往上爬。你到底选谁呢?相信你能有一个好的抉择。
有人以为王安石没有给司马光回信,其实不然,尽管王安石文集中没有收录第一、二封回信,但司马光在五六天以后写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中,提到了王安石的回信。
尽管司马光的态度略显不诚恳,也不乏有冷嘲热讽之笔,间以牵强附会之词,但王安石的回信却是“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司马光也不得不佩服王安石“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
《与王介甫第二书》写的相对简短,除去套话,我们也可从中略感一二。可能是王安石用事实反驳了司马光对青苗法的攻击,所以司马光辩解说:“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当然不会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但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我所说的,也许在几年以后就会发生。那时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负担重,当官的必然层层盘剥,以夺民之膏脂,日甚一日,那时你就知道我说的话不为过了。
司马光之所以“重有喋喋”,仍然是要劝王安石罢去新法,一切守旧。因为站在彼此的立场,王安石是一个革新者,而司马光却是一个守旧者,政见的不同注定了两人不可能成为盟友。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第二封信,仍然进行了耐心的辩解,可惜回信亦已失传,可惜之极!
司马光知道不可能说服王安石了,所以,在《与王介甫第三书》中,他的态度有了较大变化。
司马光先是客气一番,显得有品味有肚量:“惶恐再拜”,你的回信,说明你对我不见弃外,我对此不胜感激。然后就开始进入正题了:批评王安石不应该“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然后司又道:“如果“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如果“有司非其人”,就算是“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司马光不顾事实,继续攻击青苗法,说王安石从来不问百姓贫富,也不问他们愿不愿意要青苗钱,都是强制的派给的,指责王安石不识人,说王安石身边“邪说壬人为不少矣”。这多少有点不合乎逻辑吧。
司马光用历史上盘庚迁都的故事来教育王安石:“盘庚遇水灾而迁都”,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有从者有违者”,而“盘庚不忍胁以威刑”,只是加以教育劝导,“勤劳晓解”,最后人们都听从了他的决定,“皆化而从之”。这不能算是“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
我司马光并不是要劝你“不恤国事”,而是说,“天下异同之议”,你应该有所了解,并加以考虑,而不是只凭自己的意愿来办事。
司马光这封信的意思是,我跟你说了,听不听由你,以后绝不再谈。
王安石对司马光第三封信的回复,就是尽人皆知众口传颂的绝妙佳篇《答司马光谏议书》,全文如下: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鲁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
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此文写的简洁干净漂亮,王安石把司马光的长篇大论提取出了五个关键词,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天下怨谤”,然后逐一反驳,虽只三百余字,却把司马光几千字的来信驳的全面溃退,一无可取。
刘熙载称:“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当然,《答司马光谏议书》之所以流传千古而不废,绝不只是文辞好看读着上口评着过瘾。还因其思想深度与理论高度,都是他人所无法企及的。
“固由傲兀成性,究以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吴汝纶的这个评语虽然是在赞成王安石,但“劲悍廉厉”的说法有点不符合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我认为此文不但不“劲悍”,相反,却处处透着委婉,以平静的语言,表达着坚定的思想,这才真正是王安石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