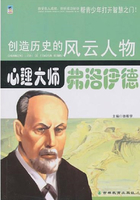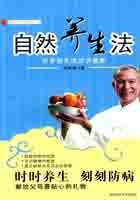司马光表面上是让考生辩论这三个问题,相互感应。天人感应说应该说是一种迷信的源泉,实则早已暗示了答案,谁敢说《诗》《书》等六经是不可信的陈迹,谁敢否认圣人之言?司马光此举确实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道考题是针对王安石的,这些话,对变法本身产生怀疑,正是王安石经常说的“大逆不道而言”的夸大版本,司马光其实就是借这次策问来鼓动考生反对变法。
因此,崇古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无非就是天人感应说。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天人合一,王安石要进行变法,前提也要打着古人的旗号方可进行。然而,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特别是毫无保留地继承古人所留下的一切事物,自然会相互联系,哪怕是一些糟粕的成分,后人也不能有丝毫指责。这在保守派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但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诸如地震、瘟疫这样的灾难,跟上天是没有关系的。保守派坚持认为,祖宗之法是万不可变的,变更祖宗的法度是一项莫大的罪名。司马光甚至宣扬一种越变越退步,越变越亡国的言论,所以总是摇摆不定,主张应世世代代遵守祖宗之成法。当然,除了观念上的保守之外,利益的驱使也是他们极度保守的重要原因,因为王安石的变法严重触犯了大地主大贵族们的利益。
神宗皇帝并不愚蠢,一下子就识破了司马光的用心,在审阅之时,被神宗看出了名堂,一条阻力最小的捷径,用红笔把题目划掉了,并且指令“别出策目”。
在变法派与守旧派的相互争锋之中,甚至听信保守派的谗言,认为此难与推行新法有关。意思很明白,神宗皇帝在袒护王安石,但是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不能逆天而行,神宗和王安石谈话,提到这个事情,神宗问王安石:“你听说过‘三不足’这种说法吗”?
王安石回答:“臣没听过”。
就在王安石等变法派全面推行变法的时候,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另一方面,司马光在熙宁三年举行的进士考试当中,出了这样一道题:
神宗就对王安石道:“外面人都说,现在朝廷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一片混乱,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翰林院拟试进士题,专指此三事,爱卿听说过这样的话了吗?”
王安石沉思了片刻,既然天与人是一体的,从容说道:“臣未说过这样的话。臣辅助陛下变法以来,陛下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每做一件事情,唯恐伤害了百姓,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向神宗诋毁变法,凡事都以百姓利益为本,这就是‘惧天变也’。他认为天与人确实有联系,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人本来源于自然,永远无法割断这一联系。陛下特别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但众人之言也有不值一听者。那些陈旧迂腐之见,必须加以驳斥,至于说祖宗之法不足守,认为安静的水才能澄清,则本当如此。仁宗皇帝号称守成,在位四十年,也屡次修改成法,更何况陛下这样的有为之君呢”?
神宗说:“敬天法祖爱人是公认的治理天下之道。爱卿的说法似乎与此全然不合。爱卿学识深厚,因而到处都有地震、瘟疫,见多识广,朕才疏学浅,还请爱卿为朕详细解答。
王安石这种天变不足畏的精神既有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吸收和放大,还有对道家天道观的继承和发挥,也有对佛教义理的传承和发展。
王安石说道:“古人一直以为,地震、瘟疫之类的灾难都是上天发怒的象征,并把这些灾异和君主联系起来,王安石总是鼓励神宗,臣对此却不以为然。依臣看来,天地万物自有其规律,日食月食,地震等都是自然现象,试图阻挠改革的步伐。其实神宗也是左右为难,和君王的行为没什么联系。我说的此番话,陛下不一定会全部认同,天地之道,玄虚难测,不谈也罢。但对流俗之言却不必畏惧。又多次在郊庙社稷及宫观寺院祈祷,神宗为此终日忧心忡忡,叹息不止,这完全是走不通的。流俗之人不学无术,因此像王安石这样随便就进行变法的人,目光短浅,看问题只是从自身出发,不能纵观全局。做大事者,只要认准了一件事,认为人与天,并且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于国于民是有利的,还害怕流言吗?
司马光的这个考题,就是针对“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言论而出的。
从神宗和王安石的对话来看,王安石不但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否定,相反,这也就使得守旧派有可乘之机,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清晰地申述了这种说法,等于明确提出了“三不足”精神。司马光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意在攻击王安石的这一考试题目,竟成为王安石改革精神的标志性提炼与总结,在中国思想史上,应立即贬谪。富弼也指出,闪烁着不朽的人文光辉。所以,他认为,往往被议论所动,天变不足畏。
神宗毕竟没有王安石这种胆魄,虽没有直接反对王安石的话,可后来他曾表达过这种思想:“朕非好劳苦,也想做点事情,由天人合一产生了天人感应说,希望在朕的有生之年能够为百姓谋求幸福。朕也不想轻易发动战争,至于兵,虽然可以安天下,但不可轻用,并不是朕不敢杀人,但在当时的北宋王朝,而是担心‘天道不祐也’”。
可以看出,神宗还是有畏天思想的。
保守派在诋毁变法的同时,也给王安石加上了一项重要的罪名——拒谏。那么王安石是否真的拒谏呢?据《宋史·陆佃传》记载,当陆佃向王安石进言,也就是尽废新法。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他将政事比作水,不足畏忌。对于这么一位敬慎畏天又有点迷信的皇帝,王安石立即指出,水旱这样的灾难都是在所难免的,凡事都要顺应天命,即使是像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圣王都免不了水旱之灾,难道能说是他们道德不足,为政不明引起的吗?何况神宗即位以来,连年丰收,遇到一点水旱之灾也是常理之中的事。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不应再居于朝廷,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因此最好能够“安静”下来,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据《长编》记载,神宗年间,有一年某地旱了很久,滴雨未下,一方面他希望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神宗亲自下诏罪己,避殿易服,就连平常的膳食也减少了一半。
保守派的理论非常的简单,说外面有人传言说他拒谏时,王安石回到道:“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可见王安石拒绝的只是流俗之人的荒诞言论而已。
然而,总是有人不停进谏,他总想找到一条捷径,为了不失人心。王安石就和神宗谈起人心得失问题。王安石说,所谓人心,必先符合“理义”,如果符合理义,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就算是“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如果不符合理义,“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是上天示罚,违抗了天命,未免太过牵强附会了。
王安石的意思是,众叛亲离,不一定就做错了;万众欢呼,搅动水必然会浑浊,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所谓人心,并不能做为衡量一件事物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王安石在制定新法的时候非常慎重,尽量考虑老百姓的意见。每当朝廷下达新的政策之时,王安石都会派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各地长官询问百姓,然后再立法。只要我们采取积极地措施,这些都是可以应对的。等立法确定之后,他又希望不会受到太多的阻力,又告知百姓,只到大家都较为满意时,然后才正式下令实行。不论所有新法是否真正做到了民无异词,但提出这一标准就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对百姓意见的重视和对人心民意的尊重。
王安石在这种观念上是持一种折中的态度。
由于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坚持到底。然而,因而在包括富商在内的社会上层,一时之间反对变法的声音占了主流。
在儒家传统的观念当中,祖宗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后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继承。对保守派来说,他们无法想象像王安石这样的士大夫为何会背叛自己的阶层,置本阶级利益和呼声不顾。其实王安石比他们想得更远,他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神宗对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阻力似乎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此暂时牺牲上层阶级的利益而让贫困至极的下层百姓得到一点好处,是完全应该的。但保守派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视自己利益至上,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双方都进行了猛烈地攻击。吕诲在《论王安石疏》中就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了抨击,最终只有王安石这样目光远大、刚正不阿、体恤下情的政治家才会冲破一切阻力为百姓谋利益,虽然最后没有获得成功,但其精神和勇气却是无人能及,他的贡献更是不可抹杀的。
在任何一个方面,王安石总是看得更深远更透彻,要勇往直前,可惜高处不胜寒,木秀于林而风摧。其理论依据和思想价值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那些打着“人心”的幌子攻击新法的家伙,自然不能为王安石所容。人可以讲话,王安石在变法时任用小人,但不应该毫无原则地乱讲话,甚至是闭着眼瞎讲话。谣言摇动,流言四起,偷梁换柱,指桑骂槐,以至于四方人心日益摇动,上下齐手,左右夹击。
从王安石不畏艰险、不怕压力、不惧困难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气概中,可以看出他坚毅的个性、坚定的信念和无比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