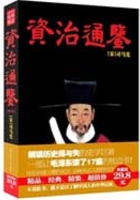住在郊野,住在那布置得非常豪华的别墅内是一什舒服的事,这座别墅有宽阔的建筑,有很多下房和马厩,古巨大的果树园、花园和菜园,顺着倾斜的地势一直迤逦到特拉夫河边上。克罗格家生活很豪华。他们家的富丽堂皇和冬妮父母家中那种殷实,然而略嫌死板的富裕环境是有区别的。在外祖父母这里一切远要奢华得多;年轻的布登勃鲁克小姐对这件事的印象很深。
这里绝对用不着佣人在屋子里或者甚至在厨房里作杂事,但在孟街的家中,除了祖父和妈妈对这一点不甚注意外,父亲和祖母却常常叨唠她,不是叫她把什么地方的灰尘拂掉,就是叫她向她那位又听话又虔敬又勤俭的堂姐妹克罗蒂尔德学习。当这位小姑娘坐在摇椅上向仆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她那从母亲体内传来的贵族习性又抬起头来了,这家里除了仆人以外,还有两个年轻姑娘和一个车夫伺候两位老主人。
不管怎么说,每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间高大的四壁裱糊着花缎的卧室里,刚一伸出手去,首先摸到的就是那柔软的缎子被,这总是一件舒服的事;此外,坐在露台前边吃早点,从敞开的玻璃门外流进花园的清新气息,喝的不是咖啡、茶,而是一杯可可,每天都喝诞辰用的可可,外加厚厚的一块新鲜蛋糕,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事。
自然,除了星期日以外,这顿早点冬妮总是独自享用的,因为外祖父母要等冬妮上学半天以后才下楼来。当她随着可可吃下一块蛋糕以后,就拿起书包,迈着碎步走下露台,穿过修整得整整齐齐的临街花园走到街上去。
她长得很可爱,这位小冬妮·布登勃鲁克。她那茂密的卷曲的头发从草帽底下露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淡会色变得越来越深了。她的眼睛是从蓝色的,炯炯有神,微微噘着的嘴唇给这张娇憨的小面孔添上一些顽皮的神情,这种神情就是在她的秀丽的身姿上也找得出来:她的细细的小腿上穿着雪白的袜子,走路的时候跳跳蹿蹿,满有自信地微摆着身子。很多人都认识这位布登勃鲁克参议的小女儿,当她走出花园的入门,来到种着栗树的林荫路上的时候,很多人向她打招呼。也许是一个头上戴着大草帽、草帽上飘着淡绿色丝带的卖菜女人正赶着一辆小车从村里来,亲热地向她招呼:“好啊,小姐!”也许是那个大个子搬运夫马蒂逊,穿着黑色的短外衣,肥腿裤子和扣绊鞋,看见她走过来恭恭敬敬地摘下他那顶粗劣的圆筒帽……
冬妮站了一会,等着她的小邻居玉尔新·哈根施特罗姆出来,她们俩总是一起上学。玉尔新是个高肩膀的孩子,一双大眼睛漆黑有光,她就住在旁边一座攀满了葡萄藤的别墅里。他们一家不久以前才在本地落了户,玉尔新的父亲,哈根施特罗姆先生跟一个年轻的法兰克福女人结了婚。这个女人生着一头异常浓黑的密发,耳朵上戴着全城找不出第二款的大蒙石。她娘家姓西姆灵格。哈根施特罗姆先生是一家出口公司——施特伦克和哈根施特罗姆公司——的股东,对本市的一些活动抱着很大的兴趣和热心,野心勃勃。然而由于他的婚姻,一些古板守旧的人家像摩仑多尔夫、朗哈尔斯和布登勃鲁克等对他都相当疏远;虽然他在各种委员会、同业公会或者理事会里都是积极活动的一员,可是他并不很得人心。他似乎千方百计跟这些名门旧族的人作对,他狡黠地阻挠人家的主张,努力贯彻自己的计划,借以向人家证明他自己比别人高明多少倍,是怎样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参议布登勃鲁克谈到他的时候说:“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总是跟别人找麻烦……他似乎专门跟我作对,只要有隙可乘,就反对我……今天在救济总会里闹了一场,前两天在财政局里……”约翰·布登勃鲁克接着说了一句:“真是个小人!”——又有一次父子两人吃饭的时候又气恼又沮丧……出了什么事了?哎,没什么……他们没作成一笔大生意——运往荷兰一批稞麦;施特伦克和哈根施特罗姆从他们鼻子底下把这桩交易抢走了;简直是一只狐狸,这个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
冬妮常常听到这种谈话,这不能不在她心上引起对玉尔新·哈根施特罗姆的某些恶感。她们同路上学只不过是因为她俩是邻居,平常她俩却老是吵嘴。
“我父亲有一千泰勒!”玉尔新说,明知道自己在撒谎,“你父亲呢?”
冬妮因为嫉妒、自卑而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她不动声色地顺口说:“我今天喝的可可芳香极了……你早点吃什么,玉尔新?”
“哎,我差点忘了,”玉尔新回答说,“你要不要吃一个苹果?——呸!我才不给你呢!”说着把嘴唇噘起来,一双黑眼睛因为得意而变得湿润润的。
有时候玉尔新的哥哥亥尔曼也跟他们一块上学,他比她们大两岁。她还有一个哥哥莫里茨。莫里茨因为身体不好,请先生在家里教。亥尔曼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可是鼻子却有一点扁。因为他老是用嘴呼吸,所以不断地吧嗒着嘴唇。“胡说!”他说,“爸爸的钱可比一千泰勒多得多呢。”在亥尔曼身上,冬妮最感到兴趣的一点,是他带到学校去的第二份早点——不是面包,而是一块椭圆形带葡萄干的奶油柠檬糕,软软密密的,里面还额外夹着几条香肠或者一块鹅脯肉……这东西好像很合他的口胃。
对于冬妮·布登勃鲁克说起来,这真是件新鲜的东西。柠檬蛋糕加鹅肉,真使人馋涎欲滴!他让她在他的饭盒里看了看,她忍不住把自己的愿望说了出来,她真想尝一块。
亥尔曼说:“今天我不能给你,冬妮,明天我可以多带一块来给你,要是你愿意拿点什么来跟我交换的话。”
第二天冬妮走到巷子里等了五分钟,可是玉尔新还没有来。又过了一分钟,亥尔曼一个人走了出来;他摇着用皮带拴着的饭盒,轻轻地吧嗒着嘴。
“喏,”他说,“这儿有一块加鹅肉的柠檬蛋糕;一点肥的也没有——完全是瘦肉……你给我什么?”
“一先令,成不成?”冬妮问。他们俩站在林荫路中间。
“一先令……”亥尔曼重复地说。他忽然咽了一口唾沫说:“不,我想要点别的。”
“要什么?”冬妮问,为了这点美味蛋糕,她想她什么都肯出的。
“一个吻!”亥尔曼。哈根施罗姆喊了一句,一下子用两只胳臂抱住冬妮,不分头脸地乱吻起来。然而他始终没有挨到她的脸,因为她以惊人的敏捷把头向后仰过去,左手拿着书包顶住他的胸脯,使尽全力用右手在他脸上打了三四下……他脚步蹒跚地向后退了两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妹妹玉尔新像一个黑魔鬼似地,从一棵树后边跳了出来,怒火冲天地扑到冬妮身上,扯下她的帽子,拼命地抓她的脸……从这件事以后,他们的友谊差不多也就告一段落了。
冬妮之所以拒绝哈根施特罗姆吻她,显然不是出自羞涩。她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姑娘,她的卤莽放纵,惹得她的父母、特别是参议为她操了不少心。她虽然头脑聪明,功课学得很快,然而她的品行却实在不端,弄到后来连女校长,一位亚嘉特·菲尔美林小姐,也不得不亲自到孟街登门拜访。她因为困窘,遍体汗淋淋的,非常客气地劝告参议夫人说,应该严厉地管教这个小姑娘,——因为这个孩子不顾师长屡次劝诫,又在街上间了一次祸。
冬妮从城里走的时候,她跟谁都认识,这并不是有失体面的事;相反的,参议对这一点是表示赞许的,因为他认为这表示他们家人不摆架子,对人和气、有礼貌。冬妮常常和托马斯一起在特拉夫河边上的堆栈里闲荡,在燕麦和小麦堆上爬上爬下,和坐在账房里的工人、记账员聊天。这些账房又小又暗,窗口贴着地面。有时候冬妮长至在外边帮助往上拖粮食口袋,她认识那些赶着马车用铝铁桶从乡下往城里运送牛奶的女人,冬妮常常让她们用车送她一程,她认识在金银首饰店的木头小屋子里干活的花白胡子的老师傅们,这些小屋子就建筑在市场的拱道下边;她也认识市场上卖鱼、卖果子、卖菜的女人,甚至连站在街角上嚼烟叶的脚夫她也认识……好了,用不着再一一列举了!
可是冬妮决不仅限于跟人打打招呼而已。有这么一个人,脸色苍白,没有胡须,谁也说不准他究竟多大年纪。清晨他常常带着忧郁的笑容在大马路上散步。这个人神经非常脆弱,谁要是猛地大喊一声——比方说,在他身后“咳”“呵”地一叫——,他就吓得瘸着一条腿乱跳;而冬妮每次看见他总不放过他,一定让他跳几跳。此外,街上还有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太婆,头非常大,无论什么天气她总支起一把硕大无比、七穿八孔的破伞,冬妮每当看见她就要嘲弄她,叫她“破伞太太!”或者“香蕈!”。这种行为当然不怎么得体。还有,冬妮常常跟两三个气味相投的伙伴到约翰尼斯街里一条横胡同去,这里面住着一个卖布娃娃的老太婆。她生着一双奇怪的红眼睛,独门住在一问小屋子里。冬妮几个人到了她的住房前边,就拼命地按门铃,等老太婆一出来,她们就假作殷勤地问,痰孟先生痰孟太太住不住在这里啊,问完了就尖声笑着跑开了……这一切恶作剧都有冬妮·布登勃鲁克的份,而且她作的时候好像心安理得似的。如果哪个受害的人吓唬她两旬,你就会看到这位小姐怎样倒退一步,噘着上嘴唇,把漂亮的小脸蛋往后一扬,“呸”的啐一口,摆出一半恼怒一半讥诮的样子,仿佛在说:“告诉你!我是参议布登勃鲁克的女儿,你敢……”
她在城里走来走去,正如一个小皇娘娘似的,她完全有权力依照自己的旨意对臣属宽容或者残忍。
3
让·雅克·霍甫斯台德给参议布登勃鲁克两个儿子下的断语,显然恰当中肯。
托马斯生来就是个商人,注定为公司未来的继承人。他现在正在一处歌特拱顶建筑的老式学校念实用科学。托马斯聪明、灵活、理解力很强,每当他的兄弟克利斯蒂安摹仿教师的动作时,他总是非常开心地呵呵大笑。克利斯蒂安在普通中学念书,天资一点也不差,然而不如托马斯那么严肃认真。他摹仿教师摹仿得惟妙惟肖——特别是那位教唱歌、图书等种种课程的能干的马齐路斯·施藤格先生。
施藤格先生的背心口袋里永远插着半打左右的铅笔,削得尖尖的。他戴着微红的假发,穿着一件宽大的浅棕色的外衣,一直拖到脚面。脖子上的硬领几乎高到额角。他很机敏,喜欢说一些双关语,例如:“你应该画一条弧线,我的好孩子,你画的是什么?你胡画了一条线!”或者他对一个懒学生说:“你在三年级蹲了三年,在六年级岂不要蹲上六年!”他最喜爱的课程就是在音乐课上练习“绿色的森林”这首歌。他预先让几个学生到外面走廊上,等到课室里唱到“我们愉快地走过田野和森林……”这句歌词的时候,走廊上的学生就低声哼唱最后一个作为回声。有一次克利斯蒂安·布登勃鲁克,他的表兄弟尤尔根·克罗格和他另外一个同伴安德利亚斯·吉塞克,一个消防队长的孩子,被委派去做这个工作。该发出柔和的回声的时候,他们把煤斗叮啷当啷地滚下楼梯去。为了这件事,他们下午放学以后,不得不留在施藤格先牛的住处等候处罚。然而他们在那里过得很惬意。施藤格先生把早晨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吩咐管家给予布登勃鲁克、克罗格和吉塞克每人一杯咖啡,接着把他们打发走了……
事实上,在这所圆穹屋顶的老学校——原先是一所寺院学校,教学的老头子们都是一些脾气温和的好好先生,领导他们的校长,一个喜欢闻鼻烟的和善老头,本人就主张待人以宽。因此这些教师们也就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学问和欢畅的情绪彼此并不排斥。他们相竟以温文尔雅的精神从事工作。中年级有一位教拉丁文的姓师的先生,从前作过牧师。这位牧师身材颀长,生着棕色的胡须,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他的职业恰好暗合他的姓氏。他不止一次让学生翻译pastor这个拉丁字。他的口头禅是“受到无限的限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这样说是不是有意在开玩笑。有时候他表演一种口技,把舌头钳在嘴里,然后倏地往外一吐,发出清脆的一响,好像香槟酒塞子弹开的声音一样,弄得全班学生都愣愣地不知所措。他喜欢跨着大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对个别的学生谈他未来的生活,谈得有声有色。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刺激学生们的想像力。最后他态度严肃地回到功课上去,就是说,让学生朗诵几首他写的小诗。在这些诗里面,他巧妙地把变格规则和烦难的语法结构都编排进去。他自己也常常得意洋洋地高声朗诵这些诗,特别把节奏韵律念得清清楚楚。
汤姆和克利斯蒂安的童年时代……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叙的大事。那些日子,笼罩在布登勃鲁克家庭的是一片阳光,商号生意特别兴隆。虽然偶然也发生一次暴风雨,一场小灾祸,像下述的这种:
史笃特先生是一个裁缝师傅,住在铸钟街。他的老婆买卖旧衣服,因此和上流社会也有来往。史笃特先生穿着一件羊毛衫,遮住他那露到裤子外面的便便大腹……给布登勃鲁克家的小少爷做了两套衣服,工钱一共七十马克;因为这两个人的请求,他同意在账簿上记了八十马克的账,把多余的钱给了这两个孩子。这是一笔小生意,虽然并不怎么干净,可是也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可是,命运捉弄人,这件事被揭穿了。史笃特先生不得不在羊毛衫上面披上一件黑罩衫,到参议的办公室来对质,汤姆和克利斯蒂安当着裁缝的面受到一次严厉的审询。史笃特先生叉着两条腿,斜侧着头,毕恭毕敬地站在参议的安乐椅旁边,极力想把事了结下来。他说什么“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说什么“事情既然已经闹出来了”,他如果能得到七十马克也就知足了。可是参议对这个骗局却气得不得了。他严肃地考虑了很久,结果是把孩子们的零用钱提高了,《圣经》上不是写着吗,“不要诱惑我们!”
这一家人在托马斯·布登勃鲁克身上显然比在他的兄弟身上寄托了更大的希望。托马斯举止有节,性格虽然活泼但不张狂;相反地克利斯蒂安常常是喜怒无常,有时候他会作出一些滑稽的傻态,有时候又会把全家人吓得七魂出窍……
有一次,家人正坐在餐桌上吃尾食水果,大家愉快地聊着天。突然间,克利斯蒂安把一个咬了一口的桃子放回到盘子里,脸色变得惨白,一双深陷的圆眼睛在那大鼻子上瞪得大大的。“我永远不吃桃子了,”他说。
“为什么,克利斯蒂安……老说这种蠢话……你怎么啦?”
“你们想想,要是我一不小心……把这个大核吞下去,它正卡在我的嗓子里……堵得我出不来气儿……我跳起来,憋得两眼发蓝,你们也都急得跳起来……”他忽然惊惶失色地呻吟了一下,不安地从椅子上欠起身来,仿佛要逃走似的。
参议夫人和永格曼小姐真的跳了起来。
“老天爷呀——克利斯蒂安,你没有真吞下去吧?”从他的动作看,好像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似的。
“没有,没有,”克利斯蒂安说,渐渐地安静下来,“我是说,假如我把它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