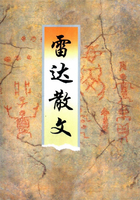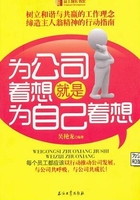真理未必就真得出奇,陈言也许是真理的一面吧,必千千万万人都想过说过方为陈言,这岂不就是千千万万人所有过的感触,难道它竟会一点道理都没有?陈言务去戛戛其难,真真又吃力又不讨好,做句翻案文章,陈言便是中庸之言——您嫌不时髦,其实,错了一。孔二光生现在很出风头,不过我不好拂您的意思;——那么民众的话总该懂得罢。(平按,心余自己也有点缠夹二,民众运动在禁止中,民众的话与中庸之言身分悬殊,巧混为一谈,奇哉!)既然知道“难”,便不该“去”,还说什么务去!您瞧古诗十九首那一首不是老腔调,却不大听见有人骂它腐化,虽然现在也难说。(平按,此节比拟不伦,口气幼稚,牢骚突发,无理取闹。)
“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种感慨老得可以罢惟其搂着如花的美眷,所以回首流光万分懊恼;亦正因为流年似水不曾等过谁来,所以把玉精神花模样的情人终于给辜负了。白发和红颜对照,芳华与迟暮结缘,是人人都有的悲感,不必定要多愁多病的身,倾国倾城的貌,方才配“心痛神驰眼中落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之文)
转瞬之间,艳冶在风前零落,灵智也是一闪的电火罢生命的颜色芳香,以体力的衰颓日趋于黯淡憔悴而犹不自觉,直到蓦然回首,昔梦前尘恍如隔世,方才知道年光走得好远,把我们早给拉下了。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回头怎么样?不回头又怎么样?人生一个破瓦罐,不回头最为得体,虽然不免回头更是人情。
人生一世,做小孩子好像顶快活,却偏偏想它不起。最小的几年简直全不记得,六七岁以后渺渺茫茫,自十岁以至三十岁,这一杯青存的醇醪回想起来馋涎欲滴,“好酒!好酒!”可是当时呢,狂鲸吸水,到口干杯,又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由你礼部堂官说得舌敝唇焦,谁耐烦“一口一口的喝”呢。过了三十岁,即使你将来康强老寿花甲重逢,也是下坡的车子了,去得何等的即溜呵!看人家刚断奶的己在学步,夹着书包的已懂得看女人,结婚未久的已在做母亲,如我辈的中年人,不垂垂待老复何所待呢?
“酱汁中段”,幸登古稀之年也只有三十年的快活。这三十年中,困觉先去掉一半,还有不少打岔的事儿,生病啊,拉屎啊,办公事啊,至少又打个七五扣,归齐只剩了十一年三个月。(平按,这又在算帐,又在用陈言,心余的记性不错。)那促狭的短命,真会“细细儿过”倒也罢了,正如兼好上人所说的:“倘若优游度日,则一岁的光阴也就很是长闲了。”但这班傻大姐浑小子,由他那样的聪明,只怕未必听得懂。人到中年,方渐渐体会出一点点儿生是怎么一回事情,只可怜残肴冷炙剩也无多,由你嚼碎骨头也将同白蜡,滋味毫无。况且年纪再老下去,又要胡涂,不免重新发十七八个昏方肯咽气。这何苦来!人寿这样短,什么事也来不及做,好像“大英国”的萧老爹曾经说过的。
名式各样的变花头,收梢结个大倭瓜,变花头不足奇,结倭瓜也是当然,可怪的是哪里来的倭瓜子。我不怕自己与草木同腐,也不恨充当蚂蚁的一顿早餐,只诧异这条生命的何来。有时午睡瞢腾,醒来心上一拎,仿佛直往下沉,仿佛四无抓挠,又仿佛大祸要临头;定睛细看,一切都照常,很合式,不多也不少,多只多了一个我。假使一旦没有这个我,我想一切还会照常,还会很合式的。
想去死吗!不,决不!只愿生命忽然遗失,或者著贼骨头偷了去,顶好困醒一觉,干干脆脆地不见了我,那没“南无阿弥陀佛!”但偏偏不,一醒来跷起脚先看见我自己雪白的高脚跟。“直头讨厌笃!”所以只得再去寻死觅活。刀乎?绳乎?河水乎?井水乎?抑海水乎?安眠药水乎?——还是仙丹乎?何去何从?
寿终正寝的,面孔已经有点讨厌相;何况悬梁的要伸舌头,投河的要鼓肚皮,服毒的要变青黑脸,抹脖子的,阿一哇!头儿好像西瓜,丁零当郎滴溜扑落地直掉。临命以前曾写出班香宋艳的奇文,曾留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倩影,都毫不相干,反正得出一次乖丢一回丑,和带绿毛笔挺挺的僵尸在伯仲之间而后已。
再说也不大好办。火葬,我总疑心会烧得滋滋作响,臭气薰天;浸在水里烂胖起来更糟;给老鹰吃,怕它挑精挑肥,扔下一只眼睛半只耳朵不吃;保存在玻璃棺材里,未必人人有这福气;给鬼子去试验有点不高兴;说来说去,还是刨个深深的土坑往里一埋这个老法子顶妥当,明知也一样的要发霉变烂,只是眼不见为净,孝子慈孙之心庶几慰矣夫!(以近日所闻“乾隆皇帝”的头发几丝肋骨几根也弄得零零落落,则人土为安原未必尽然,甚矣死不如速朽之为愈也。)然又终于不免为蚂蚁们当早点心,究竟也不很合算。话又说回来,贼骨头若老找不着,那么随便同仁堂达仁堂一个子儿一包的“九还大丹”炒豆一般吃它个几千葫芦。然后“吾知免夫!小子!”
好好儿细细儿活着不成,算我不曾活也不成,一定要妈妈胡胡活着去等死,那方才算“的确行”,这多们古怪!幸而我老是看人家去死,老实说自己还没有死过呢。“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落水鬼的疯话。我要死,至多也只死争一回试试看,第二回“恕不”了。何况口袋里还有一个子儿一包的九还大丹。
虽然如此,眼睁睁地看人家直僵僵一个,直僵僵一个,家里人围着他哀哀地哭,也活得太不得劲儿。若死者我认识他,更难免多少的伤感。若不幸是我的故人,我的至亲,这一种死生之戚,竟许弥漫于心识的表里,影响于我对一切的态度。所以以旁观的地位看生命的神气,不见得就会比自己反省高明。
死者澌灭无余,往而不返之谓。有些人呢以为如此大佳,了者好也,人世纠缠得还不够,死了再去纠缠着,未免不智且伤美。长往不返,以他们的眼光看未始不是好事,至少也不是坏事。记得山叔老人未跌下火山以前,曾在不苦雨斋中大家谈过,若死了果真要到阴间有许多麻烦。例如:见了无穷的老长辈老老长辈,一个个都要请安问好,他们还许带你去朝皇见驾,大碰其头,偶然一不小心,对看大明的祖宗说什么“本朝深仁浓泽”,立刻要碰钉子。六十岁的老头子赶着二三十岁的少年,规规矩矩叫“爸爸”;二十岁的刁、伙子不得不搂着八十岁的老太太,亲亲热热叫“夫人吾爱”。大太太同时可以有三四位,一个不好,就打翻醋瓶醋罐,大闹幽宴。小孩子老是吃着奶,老是不会大,殓时的朝衣朝帽,若子孙忘记了焚化冥衣,就得老穿在身_L,连上茅厕的时候都脱不下更有阎王爷非刑拷问,牛头马面们竹杠常敲……奇苦百端,形容不尽。
另有一班人真相信灵魂出窍,黄泉路的远近好比到一趟外国,去了自然就回来。所以供桌上的酱肉骨头不妨咬嚼,绍兴老酒也喝个三钟,穷了有元宝锡箔可以救济,受罪有和尚道士可以超度,想呼奴唤婢则有泥塑的金童玉女,想抽鸦片烟则有纸扎的全副烟盘,子孙生病他先叹气,子孙富贵他也荣华。……总之他名说死了,却没有死干净,还剩个一点儿,严格说来他是没有死哩。
哲人长闲,愚人忙瞎,我们不忙又不闲,尴尬。把死人当作活人看,死马当作活马医,(平注,又在信口胡溜。)我虽办不到。但死得一干二净,据说非常合式,我也不大相信。自己会死得如此的干干净净,即说明是美事,也有点害怕;若所亲昵的看他斩钉截铁地躺下去,愈加使我不堪。平居形影相接,言笑叮通的,一转眼不看见,永远不再相见了,这不但不可忍耐不可解释,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如依感情,我不是不喜欢宗教的,即下等的宗教也喜欢。我喜欢仙,我喜欢神,——只有菩萨端坐在莲台上,好像不大舒服——我喜欢狐狸,我也喜欢鬼,即使它不肯变红衣女郎来魅我,甚至于碰见十七八代的老祖宗在黄泉路上握手谈心,也不觉得很讨厌。老爹们不以为然吧?
然而我的叔叔姑母们,青这小孩子不敬祖先,不信鬼神,方以为是十足的新党,岂不冤哉枉也!“车旁军”的意见,我怀抱中满坑满件哩,不瞒诸位说,假如果真,上边三十三天遍住神仙,下面十八层地狱满填怨见,一世界一如来,一洞府一妖精,岂不比我们的世界分外有趣?只要一跷辫子,(平按,这是古语,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译文,仍之)少上可以看见这些古怪的顽意儿,又有什么拼不得?亲戚朋友死了,也无非在这几个地方游来荡去,那怕找他们不着,“您光走一步罢,我吃完这筒烟就来”难道我独独不会这般坦然地说吗?
可是不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环境郡来警戒我,这世界不是这样子的;肉体以外不见有生命,生命以外不见有世界,一切在你面前变灭,你也变火于一切里,既无法可想,也没有例外。这严冷的事实世界,我惟有忍耐,我惟有默认。
还偷偷地告诉你们,有一回我正嘻嘻哈哈过着孩提般的好日子,何来突兀的事变。巨浪般的打到心仁,把蓬熟中的兴会和意气,卷得落花流水,无影无踪日此以后,沉浸于哀之渊里消受一味透骨的冷,连丝毫的想象力都不再有,更不必提憨笑的重温了。我痛感幻灭的可伤。
逝者暂住在别人的记忆里,能有多久呢?忆中的渐渐抛却也就可以算永逝了。我由不得要努力追挽这些日就泯灭的影子,在笔墨间留下一二分的痕迹来,明明知道和谁都不生关系,死者更加无所为,只当作我自己的悲哀的玩具罢。
以前的也记不得了,庚戌之夏我在苏州,一个郁闷的傍晚,油灯没有点,天色有些黑了,蚊虫轰轰,成群搭淘的在“做市”,忽然走进一远方的客人,把姊姊误认作母亲,我们拜见后叫他舅舅,他便是沈彦君。
那年我十一岁,姊姊比我大一岁。我记得清楚,母亲的屋子靠南窗有一张长抽屉桌,他就坐在这桌子东边的靠椅上。不到一两个钟头,我们已经和这新来的客人熟得非凡。晚上都在老梧桐树紫藤花棚的书房里说着话,我们听得出神,好像无论什么都是新鲜的。我手背上忽被毒蚊子叮了一口,又痛又痒且肿,可是还有滋有味的听着,听着。直到母亲催了几遍,才挨墙摸角进去睡觉,而他们的话正说得热闹哩。
第二天一早直往东书房跑,他正在检点送人的礼物。我第一看见大理石面的圆桌上添了许多泥马,各式各奇,跑着的,卧着的,站着的,有低着头的,有扬着头的,黄的,白的,枣红的,数了数一共八匹,他说这是“八骏马”,都给了我。原来是给我的!弄弄这匹,摆摆那匹,十分高兴,尤爱那匹狂奔着的枣骝马,后来还为它做了一个红蓝闪缎的锦鞍:他同时给我的方墨盒至今还在,枣骆马呢,可惜查无下落了。(紫君说她也看见过这八匹马,她也想玩的;没有看清楚,已经被装在箱子里去)
他喜欢我,我自然更要亲昵他。只是不久就听见讲什么“攀亲”,他且时常以此来逗我笑,弄得我很窘;而且对于所谓攀亲也者,当时并不感兴味,有时以太窘而竟生气撅嘴,虽然心中好像也添了一种渺茫的关系,和他有一点儿私亲,暗地里在傲视我姊姊,自他北去以后,我们真是老盼着他来。
壬子以后,春秋佳日,他每年南来,来时多半住在花园里的达斋。园虽不大,也有苍润的山石,曲折的池馆,扶疏的花木。长廊下我和他比放汽枪玩,在屋子里又围着他听讲《聊斋》,谈狐说鬼,娓娓不穷。他们若打牌,我就看着。有一回我摇另另坐在一张轻巧的洋椅上,正看他的牌忽和出一付三元,我狂喜仰后就跌,四座愕然,这是一直传为笑柄的。
顶怕他有客来,如果老不走,我真气闷万分,再去张张看,总还在那边聒聒而谈,也不知讲些什么。他若出门拜客,更觉不以为然,在家里玩玩不好?出门有啥好处?碰巧风和日暖,恶客不来,太阳快要落山,他带我们观前一带走走,买点小吃,那最快活不过。我至今还想吃吴苑深处的扁豆糕,细滑白净,上面洒着红绿的糖。
晚饭以后总是闲谈,我在圆桌子旁边听着。黄黄的洋油挂灯下,低了头,无聊地看桌上红木边缘纹理的细密和嵌着的大理石面的光滑,无端有点怅触。“这清闲的景象不知有几回?”大约是这一类的念头罢,我还想得起来。这可以说是惘然的初见。
乙卯初夏初次北行,到天津后暂住他家,父亲先进京去了。他住的洋房,粉红色的墙壁,挂着美丽的古画,我觉得很精致。海边的气候,傍晚风凉,与江南又不同。一星期后,阴历五月朔,天气晴佳,他带我上了到北京的火车,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看见近畿的原野村落,绿油油的麦子和高粱。以后我来往这条路上常常看见这景色。自那年秋天我们移家北京,他一直住在天津。到丁巳年,紫君和我成婚,她是他所最爱的女儿。
恕我打个岔,说几句关于沈彦君的话。他是一个嗜好很多,性情极厚的人。这五十年中,他一味兴高采烈地活着,爱那一切,依恋那一切,执着那一切。他爱他的儿女,也爱他的亲戚故旧;他喷于宦海中浮沉,却老想优游泉石;他爱看画,也爱看如画的山;他摩挲手中匡鼻烟壶,又喜徜徉于暮年缔构中的南山别业;小至于一盆小枫,高不过三寸,细得像一根铅丝,大而至于突兀老苍的雷峰塔,一杯水整个儿的西湖,无不在他珍惜之中。他在天津,惦念那钱塘的故乡;等到回到杭州,我看他也无日不在梦见京华的软红尘土。而我于垂髫之日,就听他和我父母谈讲搬到塘栖镇上如何的好法,什么临河觅屋又没有蚊子,大门口泊着渔船,自己挑拣新鲜的鱼虾,果园到处都是,只管采着吃,我们听得津津垂涎,恨不得马上就搬去;后来看他们只是说不动,耳朵都起了腻,也就淡然置之了。其实呢,他何尝想冤咱们、他的一生时时结想,处处流连,半成虚愿,在旁人看来未见得不是傻罢;但在我如何能存这个念头,你们原谅我,我是不能够的。
他的壮年有能吏之称,而一近暮年思路日窄,执着日深,于人情物理的洞达渐不如前了,我又何必替他深讳。他一也和其他的老人一般的怀想从前,步观现在,不放心他的儿女,尤其不放心他的小儿子,觉世路风波之可畏,愁孩子们入世的艰难,下但艰难而且危险,寸积铢累,节省区区娱老之资,望其可以坐大,为儿孙们百年的基业。我从小就跟着他顽耍,十一余年中他兴致一直是那样好,惟独最后这两年以来,简直忧煎倍急,意绪萧寥,即有时还带着我们游山玩水,吃吃小馆子,我看他尽有点儿勉强。本来一个人一过中年,筋力衰颓,无复有回翔的勇气,再看看婴婴宛宛的姑娘,跳跳钻钻的小子,后顾茫茫,如何放心得下,积想既久,自成痴执:我当时嘴里虽不说,心中也不以为然,觉得“这又何必呢”。今日追思绝非恕道,对于平昔所爱敬的尤非所宜,但已觉无从忏悔了。青山黄壤之间,他撇下我们悄然白去。一晃好几个年头,姑娘新添了小子,小子快要娶人家的姑娘,还是好好过着日子,各人头上一方天,足见他的过虑真真只是过虑,而我们当日背后头的风凉话总算一说一个着。所不同的,我的忆中从此添了茕茕的默想和那恻恻的痛伤,虽说年光逝水早已磨洗了带血的创痕,而这依稀的痕迹殆将数十年如一日,轻易碰不得,碰了它若有隐痛,例如今天我写完这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