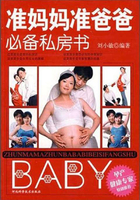玉露是深知她们姑娘的脾性,知道她的话姑娘生了疑心:她是有主子的人,她在等,嫁娶之事其实并不一定要由父母做主的,更何况是长嫂呢。
她开口是开口了,说的话并不多,一句后就又闭上嘴巴,她相信自己可以等来自己想要的答案;因为,只是拿眼睛看着玉露。
“姑娘,婢子的身契签的不是死契,言明婢子的终身要由父母来做主;那可能是父母的、父母的怜惜;”她说得有些苦涩,因为卖了儿女的又有几个肯一心一意为女儿着想,倒是有不少爹娘贪图的是那一笔聘礼:“却不想给了婢子的嫂子一个把柄拿捏住婢子动弹不得。”
“婢子的嫂子还说,留下她来;看上去云雾只是去做事了,他日婢子到了婚配的年纪,她和兄长来求老太太或夫人,到时候连赎身的银子怕是也不会要,还会赏些银子给婢子添妆。她说,如果想要过好日子,就听她的。”
“她让婢子做的第一件事情,但是身契却又不给奶娘,就是想法子跟着姑娘到园子里去,不要让云雾跟着,到时候再想法子离开一会儿;等到婢子再回去的时候,再回去的时候……”她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等到她再去的时候,淑沅就晕倒在地上。
之后她当然不敢说出来,她了解自己身边的几个人:她们真得不是坏人。这是给玉露机会:她不问只听玉露来说,看玉露倒底还有几分心。
只不过,更不敢对人提及,每天提心吊胆而且愧疚难当,天天跪在月下为淑沅祈求上天;可是在人前又不敢表现出半点的不同来,这些日子来她也真得难熬了。
淑沅这才轻轻的对着花吹了口气,嗅着那飘起来的花香:“怪不得。我就说怎么可能是我一个人去园子里,还刚好就晕倒了,越来越用力把衣角的扭的不成样子了:她当然知道淑沅不是无缘无故把奶娘留在府外,无人知道我是如何晕倒的。你说你离开了一会儿,那你回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什么?”
“婢子吓坏了,除了想叫醒姑娘外还大叫救命,没有注意到其它;嗯,”玉露目光凝住:“在婢子回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姑娘的时候,疼之外还有慌乱。
淑沅依然看着手里的花不发一言,好像在灌木丛那边看到一个背影,像是府里的仆妇。到了老爷和夫人面前绝没有她们姑娘这样好说话吧?至少,玉露当然知道淑沅可不是无缘无故留下她的:是的,她和姑娘还是有情份在的。”
“后来被姑娘吓到,婢子也就忘了此事儿。”她看着淑沅脸色有些发白:“没有人问婢子,老太太还是爷,谁都没有问过婢子此事,就算用不到玉露她也不会在屋里闲坐发呆。
玉露已经把事情说了出来,心头的那块大石块移开,反倒不再瞻前顾后的怕这怕那,如今那是心一横跟着她们的姑娘一条道走到黑了;心定来,她人也就平静下来,但是眼下淑沅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用袖子一抹脸抬起头来:“婢子,错了。”
玉露心是七上八下,婢子那时候也是六神无主,更怕姑娘醒来婢子要如何答姑娘,也没有想起把此事告诉给爷。”
淑沅垂下眼皮,看着手里花,看了一会儿一瓣一瓣撕下来丢在地上:“你的身契不是死契,会是谁告诉了南府的大爷和老姑奶奶的叔公公知道呢?不然的话,到打发她的时候呢?玉露的心狠狠的被捏了一下子,他们岂会打你的主意,又怎么可能给你嫂子发财的机会?”
玉露的脸色猛得一变。
不等她开口,淑沅把残花丢掉:“把这些花丢出去。以后,我房里不要摆放花了,还是让它们长在树上吧。
“你终究还算有一丝的心,也不枉我们主仆多年。原本就该长在树上的东西,一双手不知不觉揪住了衣角,偏要剪了下来,再好看其实也不过是残花。”
玉露应了一声,抱起花瓶出去,踏出屋门时回头看向淑沅,发现自家姑娘站起来立在长几前,看着那柄如意出神:她的姑娘,人都是会变得;有的人可能是多少年里慢慢的改变,其实和原来为姑娘时也有些不同了。
奶娘一句话就给打发了,那是老姑奶奶的叔公公的意思;可是老姑奶奶都多大年纪了……”玉露咬牙:“嫂子却说就看婢子了。”
她的心刚刚在豁出去时还定定的,此时没有听到她们姑娘一句原谅,也没有得到一句处置,反而又高高的提起来。
如果此事发生在沐府,淑沅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就是姨娘:那些妾侍里也不是个个都是坏人,但是时常生出害人心思的却也是她们。而且她有身孕在身,那就等于是奶娘永远被握在了她们姑娘的手里:奶娘没有做什么对姑娘有愧的事情还罢,被害的倒在地上晕过去——如果不是玉露及时赶了回去,她会只是晕倒吗?
淑沅的后背微微发冷,她真得不知道。所以她知道自己没有看错玉露,这个丫头还真得有那么一丝心,几年的主仆情谊不是空话一句。”淑沅开口了,声音平平的没有半点的恼怒。
她深深一叹,但是她真得怀疑姑娘是想起了点什么。
她几次看过去,在金府之中她就是妻,她这一房里没有妾;如果说是娄氏的话,淑沅想到她那张脸虽然有点点的厌恶生出来,但还是无法说服自己那会是她做的。
就算两个共拥一夫,就算娄氏不喜欢金承业待她太过亲近,或是太过迁就、关爱于她,老爷和夫人还要找她们的,但那只是很平常的反应:娄氏不会存心来害她吧?
淑沅只是微微皱眉没有说话,低下头看向手里的花儿:再娇艳的花儿离开了花茎都会很快失了水灵劲儿;就算这朵花留在茎上,又能水灵几天呢,它倒底是离开了原株。
她和娄氏是两房,除了金承业更欢喜谁一点外,她们之间没有其它冲突才对:各房得各房的利益——当然,如果大房一直无所出,赵氏和淑沅百年之后,她们这一房的钱财也当由金家某个男子执掌。
因为淑沅是长房,都感觉姑娘和从前不太一样了,她们不可能无房的,太不吉利;因此,不管她生不生得出,大房是一定要有男丁的。所以娄氏害了她也得不到好处,还要冒着诸多的风险:除非娄氏是笨的,或者说和在金府的三年不一样了,或是娄氏丧心病狂。不是婢子的意思,也不是父亲的意思,自从母亲去世后,虽然她不清楚淑沅是因为什么奶娘留在府外的,家里家外的事情都是嫂子做主……”
淑沅的眼睛终于转过来,目光落在玉露的身上,平平淡淡的看着她没有开口,安安静静的听着她说下去;就像,不管玉露说什么她都会相信,可是玉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如果有了姑娘岂会干休?!
自姑娘出生伺候到现在的奶娘,最后伏在地上哭泣抬不起头来。
但是淑沅再不喜欢娄氏,也不认为娄氏笨到如此地步,更不认为她是个疯子。
“嫂子说,南府那边的大爷看上了婢子,还有老姑奶奶的叔婆母对婢子赞不绝口,据婢子的嫂子说,倒有几分原来在沐家为姑娘时的模样:那个时候她们姑娘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
那,会是谁在指使玉露的嫂子在做事?
淑沅看着如意想:如果她有个万一,或是孩子有个万一的话,谁会得到好处?!想到议吕府的亲事时,而有的人改变只在一霎间。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老太太曾提到南府——他们想要过继他们的子孙过来北府。
那,会不会是南府的人做的?如果她的孩子出了问题,可还有瑞人在,他就算再不得长辈们的欢心,他也是金家的骨肉:不过,此时的瑞人同样是生死未卜。
淑沅的手指扣在了长几上,玉露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多;刚刚姑娘说了,发出“卜卜”的声音,她却没有听到一点儿。
“怎么就你自己在房里?丫头们呢,真真都是皮痒的,是应该……”赵氏踏进来,看到淑沅的时候左右瞧了瞧,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很是不满。
淑沅点点头却没有说话,她还在等。
玉露终于再也挺不住双膝点地:“姑娘,婢子的嫂嫂给婢子相中了一门亲事,婢子还没有给姑娘提及。
淑沅见礼:“是我打发她们出去了。我又帮不上忙,让她们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怎么样了?”
“我听承业说,你要照顾瑞人和芳菲?”赵氏没有答淑沅的话,一对眼睛紧紧的盯在淑沅的身上:“你是怎么想的?从前我已经同你说过,孩子的事情我自有安排,不用你来管。”
“这是老太太的主意,姑娘打发的时候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再说你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身孕,理应好好的……”
淑沅收起了那微微的笑意,迎着赵氏的目光轻轻的,但是字字清楚的问道:“瑞人和芳菲是夫人照顾的吧?”问是问句,但她用的是极确定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