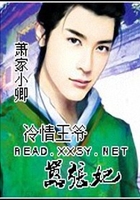他这人四肢非常发达。说到耐力和自足,他是松树和岩石的表兄弟。我曾问过他,白天干那么多活,难道晚上不累吗;他带着诚恳而认真的表情回答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辈子还没觉得累过呢。”但他的头脑很简单,简直和婴儿差不多。他只受过简单而无效的教育,就是那种天主教神父向土著提供的教育;这种方式教出来的学生没有自主性,只学会信任和敬畏;它并没有把学生从孩子变成大人,而是让他们永远是孩子。大自然赐给他强壮的身体和知足乐观的心态,并让他方方面面都很可靠和值得尊敬,所以他就算活到七十岁,也可能还是像个孩子。他非常率真,而且不通世故,所以你都不知道怎么向别人介绍他,就好像你无法向邻居介绍一只土拨鼠那样。别人只能像你这样亲自去了解他。他完全与世无争。人们花钱请他做事情,其实也算是帮他谋得温饱;但他从来不跟他们交换想法。他这人非常淳朴,天生就很谦卑——如果胸无大志也可以被称为谦卑的话;他这种谦卑是浑然天成的,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聪明人在他看来就是半个神。但如果你跟他说有个聪明人就要来了,他会满不在乎的,仿佛任何如此重大的事情都与他无关,所以那人再聪明,也就让他去吧。他从未听见赞扬的声音。他特别尊敬作家和传教士。他们的成就简直是奇迹。我曾跟他说我写的东西相当多,他思考了很久,以为我说的只是写字,因为他本人也写得一笔好字。有些时候,我看见公路边雪地上有人很工整地写着他的故乡的名字,还标出了正确的法语重音符号,那我就知道他刚从那边走过。我问过他是否希望把他的想法写下来。他说他以前帮几个不认字的人读过和写过信,但从未试图写下自己的想法——不会的,他做不到,他不知道最先该写些什么,那会要了他的命,更何况同时还要注意别写错字!
我听说有位杰出的智者与维新者[519]曾问他是否希望这个世界得到改变;他根本就没想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感到很意外,哈哈大笑起来,用带着加拿大口音的英语回答说:“不想,我非常喜欢它。”哲学家要是跟他打交道,应该能够得到许多启发。在陌生人看来,他显得一无所知;然而我有时候却觉得他仿佛变了个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聪明得如同莎士比亚,还是无知得像一个儿童,不知道他到底是充满诗意的名士,还是愚笨鲁钝的蠢人。镇上有个同乡[520]跟我说过,某天他碰到这加拿大人戴着那顶尺寸偏小的帽子在镇区流连,边走边吹着口哨,竟然觉得他像是个落魄的王子。
他仅有的书是一部黄历和一本算术书,对算术他是相当精通的。前者在他看来等于是百科全书,他认为那部黄历囊括了人类知识的精华,实际上倒也可以这么说。我喜欢把当今各种新现象说给他听,而他总是能够用最朴素、最实用的眼光来看待那些现象。没有工厂会影响他的生活吗?我问。他穿的衣服都是手工纺织的佛蒙特灰布外套,他说,穿着感觉很好。他可以不喝茶和咖啡吗?这个国家出产的饮料,除了水还有别的吗?他曾经把铁杉[521]的树叶泡在水里喝,他觉得天气炎热时,喝那个比喝水要好。我又问他没有钱行不行,他向我说明有钱是多么的便利,虽然用的语言很朴素,然而切中肯綮,简直就像是对货币制度和货币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522]进行了最深奥的哲学探讨。假设他的财产是一头牛,而他想要得到商店里的针线,如果每次只把这头牛的等值部分拿去抵押,那非但不方便,而且也不可行。他比哲学家更擅长为各种制度辩护,因为他会描述那些制度和他有什么利害关系,从而点明了它们得以风行的真实原因,而且他从不凭空捏造其他理由。又有一次,他听说柏拉图对人的定义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523],后来有个人拔掉公鸡的毛,将其称为柏拉图的人,然后他认为两者膝盖的灵活程度不同,这是很重要的区别。他有时候会大声说:“我好喜欢聊天啊!天啊,我可以聊一整天!”我曾问他[524],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今年夏天他是否有了新的见解。“天啊,”他说,“像我这么忙的人,不把原有的想法忘记就不错啦。要是和你一起锄草的人想比赛谁锄的草多,那你就没有办法想别的啦,你只能想着那些草。”在这样的场合,他有时会先问我有没有进步。在某个冬日[525],我问他是否总是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想要从内心找到某样东西来取代外界的牧师,找到更为崇高的生活目标。“这怎么说呢,”他说,“有些人满意这样东西,有些人满意那样东西。如果有人拥有得足够多,他也许会满意地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光顾着烤火取暖吧!”然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让他从精神层面去看待各种事物;他看一样东西的好坏,最高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方便合用,这跟动物没什么区别;其实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指出他的生活方式尚有可以改进之处,他也丝毫不感到懊悔,只是说那已经太迟。不过他很诚实,人品绝对没有问题。
其实他也有些独到的见解,虽然并不多;我偶尔能发现他正在自主地思考,表达他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种我随时愿意走上十英里的路去观察的罕见现象,因为那等于去观察许多社会制度的起源。尽管不愿意或者是没有能力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总是隐藏着一些可堪玩味的想法。然而他的思想太过原始,和他的动物生活关系太过密切,所以虽然比博学之士的观点有更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却始终停留在幼稚的阶段,不值得大书特书。他让我们明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虽然是那么卑贱与无知,却可能是生具异禀的天才,他们总是有独到的见解,从未不懂装懂;尽管他们的外表很可能是肮脏邋遢的,他们的思想却像瓦尔登湖般深不可测[526]。
许多游客专程绕路来看我和木屋内的境况,借口说想要跟我讨杯水喝。我指着湖那边,跟他们说我喝湖里的水,并把水瓢借给他们[527]。我住得虽远,却也逃不开踏青的游人,我觉得每年到了四月,好像全部人都出来春游了。尽管来找我的颇有些稀奇古怪的人,但我也算是走运的。有些访客是来自救济院[528]或者其他地方的笨人;但我努力让他们发挥他们所有的才智,让他们畅所欲言;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谈到人的智力;我从中明白了不少道理。我发现他们有些人其实比镇上那些所谓管理穷人的官员聪明多了,我认为应该请他们去当官才对。说到人的智力,我了解到笨人和智者的区别并不大。特别是那天,有个性格和善、头脑简单的穷汉来找我,我常常看到他和其他人被请去放牛,像篱笆的木桩般站在田野上,或者坐在木桶上,管住牛群不要乱走。他说他希望过上我这样的生活。他带着极其朴素和真诚的态度,不卑不亢地跟我说,他“在智力上有所欠缺”。这是他的原话。上帝把他造成这样,他却认为上帝待他也不比待别人薄。“我一直很笨,”他说,“从小就是这样;我并不聪明;我和别的小孩不同;我的脑袋不好使。这大概是上帝的旨意吧,我觉得。”他的人活生生地证实了这番话。对我来说,他是个形而上的谜团。我很少遇到如此坦诚的人——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如此的简单、诚恳和真实。实际上,他表现得越谦卑,就显得越高贵。[529]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明智策略所产生的后果。若是在这个可怜的愚笨穷汉所奠定的坦诚基础上交往,我们可能会得到某种更好的、和智者交往所得不到的东西。
有些来找我的客人通常并不被归入镇上的可怜人之列,但他们其实也算的;反正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些访客期望的并非你的热情招待,而是你的急公好义;他们急切地想要得到帮助,而且在开口求你之前,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要自己帮助自己。我要求客人即使有全世界最好的胃口,也别饿着肚子来看我。客人不是慈善的对象。有些人不知道他们的来访已经结束,虽然我又忙起手头的事情,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也越来越漫不经心。几乎各种智力水平的人都在迁徙的季节[530]来找我。有些人其实很聪明,却不懂发挥他们的才智;比如说那些从南方种植园逃亡的奴隶[531],他们时不时竖起耳朵,就像寓言故事中的狐狸[532],好像有猎犬狂吠着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很可怜,好像在说:
“基督徒啊,你会把我押回去吗?”[533]
其实我曾经帮助一个真正的奴隶向着北极星逃跑[534]。有的人只有一个想法,那就像只生了一只小鸡的母鸡,或者只生了一只小鸭的母鸭。有的人有上千种想法,心中千头万绪,就像那些要照顾一百只小鸡的母鸡,所有的小鸡都在追逐着虫子,每天早晨都有二十只不见了,结果搞得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还有些人想法很多,但光说不练,实在是令人敬而远之。有个人建议我弄一本签到簿,让每个来访的客人写下他们的名字,就像在白山那样[535];但幸亏我的记性很好,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来的客人身上颇有些鲜明的特点。女孩、男孩和年轻妇女通常很高兴到森林里来。他们看看瓦尔登湖,又看看各种花儿,过得很快乐。至于做生意的人,甚至包括农夫,则觉得这里太过孤寂,他们只惦记着自己的工作,认为我住的地方实在是太过偏远;他们嘴上说很喜欢偶尔到树林里漫步,但实际上并不。有些客人整天忙个不停,他们的时间不是用于赚钱谋生,就是用于维护已经拥有的生活;教堂的牧师也来过,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谈论上帝,完全听不进别的意见;还有医生、律师,以及不安分的家庭主妇——她们肯定趁我不在家偷偷翻看了我的储物柜和床铺,不然的话某某太太怎么会知道我的床单没她的干净呢?客人中还有几个不再年轻的年轻人,他们终于还是认为踏上前人走过的职业之路是最安全的。这些访客普遍都不是很看好我在这里的生活。唉,这就是问题所在啊![536]那些软弱和胆小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想得最多的是生病、突发的事故和死亡;在他们看来,生活充满了危险——其实如果你不去想,哪里有什么危险呢?他们认为谨慎的人应该仔细挑选,生活在最安全的地方,随时能请某位医生[537]过来看病的地方。对他们而言,康科德镇是如假包换的共同体,是相互保护的联盟,他们甚至连去采浆果都要带上药箱呢。实际上,人只要活着,就难免会有死亡的危险,不过如果他是个活死人,那么这种危险肯定会大大降低。一个人坐在家里可能遇到的危险,跟在外面跑是一样多的。最后还有些自命不凡的改革者[538],是所有访客中最无聊的,他们以为我总是在唱着:
这就是我建造的房屋[539];
这就是住在我建造的房屋里的人;
但他们并不知道下面两句歌词是:
住在我建造的房屋里的人
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烦了。
我并不害怕骚扰母鸡的白尾鹞[540],我害怕的是那些骚扰我的来客。
幸好除了最后这种人,还有其他让我心情大好的访客。比如说前来采浆果的儿童,在星期天早晨穿着整洁的衬衣来散步的铁路工人,渔夫和猎人,诗人和哲学家,总之都是些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到森林里来寻找自由,真正地将康科德镇抛诸脑后。我很乐意这样招呼他们:“欢迎你们,英国人!欢迎你们,英国人!”[541]因为我和这类人有共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