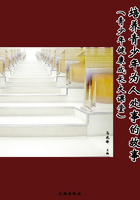我躺在床上,听见妈妈细声细气地对连安说,菜做好了,酒在这里,你自己吃吧。妈妈这样说时,解下围裙,擦干手。她消瘦而清秀,动作很慢,半低的头,欲言又止的样子。
连安好像没听见一样。他窝在沙发的一角,两眼直直地望着电视。
别只看电视。儿子在那边,注意看着点。妈妈一边穿衣服,一边叮咛着。
别唠叨了,听见了。连安很不耐烦。妈妈不急也不恼,只是无可奈何地笑笑。推开门,冷风像妖精一样钻进来,妈妈急忙回身关好门,然后小心地扶着栏杆走下旋转楼梯,踩着积雪向教堂走去。
连安是我爸爸,我是他们生病的儿子。我出生的时候,宫
内窒息,后果是直接影响了我的四肢和语言。我躺在那里,所有看见我的人都投来怜悯的目光。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在我内心,有一种超能力,我的灵魂可以飘升起来,跟随他们的行动。上帝是公平的,我不能行走,但我的灵魂可以飞翔。
这是一年一度的圣诞前夜。教堂里满是来祈祷的人。我的灵魂跟随妈妈进了教堂,选了一个靠门边的位置。双膝跪下的一刹那,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弯下腰,低垂着头,极力忍住滚滚而来的呜咽,眼泪却不管她严密的堤岸,只管纵横驰骋,片刻就流满一脸。
电视里正在演《小鬼当家》,连安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年年的圣诞电影,都是老掉牙的一套。开始他还能听到儿子呼噜呼噜的喘息声,后来就安静下来,大概是睡着了。连安站起来,看到桌上切得薄薄的酱牛肉,花生米和红星二锅头,想吃的欲望立刻灌满了口腔。尝一口,不出意料地滋味寡淡,连安叹口气,做菜的滋味就是做人的滋味呀。他叹息道。然后不情不愿地站起来,在橱柜里乱翻一气,找出生抽老抽一大堆,给菜浇上浓浓的调料。
连安正吃得兴起时,电话响了。电话里的女人说,安,你怎么还不回来?连安说,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今晚秀兰去
教堂,我在这里看孩子。那边的女人就委屈说,今天是圣诞夜,你好忍心,也不想想我们母子俩怎么过。连安说这也是没办法嘛。你们先过着,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女人又说,她也真是,圣诞夜还出门,你不是说她是好妈妈吗?连安有点不耐烦,他说秀兰是教徒,这对她很重要。那边的女人又说,你不是都跟她说明白了吗?她为什么还总找你?连安捏着酒杯的手有点不高兴,啪的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说,我们是有孩子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声音里就带了气。那边的女人噤了口,半晌说,那你快点儿回来,我们等你啊。连安应了一声,重拿起刚才那只酒杯,兀自端在手里,愣了一会儿神,才喝了一口。
我睡在床上,耳边却能听见那个越南女人呢喃的英语。连安喜欢这样会撒娇的女人。他曾说过,秀兰,虽然质地好,却是一架哑琴。你说十句话她都不回一句,跟这样的女人怎么交流?没法儿交流。怎么过日子?没法儿过日子。
弥撒做完时,妈妈站起来,教堂里的人们开始相互拥抱,问候圣诞快乐。妈妈刚要走,见素素远远地向她招手,就停住脚步等着。素素问她近来还好,秀兰就说还好吧。声音里带着沉重。素素说相信主,多多保重,我会为你祈祷。妈妈谢了素素,打开门,见皮埃尔老爹站在那里。兰,我有礼物送给你,他一头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着,手里拿着一个精美的小盒子。妈妈打开盒子,见里面装着12只水晶一样的玻璃珠子,是挂在圣诞树上的装饰品。珠子晶莹剔透,妈妈的脸就映在上面。谢谢你,老爹。
素素的丈夫带着孩子等在那里,妈妈望着素素一家远去的背影,痴痴地站了好久。
妈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突然她站在雪地上。我看到一种强烈的愿望占据了她的内心,她不再想回家了。这种思想是那么的强烈,让她一时不能动弹。她站在雪地里,使劲儿地摇头,想把这种想法赶出去,这想法却那么顽强地矗立在她的头脑里,像百年大石一样不肯动摇。妈妈站在雪花纷飞之中,与自己较量了好久,终于败下阵来,她无助地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望着漫天大雪发呆。
为了这段婚姻,妈妈绝望过。最早知道丈夫有了别的女人,妈妈曾问过连安,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妈妈圆润的脸庞在一夜之间憔悴不堪。
因为我可怜她,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总打她。连安这样回答说。
那我呢?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妈妈又问道。
连安不回答,只是别过脸去。
妈妈不再追问。妈妈的嘴唇颤抖着,心里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来。妈妈是一部哑琴,连安说的不错。我真为妈妈着急。妈妈,你不说,是因为你口拙,还是你不忍心说?
妈妈知道,连安说的不是真心话,至少不全是真心话。
那段时间,连安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之间跑长途,经常两边住着。后来回来得越来越少,后来就有了那个女人。连安每次回来,照例给妈妈留下生活费,照例睡在妈妈的床上。除了有个遥远的女人,妈妈的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只是丈夫曾向她坦白的那个女人,像蛀虫一样撕咬她的心。
孤枕难眠的时候,妈妈趴在电脑上,顺着丈夫的QQ号和MSN一直找过去,她终于找到丈夫的电子邮件。她找到那陌生却与她息息相关的女人,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的照片传了出去。
这次连安回来得快,一进家门,就说,你不要骚扰她,再骚扰我就和你离婚。
连安酒到半醺时,窗外的雪也下得正大。狂风裹着雪花,让连安想起“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诗句。我惊讶地看到连安突然热泪盈眶。几年来艰难的生活,他身心疲惫。也曾“斗酒诗百篇”,也曾“长安市上酒家眠”,或者就是“一夜踏遍洛阳花”吧!但那只是少年轻狂。青春的理想,在卡车的碾压下,变成了一片粉碎,粉碎之后的碎片在阳光中闪烁,只是徒增了空枉的嘲笑而已。连安这样想着,就在半醉中举起酒杯。向着射顶灯投下的阴影,他看到自己像一只被放大的大熊,在光影中改变着形状。窗外的雪花飘舞着,大熊张牙舞爪,大熊左摇右摆,大熊穷凶极恶。然后,大熊突然停止了行动,呆呆地站在那里。落地窗映出大熊的脸,大熊的脸突然走了形状。他抬起短短的上臂,抹了一把脸,才感到脸上湿漉漉的。
电话又响的时候,连安听到电话里的声音变了。沙丽带着哭腔:“安,求你,回来吧!”沙丽说,我和微微安很害怕,很孤独,你让我心里好难受。连安说你让我怎么回?秀兰不在,孩子怎么办?沙丽说,安,你知道,在这样的雪天我很害怕,后院的门一直在响,我都不敢去关,四周都没有人。风声叫得像鬼一样。
连安说那我带儿子回去。沙丽说不要,你放他在家,行吗?他不会动,没有危险的。再说,秀兰也快回来了,你只要早点回来,我就心安了,求你,安。
连安的心,在沙丽的请求中,泡得软软的。连安进了卧房,见儿子歪着头,睡得正香。也许是酒精的原因,连安突然有了一种冲动。尽管从儿子一生下来,他就不喜欢他,或者还嫌弃他,怎么办呢?对一个不会说话也不会动的孩子,连安的心里有一种恐惧和挥之不去的不安。
而今天,连安醉了。有时酒真的是个好东西,有了酒,你就放松了神经,放松的神经就让你随心所欲,甚至为所欲为。今天连安喝了酒,今天秀兰不在家,今天是圣诞夜,钟声敲响的时候,你应该拥抱和亲吻在你身边离你最近的第一个人——
连安弯下腰,好像做贼一样,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嘴唇放在儿子的脸上——那是柔软如丝的温暖,那是花朵,那是蓓蕾,那是心灵中湖水一样温润的地方。连安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我紧闭着眼睛不敢张开。连安趴在我的床前,哭得像一只大熊,他呜呜咽咽地说,儿子,你知道吗?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和你对视,因为我知道我对不起你。那天我为什么不早一点醒来,把你送到医院,也许你就不会这样了。可是那一夜我实在太累了,我对不起你啊,儿子。
我不能回答。我不能告诉他,其实他不用这样自责。我有我的快乐和能力。我的目光在他开始秃顶的头上抚摸,希望这样能让他好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