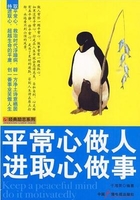慢慢的,全身的肌肉在逐渐紧缩,似乎绷成了一根直线,好像拉伤了的感觉,但又感觉不到痛。铅块已经吞噬了大部分鲜活的血液,它们好像都已经坏死了。此刻我就像是一个由铁丝和石块组成的建筑。视觉系统还很完好,除了远一点的东西看不清之外,接收图像没什么大问题,像是建筑物的监视器。我转动着眼球,看到的景象仅限于天花板和稍微下面一点的墙壁,此外就是从眼角跑过来的路灯光。我终于能体会到《潜水钟与蝴蝶》中隐藏的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但和作者比起来我还算幸运,我可以眨的是两只眼睛,如果再努点力,说不定手还能稍微移一移。
大脑也是运转着的,我想沉下心来好好想想过去的一切,但死亡化作了一个可怕的幻影,和弗吉尼亚的影像在脑海里交替出现,所有的思绪都被这堵墙挡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点遥远的喧闹声让我从半醒半睡的状态里回过神来,声音有点像平日里邻居家养的狗的叫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还混杂了奔跑的回声。我可能睡了几个小时,又可能一直在盯着天花板发呆,好像时间是一件和我无关的物件。喧闹声越来越大,伴随着光脚踏在地板上发出的冰凉的吧嗒声,我听出来好像有人进了家门。我还分辨出,有好几只脚疾走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听起来好像不止一个人。
所有声音都很遥远,好像这些声音是从好几栋房子之外传过来的,但直觉告诉我声音的发源地是在我家。会是谁呢?我半睁着眼,十分虚弱地想,天花板上的光影像烛光一样摇摆不定。我首先否定了弗吉尼亚,她只会在我的幻想中出现。最有可能是菲利普,我已经把罪犯的身份锁定在了他身上,但是我找不到证据,也找不出弗吉尼亚,如果给我的时间再多一点,说不定就能真相大白。夜长梦多,所以菲利普在最后时刻都不放过我。他要杀我也好,要重新把我关起来也好,我都不关心了。唯一的使命没有完成,那就让我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吧。
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我条件反射式的怔了一下,我差点就真的以为是家里的某个地方发生了爆炸。我努力把视线压低,朝门的方向看去,然而头不能转动,我怎么也看不到那里。过了几秒,发现屋子里没有被损坏的迹象,我才反应过来是卧室的门被撞开了。进来时我没锁门,为什么不好好开门呢?回想起刚才振聋发聩的响声,我闭上眼暗暗抱怨,那个声音只有两种产生的途径,用力一次性把门踹开,或是侧过身,用肩膀猛地撞开。考虑到来的人可能脱了鞋子,也许他是用肩膀撞开的。
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把我压住了。这次不是铅块了,压着我的东西不重,隐约中我还感觉到了一丝温热。有那么一切都停滞的几秒钟的时间,短暂的时间静止后,气味开始像缓慢生长的藤蔓植物深入我的鼻腔。一股香水味,如果是别的香水味我一定会皱起眉头,但这是一种我熟悉的味道,香味很淡但扎根很深。我的脸被一双手抓住了,我能感到纤细却又有沟壑般的皱纹的手指从两颊滑过,好像是被捧在手里似的。与此同时,一股直直的炙热又湿润的目光穿透了我的脸庞,这时我才像刚从睡梦中醒来时痛苦地睁开了眼。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看向哪儿,我被那股目光引导着望向力量的发源地。
是弗吉尼亚。她的脸占满了我的整个视野范围,正对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了一起。借着外面影影绰绰的灯光,熟悉的线条让我莫名的感动。弗吉尼亚看上去也很激动,她的眼眶红红的,咬着嘴唇,身子在微微抖动。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直在盯着对方看,没有说话。她像是做了某件错事似的沉默着,努力压低自己的抽泣;我和她不同,我的沉默则包含着一种幸福的宁静,如果把时间往前推移,现在的情形只可能是我做的梦。我在观察弗吉尼亚,我想知道,现在的她和我熟悉的弗吉尼亚有什么不同。如果现在只是个梦境,那么我一眼就能觉察出来。我们一起沉入寂静之中,时间在那个时刻仿佛被无限地拉长,几分钟的时长似乎被赋予了永恒的力量。我欣喜地注意到,弗吉尼亚的脸色一如既往的苍白,仿佛包裹在晶莹的冰块中,连脸上细微的茸毛也和原来一模一样,好像她是从几天前直接穿越时空来到现在的。仔细看了一会儿,弗吉尼亚的脸色和以往还是稍有不同,这增加了眼前这个弗吉尼亚的真实感,如果弗吉尼亚真是和原来没有差别,那我才可能是在做梦。她的苍白脸色里混入了几分疲惫,这种疲惫,只有在背负巨大的工作压力或者为要事不停奔波时才可能产生。时光顿时回到五年前,当我们结束了伦敦之旅后,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从身旁熟睡的弗吉尼亚脸上看到了同样混杂了疲倦的苍白。我也很累,但那时候我们都被幸福所包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瑕疵。除去忧伤的神情,现在的弗吉尼亚和那时有着同样的疲惫,她一定是匆匆忙忙地赶去了哪里,又赶了回来。去了哪里呢?梦想实现的畅快和满足感消失后,又一个疑问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但我的思绪被扰乱了,关于弗吉尼亚离家之后的所有细节,我打算都把它们给问清楚。
然而,我痛苦地发现,我不能说话了。嘴巴能张开,能闭合,能像正常的嘴巴一样做出各种造型,但就是不能发声,一丝声音也挤不出来,除了上下嘴唇不断碰撞发出的声音。一般的失声,大多是声带损坏了,但也顶多是声音沙哑而已,休息几天就好,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丧失了某些声带的功能,但日常的交谈还是能应付过去的。总而言之,再严重的声带损坏,其患者都能够说话,也许音色不够好或者声音不够大,但总能够和人交流。我不断地张口闭口,想按照平日里说话的节奏和弗吉尼亚说说话,但结果只有一片寂静回荡在我的耳中。我像一个先天性聋哑人一般,在急切的时候嘴巴不断开合,好像这样就能赋予它说话的能力似的。有一会儿,我甚至都把自己当成了一名聋哑人来对待,尽管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我的听力正常,声带也完好无损。在试图说话的时候,我还想抬起手臂朝弗吉尼亚比划一番,但没能成功,我忘了我无法动弹,好似瘫痪一般。
要追溯我失声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除了癌症扩散造成的并发症,我想不出其他原因。既然是并发症,也许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都不能再开口说话了。当然,我也不能再站起身来,挥动我的手臂,给弗吉尼亚一个拥抱了。人就是这样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生物,我已经见到了弗吉尼亚,还能有什么遗憾呢?然而此刻,我觉得无法动弹就是我最大的遗憾。
好在我的视觉和听力还是完好如初,于是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场景。我和弗吉尼亚凝神细视了一阵,也许是长时间俯着身体觉得累了,她直起了腰。但她还是看着我,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的眼睛此刻就像是浸在水中的圆润的猫眼石。随后,她背后传来了声音,是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坚硬而冷漠的声响。奇怪的是,皮鞋的声响音色并不统一,我分辨出有两双不同材质的皮鞋在交替踩踏着地板,好像有一双底子比较薄,有一双是厚厚的硬底。弗吉尼亚转过头去,她对背后有声响的反应不大,在我看来,甚至还有点迟钝了。这时候,灯打开了,不知道是不是视觉受到了并发症的影响,原本明晃晃的白炽灯现在竟暗了许多,像是罩了一层黑纱。灯亮起不久,房间里回荡的脚步声越来越强烈,声响在要达到顶峰的时候戛然而止。弗吉尼亚没有把头转过来,她的头茫然无措地扭向一边,似乎来者不是陌生人,而是审判者,他们是来把弗吉尼亚从我身边带走的。
我把视线从弗吉尼亚的身上移开,转动眼球,分别朝两边看去。天花板上发散出来的微弱白光和从外面流泻进来的昏黄的路灯光混合在一起,营造出了一个凄清的氛围。伴随着弗吉尼亚止不住的低声抽泣,不大的卧室里很压抑。周围的变化由模糊变清晰,对我来说,是一个由恐惧到惊讶的过程,在惊讶的最后,甚至还有点狂喜。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在床的左右两边,分别站着两个人,从我听到的声音判断,两人穿着不同的皮鞋。两个惊人的来访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不会想到来者会是他们,弗吉尼亚出现在我眼前已经很不可思议了,他们竟然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布莱克先生站在床的左侧,身穿今天下午拜访他时穿的同一套衣服,两条略显虚弱的腿艰难地撑起肥硕的身躯。菲利普套上了一件棕色的休闲外套,里面是蓝白条纹衬衫,下身则是灰色休闲裤,双手插在裤兜里,斜站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形是个意味深长的布局:布莱克先生和菲利普分列两边,弗吉尼亚位于中间,而我在他们三人的前方。好像他们三人是一方,我是一方,双方敌对。我突然欣喜地恍然大悟:菲利普果然是最终的凶手,他一手策划并实施了弗吉尼亚失踪的事件,其实是把她软禁在了某个地方,我下午空手而归是因为没找到那个软禁弗吉尼亚的地方,是布莱克先生充分发挥了他的智慧,找到了弗吉尼亚,带着凶手菲利普到了我家。一切真相大白,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听布莱克先生述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我的脑袋里浮现出《凡人》淡蓝色的封面,心头泛起模糊的成就感,就像我第一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样,那时还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是做个学者,还是离开学校。正是这本关键的《凡人》,整个事件变得豁然开朗,两条岔路终于汇成了一条大道。
我努力睁大眼睛,瞪着菲利普,想用尖锐的目光刺穿他。但那显然不可能了,因为我极其疲惫,又无法正常入睡。我的眼睛像被人用力挤压一样,有一股外力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连闭眼都不能。菲利普对我的注视没有什么表示,他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眼神又游离到了房间里的其他地方。我扭过头,看向布莱克先生,他的眉头轻轻皱在了一起。我不能说话,我希望他能明白我的意思,赶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遍。虽然还不知道实情,但侦探破案后的自豪感依然在我心中不断滋长,我给这个事件还取了一个名:弗吉尼亚失踪案,或者未婚妻失踪案。我的眼神镀上了一层渴望,快讲实情吧,我急切地想,对我来说,聆听的时间随时可能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