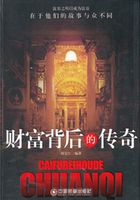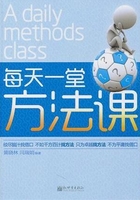坐进了车内,视线顿时暗了许多,但是也给了我一个休息的良机。只可惜我没有休息的机会了,目的地可能很快就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坐车,那天独自去医院时我都没有想过要乘车前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难以解释这个举动。现在我知道了,我坐车前往的决定是在我知道要去哪里之前想好的,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感觉会胜过一切。一进入车内,外界的一切仿佛都和自己无关了,交通拥挤似乎也远离了自己,绿灯在我进车时亮了起来,车子很快就通过了那个闸口般的十字路口。车子里开着电台节目,一个低沉的男音在向众多司机听众传达各条道路的交通状况,很多地方都被车流填满了,还有几处发生了擦挂事件,离这个路口不远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三辆车纠缠在了一起。就在我拧起眉头往车窗外面望时,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听到我前往的那条街道的名字,我就条件反射似的挺直了背,低沉的男声仿佛在我耳边低语,他告诉我那是仅存的交通畅通的道路了。
这唤醒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继续听下去,我不相信市区这么大一块交通区域就只有一条道路是正常运转的,说不定这个沉重但温柔的声音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但是,就在这条消息被他念完没过多久,电台播放着过渡性的舒缓的音乐时,乐声和电台的嘈杂声却戛然而止。司机关掉了电台,他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但这时却把头往我这里一偏,对我说:“听道路有多拥堵完全是自寻烦恼。我又没有边开车边听音乐的习惯,偏偏有些乘客又喜欢听音乐,这让我很为难,真麻烦。”他好像在为自己的举动作辩解。“到处都是烦恼。”我随声附和道,我没有兴趣听电台,我的脑袋里连一丝乐声都没留下,它们像水流般流走了。我的感觉一向很准,这是一个沉默的中年司机,基本上只会专心开车,而不会像一些司机为了解闷,乘客坐进来之后就变成话匣子。如果坐进来时司机在不停的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就会一直喋喋不休,按照这条我总结出来的定律,这位司机会很安静,这也符合我的内心状态。转过了十字路口,视野开阔了许多,又关掉了声音久久回荡在车内的电台,司机这才向我问起了目的地,我带着一种坚决告诉了他,就像告诉对方的是家的所在地一样。他略微点了点头,然后便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驾驶上了。除了一些必要的事情外,他果然没有多说话,这样也有好处,少了讨论天气好坏这样的愚蠢问题,我的思考时间一下子就变得充裕起来,虽然路程不长,但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我没有任何感觉,不知道现在的心情是好是坏,就像有时候对着某个不特定的东西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心情也是一片空白。车行过一个短促的隧道,里面没有灯光。我无意中通过车窗的反射看到了自己,发现自己的眉头又拧作了一团,但是我没有任何物理上和精神上的感觉,仿佛车窗上这个表情不受自己的神经控制似的。
接下来的道路突然变得很畅通,好像所有驾车的人都在同情我的处境。车开得越来越快,时间在一点一点地流逝,我的内心也慢慢焦躁起来,感觉一股绳拧在一起然后卡住了喉咙。为了让自己放松一点,我打破原有的姿势,不再机械地靠在座位上了,手上的动作也骤然多了起来,左手垂放在旁边空着的座位上,而右手则一会放在膝盖上,一会又拉着车窗上方的扶手,事实上车开得很平稳。遭遇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之后,就会对一些身边理所当然的事产生怀疑,为什么我恰好碰上这辆车呢?我稍微想了想,在拥堵的长流中这辆空车碰巧从我身边缓缓经过,我才注意到了它。会不会是有人特意安排成这样?当然,我并不知道。从车里面的情况来看,我完全有理由怀疑车的详细背景,因为一切都太奇怪了,和我遭遇的事情完全同属一个性质。司机少言寡语得可怕,像是得了交流障碍症,让人怀疑他的脑袋有问题,但从他在开车过程中说的仅有的几句话来看,他的智力肯定符合正常人的标准。像是电影里的情节,我竟然认为我在又一个阴谋的控制之下,他们买通了这个司机,让他载着我把车开到他们那里去,或是开到一个荒凉的近郊,在黑暗中解决掉我。就算发生更离奇的事情,这依然是一个荒诞的想法。
不过,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给予我前面那个人充分的信任。借着调整坐姿的后劲,我把身子往前倾了倾,动作不大,但是效果很好。专注的司机一般把注意力放在左右两侧,这样一来也就忽略了后面的乘客,动作再大一些也无妨,我想,但我还是保持着适当的限度。我弯下腰,头自然而然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这样可以隐蔽地窥探到司机的表情,然而范围仅仅是侧面而已。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不在于追求结果如何,只求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好像它是做给大家看的,目的是提醒各位好好看着,我正在提高警惕,但周围一个观众都没有。他的表情冷漠,一双眼角耷拉下来的眼睛盯着前方,眼珠不时转动,以观察左右两边的状况。他盯着前方,我不动声色地盯着他。我的眼睛把他从针刺一般的头发到瘦削的下巴垂直扫描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我准备重新靠在座位上,这样能让自己感觉舒适些,在我身体向后舒展的过程中,我的目光掠过上方的后视镜时,我发现他的目光也刚好停留在后视镜上,于是我们的目光便毫无预兆地产生了交集。我感到了一丝尴尬,他似乎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接下来的时间便只顾前方的路况了。
我去过那地方几次,都是和弗吉尼亚一起去的。那几次里,都是她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她从没让我来开车,每次她都率先握上方向盘,这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想到这里,我又一次感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她太善解人意了,那时候,我内心的忐忑和紧张无疑会使开车成为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线路固定,所以街景在潜意识里变得熟悉起来,我一眼就能辨识出方向和地点,只是叫不上地名。
“朝前面那条路走吗?”司机又开口说话了,实在是令我出乎意料,“电台的话果然信不得。”语气中有一种自嘲。
我缓过神来,往前面看去。司机没做出任何指示性的动作,只是一味地看着前方,但我还是领会了他的意思。正前方是一条中等宽度的道路,车辆不少,有拥堵的趋势,一片红色的尾灯不停闪烁,像是闹市区的霓虹灯。是条老路,我默念道,每次我们都会经过这里。车子距离那条路大概还有几百米,道路还是很畅通,车子正在全速前进。
“对。”长久的沉默让我觉得发音变得更困难了,其中或许也有病痛的原因。
“赶时间吗?”他立刻回答说,更多的是像在提一个有点过分的建议,“前面情况不妙。”
“如果能快点,当然更好。”我本来想说无所谓的,但这时候我脑子正在想别的事情,需要充分调动脑细胞,于是就说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他笑着说:“每个乘客都那么想。”
我的心完全放下了。他虽然话不多,但态度很和善,是个一门心思当司机的人,绝不会想一些旁门左道。见我没答话,他继续说:“我知道有条近路,有点窄,但没多少人知道。从左边那条岔路就可以了。”怕我不相信他的说辞,他腾出一只手指向那个方向。
那条路果然要僻静许多,从路口处就可以看出来。背光,又斜又窄,没人愿意走这样的路。我经过这地方几次,还从没注意过那里,但不管我是否注意到了它,它都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好吧。”我说,及时排除了头脑中的荒诞想法。
车子迅速拐入了岔路口,动作流畅而又平稳,仿佛是按一个流线型的路线滑过去的。光线一瞬间变得很暗,这是我早就料到了的,但如果仔细地看,等到眼睛适应这片昏暗后,窗外的事物还是能看得清楚。路很窄,只能容一辆车经过,但它是单行道,再加上名声太小,道路每时每刻都是畅通无阻的状态。道路两旁满是陈旧的小礼品商店,不时闪过一两家咖啡馆,都是生意惨淡。除此之外,一切都是陌生的东西,也就是说,我能立刻接受的东西也就只能是建筑和道路这一类直观的东西了。对我来说,陌生的东西更能不引起我注意一些,就像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盯着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看,也不会找一位陌生女士搭讪。有了陌生的东西,我能更专注地思考、做事。这样片刻的宁静对我的思考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坏消息是腹部又开始隐隐作痛了,根据我的经验,药效开始减退了,这一阵一阵的疼痛会越来越强烈,这是神经中最极端的痛。等到我再也忍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必须注射第二支吗啡。医生可能会认为我的使用太频繁,然而此时没人会考虑上不上瘾的问题,只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疼痛而送命。
还好,这种程度我还能忍受。它让我想起病灶刚显现出来的时候的痛,那种对意志强硬的人来说如蚊虫叮咬般的痛,丝毫不会引起常人的关注。我像一个病情还处在潜伏期的人一样忽略掉了疼痛,我故意歪着嘴,牵动起来的肌肉分担掉了这部分不适。
姿势又归于呆板,好长时间都不挪动一下。望着外面诡异的旧建筑,我的眼神飘忽不定,车子里好像只剩了我一个人,前面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操控方向盘。我直到现在才陷入思考,也只有真正处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体会到静下心来专注思考的不易。一直以来,我好像都在逃避这样一个时刻,周围降下永恒般的安静,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与这个时刻无关。就像这是在奔赴刑场的车上一样,死去或逃走,现在是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我感到这将是我的最后几步路了,不管怎样,选对方向肯定对我有好处。
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两个方向,我一时还找不到办法来辨识它们。有些人表面上可能和我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解决的过程却要简单许多。同样是两条不同的路,一左一右,分别从主干道分支出去,看上去各自连接着只和自己相关的街道,但事实上到达的是同一个地方,它们的最终归属是同一个方向。我的情况不一样,不止要考虑到选哪条路的问题,还要想到走错方向的后果。这两个方向,一个是按着意外浮现出来的罗斯的这条线索查下去,另一个就是紧咬住菲利普不放。这是寻找弗吉尼亚的方向,也是如今主导我人生轨迹的方向。我很清楚我现在进退两难的境况,着手调查另外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从时间上讲就已经行不通了,我是一个连生命都不能保证的人,时间是一件奢侈的物品。况且线索也不能只靠观察和逻辑推理,它讲求灵感,偶然性占它的很大一部分,就像我纯属偶然地发现菲利普来过我家一样,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不能为了追查一个不清晰的线索把时间托付给偶然性,那样有可能到死我也不会知道真相。罗斯这个人,可以很重要也可以无足轻重,重要在他的身份我一无所知,这样容易引人遐想,而他的不重要也是因为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突然出现会让人觉得蹊跷。一切都还是推测,我只是在凭感觉找准一条方向,碰上无法解释的事情,侥幸心理才是最好的感觉。
菲利普是我最有把握的一条线索,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它能带我发现真相。真相一被发现,那么离弗吉尼亚的现身就不远了,我希望我能在死之前看到她。我不算了解菲利普,不知道他的工作履历,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工作。说实话,这件事情牵扯到他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们也许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对敌人,我们的性格处在对立面,本身就无法兼容。对于自己讨厌的人,应该尽可能的回避才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挑中我,或许这就是命运吧。
要调查菲利普的背景不是难事,去一趟学校就可以了。在放档案的柜子里翻出他的档案,就可以把他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后的经历了解得一清二楚。只是现在我不可能再回学校了,那里的人说不定会接到一个通知,让他们看到我之后就立刻通知某个部门,随便跟他们说个理由就可以敷衍过去,比如我得了重病却不肯接受治疗,现在必须要去医院。我不能冒这个险。另外,档案处也不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据说要有查找的证明,才能在里面查看他人的档案,以免被人用在其他用途上。
我要尽量挖掘自己的人脉,如果文字的资料不能利用,那就只能靠人的关系了。我们同属学校的这个圈子,或者范围更大一点,同属城市中的某个学术圈子,我认识的他肯定认识,了解他的当然不在少数。但问题是,我和那些人的关系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上,和他们称不上是朋友,只能说是互相知道各自的名字,在一些会议和学术活动上打过招呼。我要找这么一个人,他和我的关系不能太疏远,我要有充分的理由去拜访他;他还要和菲利普有较紧密的关系,这样他才能比我更清楚菲利普的为人;只要我说出实情,他一定会无条件地帮助我,甚至会和我像一个探案团队一样坐在一起分析一条条线索。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已经走入了这个方向,无论遇上什么情况,我只能义无反顾地冷静下来,严格遵守定下的计划。吉尔伯特校长是最完美的人选,我告诉自己。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吉尔伯特太老了,思维停滞,口齿不清,和学校相关的人现在都是危险人物,我无法信任他。
我是首先想到了最好的人选,然后才想出来这个办法的。在想出来这个办法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要去见那个人了,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我决定去见布莱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