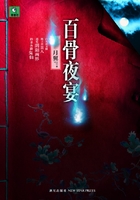我设想过很多种醒来时的情景,其共同点就是我醒来后带着浑浑噩噩的漫无目的。人活在这世上最怕这种感觉,因为一旦活着没有目的,行动的轨道就会发生偏离。杀人、抢劫、绑架,统统都是一念之差,我还忘了一种重要的偏离,那就是自杀。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很早就醒了。外面雨也已经完全停了,天空仿佛被冲刷了一遍似的。我以为虽然只注射了半管,但药效应该还是很强劲,所以一定是玛丽或者菲利普把我叫醒,我也就没有做准备的打算。而醒了之后,我没有浑浑噩噩的混世之感,只觉得身体里充满力量,等待着我去释放。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回荡,今天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虽然才进来没多久,但我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里无比压抑的气氛了。这个时候,整个计划也已经大致成形了,不需要出去侦查,也不需要勾结他人,只需要我在这里静静等待,逃走计划就可能成功。这也是一次危险的行动,稍有不慎,我可能就永远也出不去了,他们会加强安保措施,时刻把我关在这个病房里。
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我要和菲利普独处一室,不能有其他人在场。最完美的情况是没人注意房间里面的动静,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学校和医院现在是合作者,他们没理由怀疑菲利普。就算菲利普身上藏了窃听器,我也不用担心什么,因为菲利普会是我的合作者,他身上有没有窃听装置不重要,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只要没有随行人员,一切都好办。对于没有随行人员这一点我很肯定,菲利普一直都是独来独往,除了出席重要会议,他身边不会有一个人,就连社交场合也是这样的。
因为时候还早,我担心到时玛丽会叫我吃早饭,从而影响计划的进程,于是我决定把玛丽叫来解释情况,告诉她药力还没过,不想吃早饭。
按下了床头处的按钮后,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抬头就看见一个陌生的护士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像幽灵一般,但脸上精致的五官却陌生得让我感到熟悉,仿佛远处传过来的散入空气的乐声。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才发现她是昨天坐在柜台背后发呆的两位护士的其中一个,我当时只是从她们脸上扫过,觉得她们很年轻而已。
她脸上面无表情,探过身子小心谨慎地问我:“先生,哪里不舒服吗?”
年轻的护士总是比经验丰富的老护士更呆板,也更不会拉近和病人间的距离,她的这副表现也会招来病人心里的不满和厌恶。
“其实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我不用吃早饭了,等会儿不用来叫我。玛丽呢?”
“她还没到,她不住在医院里,所以会晚点到。我们是在这里值班的,就住在这层楼。先生,早饭是很重要的,最好按时去吃。”
“昨天晚上我打了镇定剂,现在觉得不舒服,早饭肯定是吃不下了,午饭会吃的。”
“好吧,今天是特殊情况,到时候不叫你了吗?”
“菲利普校长会来看望我,如果玛丽到了,就叫她不用进来了。”
“好的,先生。”她拉上了门。
这样,我就避开了玛丽带来的麻烦,我和菲利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处一室。而玛丽又不会怀疑什么,既然菲利普把我送了进来,他就不会把我放出去,玛丽深知这点,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和菲利普见面,而不必在关键时刻畏手畏脚。我也明白,玛丽虽然不会靠近走廊,但不保证值班护士和守卫就能老老实实坐在大厅里,我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不知道我是个处在这种境况下的绝望的人,也不知道我对他们怀有仇恨,更不知道我有明确的目的,他们恐怕以为我跟其他癌症患者一样,每天都躺在病床上坐以待毙。这些游离在事件之外的朋友,就算觉察到了房间里的动静,也不会有任何动作,除非玛丽对他们发话了。因为我想到,如果刚才进来的是玛丽的话,我是肯定要吃早饭的。
护士走后我才想起我没有问时间,但现在问不问已经无关紧要了,对一个怀有重获自由的希望的人来说,等待才是催生幸福的良药,否则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不知所措。我心中泛滥的感情很复杂,不知道该描述成兴奋、高兴,还是该说成悲哀。跟原来每天差别不大的生活比起来,我已经习惯了想象接下来的混乱不堪和漫无目的,这其中还包含了未知的幸福,比如我一直都在想象的和弗吉尼亚的重逢。但一想到我现在决定逃出去,就等于完全放弃了治疗,我的归宿也一定是死亡,我的全身上下就会缠绕一缕灰色哀愁。如果结果是这样,我和弗吉尼亚的重逢又有什么意义?我还不知道答案,这要等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我像原来每天早上去学校上课时那样,起床后慢悠悠地走进了卫生间,整理自身的兴趣又回来了。其实并不是我的态度变得积极了,而是我考虑到逃出医院后接踵而至的大堆麻烦事,我不能太邋遢,免得引起爱管闲事的邻居、路人甚至警察的注意,我要像个体面的教授回到家里。想到这里,我立刻停止了联想,现在事情还不是完全有把握,不应该把事情想得太美好。我瞥了一眼那扇寂静的门,想着什么时候菲利普能从那儿走进来,那时候离事情的最后结果就不远了。我对着镜子开始梳洗,这一次我极为认真,差点就找回了往日生活的感觉,这个时候弗吉尼亚一定还在卧室里酣睡。我像往常那样,用沾湿后的梳子把头发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头发变得整齐而富有光泽,接着,我用热水洗了脸,把脸上那些莫名的悲伤形成的皱纹去除了。我又看了看镜子,人精神了许多,不过,人们还是看得出这是个病得不轻的家伙。那下垂的眼角,消瘦的脸庞,没有神采的眼睛,还有那不健康的肤色,所有的一切都是证据。脸上和手上还残留着热水的余温,驱除了一点孤独造成的寒意。
就在我凝视镜中那个衰弱的自己的时候,敲门声响了。指关节轻叩在门上的声音低沉且强劲,显然不是玛丽找我。
我出人意料地冷静,尽管如此,从卫生间走向门的那段时间里我还是想了很多。和最初想到这个办法时的胸有成竹不同,我开始计算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想了很多鼓励自己的词,在计划的最初阶段,这些词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打开了门。这一次更像是朋友的拜访,菲利普穿得很随意,一件棕黄色的夹克,里面是一件休闲式的衬衫,下身是一条卡其色的休闲裤。他前倾着身子对我笑,背后没有其他人。看着他的这副打扮,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让他进来了。我一直握着门把,所以必须要让我来关门,这样我才能清楚外界的状况,是否有人在外面随时待命。在他向里面走去的时候,我侧耳贴在门上听了听门外的动静,又把门打开一条缝探出头往外看了看,外面走廊空无一人。我的动作很迅速,菲利普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就算他觉察到了,我也可以对他说:“我只是看看护士在外面没有,有了紧急状况还需要她们来处理。”
等到我坐到了床上,他站在不远处对我说:“我们又见面了,过得好吗?”
“这里的生活还不错,我已经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那里有把椅子,你也坐。”我指着对面墙角摆着的一把椅子说。我昨晚意识到了那把椅子的价值,于是发疯的时候没有把它放倒在地。
他露出熟悉的笑容,好像又隐藏着什么阴谋。“我还以为你会记仇呢,现在你似乎想通了,我们都是为你好。只是有时候我们方法欠妥,还请你原谅。”说着,他转过身去搬那把椅子,因此我没看到他的表情。
他身强力壮,出入健身房是常有的事,搬起那把看起来有点沉的椅子来自然是毫不费劲,这滋长了我的担心。他在隔我大约两米远的地方坐下了,没有很近,也没有特别远,在我看来,这是一段合适的距离,我向前一倾就可以碰到菲利普。从他脸上轻松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没有做出提防,就算我有仇恨,他也不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他面对的只是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而且我本来就是个体质差的人。以我的力量,是不可能和他抗衡的。
“我以为这次我来,你会向我大肆抱怨这里糟糕的环境,没想到你很喜欢这里,这太让我惊讶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他坐在椅子上,翘起腿侃侃而谈。
“还没开始正式治疗,只是打了止痛药,还打了镇定剂。对,就像你说的,我很喜欢这里。”
“我没来过这里,不过听说过有这个地方,但来了之后就让我大失所望了,”他摇摇头,“一切都太业余了。那个守卫昏昏欲睡,到处乱晃,护士又喜欢发呆,环境也谈不上美好。”
“你说得很对,但玛丽是个称职的护士。”
“我听马丁提过,他说挑玛丽出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别人不放心,为此他吃了很多苦头。马丁为你的事操了很多心,这是唯一好的地方。”
“你来这里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大笑起来:“我的朋友,你当我是什么了?我当然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告诉医院,要给你最好的治疗,尽全力让你康复,哪知道他们让你住在这儿了!这是医院安排的,我们不知道医院会怎么治疗你,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
马丁和菲利普在办公室强行将我麻醉的一幕浮现在我眼前,如果他们真有这么好心,会忽视我的意愿吗?我装作相信了他,没有深究这个问题,继续问:“那……玛丽来照顾我马丁为什么会吃很多苦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只是这么给我说的。”
沉默了一会儿,菲利普突然摊开双手,他说:“这次太匆忙,没带什么东西,他们对送东西这方面也有限制。我没来得及思考。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一定帮忙。”他似乎对我心怀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