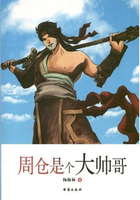但我可能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那时,我在一阵柔和的摇动中惊醒,我以为发生了轻微的地震,或者那是梦境里快死的标志,是死神来索取我的性命了。还好,不是上述的情况。从熟睡中挣扎着醒来是不容易的,我努力睁开双眼,天花板的白光像利刃一样刺进我的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我才能完全睁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我意识到房间里的灯被人打开了,随后我才看到是玛丽在摇我,她动作很轻,没有说话。我仍然是微睁着眼睛,或许到她离开的时候我才适应房间里的强光。
看见我有反应了,她立刻停止了摇晃。她直起身,向后退了几步。
“我敲了很久的门,见你没回音,怕出什么状况,所以才开了门进来。”她像是在为自己的擅自闯入作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多余的,她本来就是在监视我。对一个囚犯来说,是没有隐私可言的。
“我睡着了……可能是药效太强。”我说。
“我早该知道是这样,真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
“是来定点查房吗?”虽然我眼前一片朦胧,但头脑却很清醒。
玛丽张大嘴巴:“噢,我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才来的。是这样的,刚才值班护士那里接到电话,说是明天菲利普校长会来看你,时间大概就是在明天早上。按照规定,你是不能和外界接触的,但因为正式治疗还没开始,他又是你的校长,所以就答应了这次探望。这也是最后一次外界的探望。就是这样。”她把话说得言简意赅。
我本想说“没关系,我不想见他,是不是最后一次也无所谓”,但我什么也没说。这是恨意在作祟,如果学校真的想让我康复的话,他们不会这么对我,无视我的个人意愿,把我关在医院里。而这一切,都是菲利普实施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脑袋里就一直在盘算我是不是可以借这次他来看望我的机会报复菲利普,同时我也在思考我的出逃计划。我知道这都是很黑暗的想法,但不代表我已经堕落了,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没人能阻拦我寻找弗吉尼亚的脚步。如果有人阻拦怎么办呢?很简单,那就像个莽夫一样干掉他。
“你清楚了吗?”玛丽停顿了一下,“那我就不打扰了,你继续睡吧,祝你好梦。”而与此同时,我的思考也已经有了结果。
玛丽已经走到了门边,准备关灯。我观察到,因为眼睛不好,晚上关了灯后看不大清,她是先打开门再关灯的。她扭动了门把。
这时候,我强忍住身体的疲惫不堪,像个精力充沛的小孩一样,一把掀开被子,从病床上跳了下来。落地后发出一阵巨大的声响,玛丽惊呆了。如果我只是个小孩,她可能会认为我只是在调皮捣蛋。现在,我能控制住自己吗?我觉得不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脸已经变得扭曲,愤怒在上面蔓延。我张着嘴大叫,双手抱住脑袋,拉扯着头发。咆哮声越来越大,玛丽已经打开了门,在往后退,她可能从来没照顾过这样的病人,所以她害怕了。我半蹲了下来,像犯罪嫌疑人一样双手抱头,继续发出内心深处的怒吼。她往后退了几步之后,又重新向前移动。玛丽正在经历心理上的挣扎,她是个护士,又是我目前的看护人,理所当然要保护我的生命安全,但她又是个普通人,扮演着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面对危险总得考虑到方方面面。最终,她迈出了一大步,她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弯下腰把我扶起。她一直轻拍我的肩膀,既为了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是在努力安抚我的情绪。
事情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受到控制,因为我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了。她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但这没能带给我放松的感觉,反而让我更不自在了。她的安抚让我觉得有一副枷锁套在了我的身体上,因为我感到肩膀没法移动了,情绪失控者的感觉比任何人都敏感。我又开始咆哮,这一次声音更大,脸上的表情更疯狂,以为已经控制了形势的玛丽又被吓坏了。我趁机挣脱了她的手,在房间里不停转着圈,拿起一切能被我拿起的东西乱扔。玻璃杯,被子,枕头,房间里的盆栽,我那可怜的眼镜。几乎病房里所有物件都被我摔在了地上。玻璃杯在触地的一瞬间就碎了,碎屑甚至溅到了我和玛丽的脚上,盆栽里的土也倒出来了一点,其他东西都胡乱倒在地上,病房里一片狼藉。但我唯独落下了床脚的那一袋吗啡,可能是放的地方太隐秘,没让我发现。玛丽被眼前这一切惊呆了,她不知道我的体内在发生什么化学反应。然而我还没有住手的意思,我满脸愤怒地走到床边,一手抓住床尾,一手握住床边,想把病床掀翻。这时候,玛丽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我斜瞟了一眼门那边的状况,发现玛丽不在了,但还是没停止这疯狂的举动。很快,最开始看到的那三个工作人员冲了进来,玛丽也紧跟着他们进来了,但她只是站在门口。他们没有任何停顿,一进房间就冲到了我的身边,把我按倒在了床上。床本来就已经抬起来了大部分,但现在因为我被按倒,所以床也落在了地板上。我还是继续挣扎,其中一个瘦削的工作人员掏出针管直接刺向我的手臂,直觉告诉我那是镇定剂。等他注射了一半后,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于是就又开始拼命挣扎,仿佛遭受着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们都快按不住我了。
我挣脱了他们,但镇定剂还没注射完,针管却已经消失不见了。我的手上又被划出了一道血痕,显然是挣扎的时候工作人员没拿稳,让针管借着惯性飞了出去。他们见带来的唯一一针镇定剂消失了,都显得很慌张,玛丽也在不远处躬着背在地板上寻找。“我要再去拿一针过来吗?”那个瘦削的人按住我说。这三个人的脸差不多占满了我的眼眶,他们神情紧张。
“没必要了,你看。”其中一个人说。
“这么快就发挥作用了。”
“真是不可思议。”
在他们诧异眼神的注视下,我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不再挣扎,脑袋重重地垂到已经被捡起来的枕头上,看样子已经回到了理性状态。没人料到镇定剂的药效这么厉害,也没人想到这么快我就能恢复理智,只有我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他们三个人和玛丽围到了一起,交代了几句后,他们就离开了。就像刚才进门的时候一样,玛丽也是最后才出去的,她关上房门之前担心地回头看了看我,眼神中流露出关怀和担忧,虽然她年龄没那么大,但是配上她那臃肿的身材,此时的她就像一个和蔼的大妈一样。
“记得明天菲利普校长会来。”她声音很小,蜜蜂般的声音。尽管我听到了,但没有做出回应。出去时,她把灯也关掉了。
他们走后,病房里重归寂静,损坏的东西已经被他们打扫干净了。我嘴角显露出浅浅的微笑,就好像不久前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趁着镇定剂还没发挥作用,我想起身确认几样东西。因为害怕他们不放心,又走回来查看我的情况,然后把我按在床上,甚至想出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我身上实施,我就又在床上躺了一段时间,直到镇定剂在血液中溶解后产生的困意扩散到了全身,直到外面屈指可数的灯光一盏盏熄灭,我才在黑暗中站起身来。
我要做的事情不多,所以我不担心我会在药力的作用下突然睡去。房间里很暗,时间大概已经午夜了,外面的走廊传来幽深的脚步声,可能是无聊的守卫在走廊里来回巡视。要从这里逃出去是不容易的,我想,这么晚了还有人兢兢业业地看守整层楼。起身后,我一直在床底下摸索,尽管没光亮,但凭着直觉,我动作很熟练。我先确认了放在床边的塑料口袋,里面装着解急的注射式吗啡,它放在那里完好无损,我又把它往床底下推了推;然后,我伏在地上把身子探到了床下,一手放在地上支撑身体,另一只手在不断摸索着什么。
我用右手臂做扇形状来回大范围地搜索床底,几番周折后,没有任何收获。一丝紧张的神色像刺青一样刺在了我的脸上,好长一段时间,我的脸都定格在这样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上。随着搜索无果,我又把身子往里面挪了一点,继续大范围摸索,手移动到了床底下正中间的时候,我摸到了一个东西,一阵持久的兴奋感突然在我心中爆发出来。我迫不及待地把身体移出来,不顾床底下的灰尘和越来越强烈的困意,一出来我就把拿到的那个东西放到有微弱光源的地方仔细查看。一个还有一半剂量的针管出现在我的眼前,因为我握住的是针管尾部,所以一直没有伤到我。我满意地笑了,在镇定剂的作用下我能感觉到笑容很疲惫,但这不妨碍我的好心情。在这种痛苦情况下还能咧开嘴笑的时刻是不多的,除了对没把药弄丢感到高兴之外,我还在庆幸仁慈的上帝能让我在这种时候还能开心地笑。
在我抓准时机,把针管扔出去的时候,我的把握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什么也看不到。我仰面只看得到他们三个人的脸,而且我被死死按住了,如果不拼命挣扎,是不可能把那针镇定剂拿走的。这就造成了针管的不确定性,我只是在针管飞出去的时候抓到了一下,改变了针管滑行的轨迹,而他们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比起他们,我知道针管大概在什么位置。
我像找到一个宝物一样捧着针管,用手拂去上面沾上的灰尘,再拿衣袖弄干净针头。随后,我摆正了枕头,把针管放在了枕头旁边,我放得有些歪,因为镇定剂让我站不稳了。想到我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不由得对我的身体捏一把汗,本来就有这么严重的病,还这么肆无忌惮地使用镇定剂和止痛药,我知道这样对健康没有好处,但时间是宝贵的,只要能延长我的时间,什么办法我都愿意试一试。
我如释重负地倒在了床上,身上的灰尘因为撞击都飘到了空中,在房间里微弱而寂凉的光线映衬下,飘渺的灰尘仿佛把我带到了一个冰天雪地中的沙漠。出于谨慎,我又把针管往枕头下面移了点位置,确认了所有事情之后,我才放心地合上眼。在没有任何牵挂地入睡前,我还在想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我最后睡的一次安稳觉?我扭过头看了看压在枕头下露出一半的针管,再把手垂到床下用指尖碰了碰塑料袋,然后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