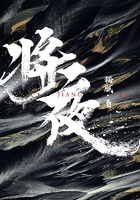让我来简单描述一下最开始的状况:我就是一件静卧的物件,一个游荡的灵魂瞄准了我,然后迅速飞入我的体内,就在那个灵魂撞击我的一瞬间,我的身体条件反射似的抽动起来。这就是获得知觉的过程,不论是婴儿出生时的啼哭,还是刚清醒时扭动身体的病人,还是感觉四肢沉重的从太空返回的宇航员,都是灵魂附体的正常反应。我经过一阵猛烈的咳嗽,然后醒了过来,疼痛在胸腔和腹部又扩散开来。我用手臂支撑起身体,把头微微抬起来甩了几下,这让我感觉清醒了些。我发现我身上没有像之前预想的那样,插上各种管子,连接着各种仪器,就连手上也没有插上输液的细针。除了左手臂上打麻醉药留下的伤痕,还有疼痛的病体,我就像躺着睡了一觉,现在睡眼惺忪地睁开眼。
和初次进病房一样,我的衣服换成了全新的病号服,上面还留有消毒水的味道。当然我身上的现金和银行卡也被医院合法地收走了。我摸索着戴上了眼镜。
这个病房和我之前住的那个没有什么区别,连结构都是一模一样的,床头柜上放的玻璃杯也出自同一家工厂。我又躺了一会儿,等到我完全清醒后,还没有一个护士或者医生推门进来,给我服药或是解释病情。我想到了马丁医生给我描述的那个监狱般的生活,难道他们就把我扔在这里不管了吗?我就像一个得了严重传染病的人,必须隔离开来,连饭都只能从门缝里塞进来;面对的人,也都是戴上面罩、裹上防止感染的服装的医护人员,他们这副样子毫无人情味。
我害怕而绝望地想着一切,在床上搜寻可以发出声音的工具,我要引起他们注意,不然他们可能以为我还没醒过来,直到把我遗忘在这里。以前我从没住过院,也不知道医院病房的构造,但我看过不少故事发生在医院里的电视剧或电影,男主人公遭遇了车祸,女主人公在房间里悲伤地陪在他身边,这是爱情常见的题材,还有家族掌门人的更新换代,场景也多半发生在病房。我搜寻的地方来到了灯的开关处,想起了电视里人们常常按一个按钮来呼唤护士,我也找到了那个按钮。
按下那个按钮之后,没过多久,我先是听见一阵急促的平底鞋踏在地上的声响,然后听到扭开门把的声音。一名护士出现在我眼前,不是上次那个护士,她们样子差别很大。“我叫玛丽(Mary),”她微笑着说,“我们要打一段时间交道了。”玛丽不漂亮,看上去快步入老年了,身体开始发胖,体型变得臃肿。她还烫了她的短发,脸上的皱纹也不少。但这些不能阻挡她的模样和话语产生的温暖感觉。“我在这儿工作快三十年了,把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它。”她扬着下巴自豪地说。玛丽护士显然要比之前我遇到的那个漂亮的年轻护士健谈得多,她可能照顾过许多孤苦伶仃的老人,和他们在一起久了,就养成了唠唠叨叨的习惯。也许玛丽刚进医院当护士的时候也是年轻护士那样的,一副不可接近的模样,谁都别想打她主意,但年龄逐渐剥夺了她高高在上的资本。“后来年龄大了,经验丰富了,就经常被派来照顾重要的病人,他们几乎全都是老人。你可是第一个被我照顾的中年人,我年轻时都是照顾小孩子。”她打量着我。
“你知道了我的情况吗?”我问。
“我觉得很抱歉,依照规定,我们不能当着病人的面谈论他们的病情,”她叹了一口气,“不过命运真是太不公平了,你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种病。”
我自嘲似的冷笑了一声。
“但年轻也是你的资本,你的身体还很强壮,只要保持乐观,没什么病能打倒你。”
“我是说,除了我的病之外,你还知道我哪些情况。”
玛丽说:“他们都告诉我了。马丁医生吩咐过我,你们的校长也给我说过。我很诧异你的身份这么重要,连我以前照顾的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都没这种待遇,那个和蔼的老人的主治医师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照顾好他的起居饮食就行。’最后他因为器官衰竭去世了,不是我照顾不周,而是他太老了,谁都无力回天。这一次,你的主治医师马丁告诉我除了照顾你的饮食起居,还要看住你,也就是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像FBI的探员那样。这一点你的校长也提到了。我很奇怪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像绑架案的共犯一样,我也奇怪你究竟犯了什么大错,要让他们这么对付你。他们说你在确诊的时候又遭到了另外的重大打击,情绪有点不稳,比如你一会儿爽快地决定接受治疗,一会儿又大吵大闹嚷着要回去,就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为了让你好好接受治疗,所以得这么做。我还从来没照顾过精神病患者呢,不过看样子你很正常。医生和校长都提到了你是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头脑都是很冷静的,你们的军人被敌军俘虏了宁愿死在他们枪口下,这可是美国士兵做不到的。他们没告诉我细节,我很好奇你遭遇了什么事,难道还有比得病更令人绝望的事?”
这并不是我的禁区,我决定把事实告诉玛丽。我已经不对治疗抱有希望了,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我应该珍惜每一个出现在我生活里的陌生人,死亡的临近让我明白人与人产生联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未婚妻不见了,我以为她只是去办事了。但我昨天回到家得到消息,说她是因为知道我得了晚期肝癌,所以离我而去,不再回来了。”
她露出难过的神色:“我感到很伤心,我知道你的感受。我也觉得医院和学校的决定太不通情达理,换做是我,受到这种待遇,我也会大吵大闹。你们快结婚了吗?”
“她父亲已经同意了,随时都可以结婚,只是婚期还没定。她父亲很苛刻,始终看不起我,是他一直在阻挠我们,我和弗吉尼亚相爱了十年,不然早就结婚了。现在他看到了我的成就,终于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觉得弗吉尼亚压力一直很大,只是没告诉过我。知道我得了绝症,她可能觉得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她父亲一定会反对我们。等了我十年,现在她一定满肚子的委屈。我理解弗吉尼亚。”
“你们相爱十年,现在你身体不好了,她就这么走了吗?她走就走吧,连一句问候、一句道别都没留下?十年的感情到最后还抵不过一句话?”
玛丽的话很有道理,我沉思了一会儿说:“这里面的确有疑点,但她去哪儿了?她知道我得了病,但是却躲开了我。菲利普校长还给我放了一段录音,我没法不相信。”
“我看了你的病历,你叫李是吧?我这辈子最崇拜搞文学的人,而你就是个文学教授,我们真有缘分。”
“叫我李就好了。”
玛丽无奈而难过地说:“我同情你的处境,对一个已经无欲无求的人来说,把你像囚禁犯人似的关在病房里简直是折磨,但我可没鼓励你自杀。”
“我知道,自杀现在已经没意义了。再说,医院也是为了我的健康着想,他们准备怎么限制我?”
“医生说,除了不能和外界产生联系之外,你有自由的活动空间,但只限这层楼。这里是顶楼,有个巨大的花园式房顶,你不用担心没地方散步。”她机械地说,好像这句话只是在照本宣科,不是玛丽的真实想法。
“顶楼也有病房?”
“当然,但是这儿不对外开放,所以周围很安静。顶楼病房曾经的主人们的构成很复杂,有地位显赫的人,政界要人或是企业巨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接受最顶尖的治疗,他们肯出钱。还有患病的罪犯,他们被软禁在这里,并接受治疗,这是警方要求的。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得再加一种情况了。”
“我是属于哪种情况?”
“好像都不符合。学校足够重视你,尽最大努力让你康复,只能这么解释了。”
“我觉得我像个罪犯,被软禁在这里。他们这是在重视我吗?”
玛丽摇了摇头:“我永远也不会觉得这是重视,他们可能好心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管怎样,他们听不到我的咒骂,我只是个小角色,对我来说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你的工作有些什么内容?”
“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干的事,还有的我暂时想不起了,你会慢慢见识到的。”
“你觉得,对生活我还能抱有什么希望?”我试图拉拢和玛丽的关系,她是个善良的人,这样,我以后的住院生活就会好受多了。
“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你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找到弗吉尼亚,不是吗?我照顾过形形色色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眼都看得出,你是个重感情的人。”玛丽的话一针见血,让我一度以为她会义无反顾的帮我,无论我提出什么要求。
找到弗吉尼亚?我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再为了照顾自己的感受,对自己撒谎。如果不是玛丽提起,我还不知道这个想法多久才会从脑子里涌现,我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考虑寻找弗吉尼亚了。当菲利普告诉了我那个惊人消息的那一刹那,我也许就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只不过是因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才怀着弗吉尼亚回心转意的希望到医院接受治疗。但这样的治疗状况让我连仅存的希望都没有了,我越来越害怕地意识到弗吉尼亚是不会自己现身的,除非我主动去找她。我为什么会回到医院?不就是因为弗吉尼亚吗?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说。
“你看,一提到弗吉尼亚,你精神就提了起来。”
“那你会怎么做呢?”我努力暗示玛丽,想让她明白我此时的想法。
她有点不怀好意地笑了,好像提醒我尽快打消这个念头。玛丽很聪明,她明白了这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正在我脑中产生,虽然还在孕育,但已经有一个雏形了,仿佛一个在成长的生命一般。既然有了雏形,要打消这个念头,除非扼杀掉这个生命,也就是干掉我,让我的意识就此消失,不然这念头再也没办法打消。我觉得既然已经被逼到了绝路,这样的治疗也让我看不到任何生命的希望,那不如就坚持最开始的希望。就这样,我现在的生命不再迷茫了,我也是在醒过来后这么清晰地看到眼前的目标,那就是找到弗吉尼亚。我得从这座监狱逃出去,在生命走到尽头前找到弗吉尼亚。不论患病与否,还是艰难是否伴随一路,怀有希望的生命永远是鲜活的。
“没什么特别的,一切按医生说的做。”她轻松地说。
玛丽是个称职的护士,这个回答表明了她对我的态度,她拒绝帮助我,拒绝协助我逃出去。很多时候,人们想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平静地点了点头,尽管我们都清楚,我还是不能让我的想法泄露出去,万一她告诉了马丁怎么办?到时候肯定会加强安保措施,那时逃出去就更难了。我觉得只要我不明目张胆地提出逃走,以玛丽那颗善心,她是不会告诉他们的,因为我没为难她。
但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的时间紧迫,我越来越无法忍受腹部的疼痛了,不知道是病情的恶化,还是打了止痛药后产生的依赖。这些都不是好兆头,不管是分裂的癌细胞,还是凝聚在一起御敌的止痛药,都一步一步把我往死亡的深渊那边推。我想加快这一切的速度,但我知道急不得,每一件事都要耐心对付。
从思绪回到现实,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似乎谈了很久,而我还像个死人那样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除了我的嘴巴,我的身体几乎没移动过。我侧过头看向窗外,绿色窗帘只拉上了一半。雾已经散了,从顶楼病房的窗户看出去视野很好,城市里的一切地标和绿地都尽收眼底,但外面天色已晚,让景色逊色不少。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问。
“晚上七点二十。”玛丽迅速回答了我。她过来时刚看了时间,看来我们没聊多久,不然她也不会这么快估算出现在的时间。
这一次,我的昏迷持续了三个小时左右。如果我没猜错,我在医院办公室里呆了大概一个小时,我在四点多的时候被扔在了这个病床上,而七点过的时候我才醒来。你们的印象可能不深,但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次麻醉后昏迷不醒的时间和病症突发引起的昏迷的时间惊人的相似,都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甚至不及一次午睡。如果这两次昏迷中任意一次有问题,我更多的怀疑第一次的昏倒。对昏迷本身我没什么疑问,无疑是癌症造成的,但是我有可能只昏迷几个小时吗?后来到了医院,我是在疾病、止痛药、麻醉剂、镇定剂和各种药水的联合作用下持续昏迷的,如果注射普通麻醉剂的人只会昏睡几个小时的话,那么只要加大了剂量,或者再混入其他药剂,昏睡的时间肯定会大大加长。
“教授先生,你在发呆了,你还需要休息吗?”
“不用了,正是因为精神来了,所以我能思考了。”
“好吧,时候到了,起来收拾一下跟我去吃饭吧。”
我挣扎着病体起来了,虽然我不情愿现在就起来,我还想再多躺一会儿,但我心里盘算着一个计划,那就是找机会逃出这个地方。我现在呆的地方,就像过去某一个时期世界上盛行的疯人院,里面的人借口精神病把一些健康人关进疯人院再也不让他们出去,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逃了出去。而我还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构造,所以要找个机会到处逛逛,摸清这里的一切,连一根下水管道都不放过。玛丽给我说了这是顶楼,那这栋楼肯定就是病人住院部了,医院不可能为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安全清空整栋楼的病人,毕竟十个普通病人就能带来相当于一个富豪病人的利润。官方对外公布的是这层楼不对外开放,贵宾才能入住治疗,但实际上他们是封锁了整层楼。真正的贵宾可以随意出入,在那个时候,这里只是贵宾病房,病人享有充分的自由权;而我们这些特殊病人,就只能像精神病人一样被关在这里,和外界没有任何交流,如果最后我们重获了健康,但失去了自由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没有亲人,没有人群,没有声音,只有亲身体验了这样的险境,才能体会到世界上的孤独是多么没有意义。那些叫嚣享受孤独的人,哪个不是至少有自己心爱的人陪在身边?没人知道这里黑暗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病房只进不出,出去的人不是变傻,就是丧失了和社会沟通的能力。虐待,毒品,还有暴力,你能想到的最恶劣的行径都能在这个地方找到,只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不能体现出来。
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病号服,然后就想走出房间,玛丽跟在我身后,她似乎是想让我熟悉一下我会一直住下去的这个地方。但走到房门的时候,她叫住了我。她的声音很突然,就像晴空中不知从什么地方落下来的一滴水,不偏不倚地落在人的头上,又像划破静谧的夜的一道闪电。我心中一惊,我害怕她觉察到了我的出逃计划,不过还是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下来。
“你不收拾收拾吗?不只是整理衣服。”
我立刻明白了她在说什么,我上一次这么不注重仪表,还是什么时候?或许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因为那是面对弗吉尼亚,我们对彼此的深入已经穿透了外部的隔膜。而现在我周围是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人。玛丽的这句话唤起了我的羞愧之心,“谢谢,你又提醒了我一次。”我狼狈而不动声色地走入了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