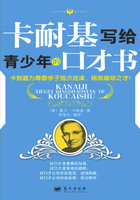娘上到了阿弥石,大雪茫茫,下得天和地一样的颜色,呼啸的北风里都是白。白里有她的儿,大儿和二儿。大儿前面走,二儿后面跟。二儿用火铳指着前面的大儿。娘就听见了吼声,娘看到观音洞洞口之上,一个拿着火铳指着他的大儿和二儿。那人吼,公鸡啄白米!她的二儿马上回答,白米管玉帝!那人吼,玉帝管土地!他的二儿答,土地驮长枪!那人收了火铳,朝洞里喊,客来了!娘听那人的声音好熟,远远望,竟是他的三儿。他的三儿从另一条山路先到了。原来她的三个儿不约而同,瞒着她都到观音洞来了。娘身子贴着崖,心一阵扯痛。娘转过身去,娘不愿在这时候出现在儿们的面前。娘是知书达礼的人。娘想走,脚挪不动。脚挪不动,娘还是支撑着走。娘的耳朵里都是那些声音。问,长枪打毛狗!答,毛狗拖公鸡!问,公鸡啄白米!答,白米管玉帝。娘的耳朵被那些声音灌满了。那些声音是大别山里孩子们玩的一种纸牌游戏,孩子们用硬纸壳儿一张张写上这些字,分发了,一张张地亮,一张张地压着吃掉,回环往复。娘的脑子里幻出小时候的儿们来,她的儿们小时候趴在草地上,做这种游戏。娘想不到儿们长大了,这游戏竟成了他们接头的暗语!
娘提着空菜篮子朝回走。菜篮子落满了雪。娘的心空落落的充满了辛酸。娘走到王姓的祖坟山上,白雪茫茫的,桂儿山上的桂花树的绿叶上压满了雪,厚厚的。娘提着空篮子走到那个雪馒头前,弯下腰,伏下身子抓了一把雪。娘咽一声就是两眼的泪。娘忍不住哭出了声。娘说,老鬼呀,你的儿我一个个地养大了,可我拢不住养大的儿了。娘平常最看不惯山里的女人嚎天撞地的哭。娘现在也忍不住了。娘发现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任眼泪流出来,心里就好过一些。嚎天撞地的哭,原来也是一种幸福。天地在雪里静静的,静得人的耳朵痛。娘的脑子里出现了丈夫临死前的景象,丈夫临死前拉着她的手,流着眼泪不松手,不能说话,却张着一张大嘴不肯闭。她知道那是丈夫要说话。她俯下身子伏在丈夫的胸膛上听,她听见丈夫喉咙深处浓痰滚动的声音,那声音别人听不懂,只有她听得懂。丈夫对她说,你答应我,你不能丢下我的儿女,你要把他们抚养成人。男婚女嫁。她含着眼泪点头说,我答应你。你闭上眼睛放心走吧。娘想起这些,眼泪又止不住地流出来。
娘顺着原路回到了石槽冲。娘来到菜园子,放下菜篮子,倒掉篮子里的雪。娘弯腰,在雪地的菜畦里扒菜。娘将菜叶子一片片地摘下来,放进菜篮子里。娘不能空着篮子回去。家破败得只剩一个管家了。她是娘,没断气之前就是家里的主心骨。家里还有两个儿和两个女儿,等着她的菜回家,做中饭。
十四
娘走了。娘回去了。
娘的五个儿,有三个参加了这个有名的,历史上叫做“观音洞会议”的会。
洞上,王幼刚手里拿着火铳继续放哨。洞下,王幼猛用火铳指着大儿王幼勇吼,站住!王幼勇问,站住干什么?王幼猛说,叫你站住你就站住!你要是不站住,我就开你一铳!王幼勇就站住了。王幼猛吼,闭上眼睛!王幼勇就闭上了眼睛。王幼猛说,不许偷看!王幼勇闭着眼睛说,我不偷看。王幼猛放下火铳走上前,从裤腰里掏出一样东西来,戴在王幼勇的眼睛上。王幼勇问,你给我戴的是什么东西?王幼猛说,你这么聪明的人,未必猜不出?王幼勇笑着说,是不是磨面驴戴的眼罩子?王幼猛说,你真聪明,猜得对了。王幼勇问,你这是干什么?王幼猛说,少罗嗦。进去!
王幼猛用火铳押着王幼勇,朝洞里走。洞不大,进了石头做的门就到了。观音洞里的尼姑没来,尼姑是半路出家的,山下有她的儿女。山上忙的日子她上山点灯烧香,山上不忙的日子,她就下山持家过活。观音像石头做的桌子下,烧着一堆火。湿柴架的,因为泼了石缸里的剩油,所以还旺,熊熊的,冒着青烟。王幼勇进洞后听见许多声音在窃窃私语。王幼勇进洞后那些声音就没了。走到火堆前,身后的王幼猛用火铳捅了一下他的后背,说,站好!王幼勇站住了。王幼猛说,报告师傅,人我押来了,就是他。这个人近几个月以革命的名义四处活动,太张扬了。我怀疑他是奸细。师傅对王幼猛说,你做得对。师傅对王幼勇吼,跪下!众人一齐吼,跪下!王幼勇说,不能跪。有三句话要说。师傅问,哪三句?王幼勇说,这三句话不是普通的三句话。不是一去二三里,也不是公鸡啄白米。师傅问,是接头暗语吗?王幼勇说,对。师傅笑了说,对不起,我们除了一去二三里和公鸡啄白米,其余的不晓得。王幼勇说,你们中间肯定有人知道。师傅说,那好,你说吧!王幼勇说,英特!这时候王幼勇听见观音洞外传来一个姑娘的笑声。那姑娘一身男装踏着雪进来了,掀了头上帽子,露出两只明亮的眼睛,说,我来答。姑娘说,纳雄!王幼勇马上答,奈尔!姑娘伸手摘掉了王幼勇的眼罩子。王幼勇喊,素云!是你?姑娘喊,没有想到吧?王幼勇说,你怎么回来了?暑假过后你不是回学校了吗?老师不是叫你当秘书吗?傅素云说,是老师派我回来的。傅素云对众人说,同志们,这就是组织派回来的特委书记。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表哥。傅素云对王幼勇说,对不起,误会了。都是一家人。今天同志们才见面,平常都是单线联系。要不是老师派我回来,告诉我与你的接头暗语,你今天就没命。王幼勇问,老师可好?傅素云说,老师好。王幼猛和王幼刚上来叫傅素云叫表姐。傅素云笑着答应。
众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众人都知道傅素云是夫子河傅家的大小姐,没有想到傅家大小姐也是革命的人。王幼勇用眼睛扫着洞里的人,发现座在观音像下石桌前,王幼猛叫师傅的,原来是“肥肉”,怪不得大清早“肥肉”就来石槽冲唱八仙。王幼勇看见“肥肉”的那个婆娘就挨在他的身边坐着。王幼勇看见那个曾经戴着破草帽腰间藏着刀到他家讨赌债的人也来了。王幼勇明白了,他家老二和老三原来都参加了地下组织,那八担棉花其实不是赌博输的,而是作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肥肉”是老二联络人,老二给“肥肉”打了欠条子,“肥肉”不出面,让戴破草帽的人去讨的。王幼猛上前朝王幼勇肩上拍了一把。王幼刚上前叫了一声哥。王幼勇的两只手同时握住了王幼猛和王幼刚。傅素云鼓掌,欢迎王幼勇。王幼勇坐到观音像下石头桌子前,“肥肉”不让。“肥肉”问傅素云,凭什么说他是上级派来的特委书记?就凭那三句谁也听不懂的话吗?傅素云哭笑不得,说,那三句话是英语共产主义的意思。“肥肉”说,我怎么听起来像南无阿弥佗佛。傅素云说,不要瞎说。“肥肉”说,我不管那些。我不要肉口传,我要看真经。王幼勇就把带在身上的文件拿了出来,叫傅素云宣读。原来那文件王幼勇从学校回来时就带在身上了。文件上盖着鲜红的章子,“肥肉”这才信了,让出观音像下石桌前的位子,让王幼勇坐下。
于是傅素云就宣布开会。王幼勇说要布置一下会场。“肥肉”说,什么都没带,就这样开算了。王幼勇说,不行,这是一个严肃的会,不能草率,要布置一下。“肥肉”说,空手白巴掌用什么布置?王幼勇说,主席台正中央最起码要挂一面党旗。“肥肉”问,急赶急的哪里找那东西?王幼勇说,想办法。“肥肉”朝观音像望,观音像用一面红幔子遮着。“肥肉就搭梯上去,将红幔子拉上了。“肥肉”踩着梯子问,党旗上画的是什么?傅素云笑了问,党旗上画的是什么你也不晓得?“肥肉”说,我只晓得农会的旗上画的是一张犁。傅素云说,党旗上画的是镰刀和锤子。“肥肉”说,那好办。画不到,我们挂实物怎么样?王幼勇一想,也行。本来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于是就挂实物。王幼刚从腰间拔出镰刀递给“肥肉”,戴破草帽的是铁匠从背后拔出锤子递给“肥肉”,镰刀和锤子是他们的工具,他们随身带着作防身的武器。“肥肉”从壁上拔几只钉子,将镰刀和锤子挂在红幔子的正中央。历史记载观音洞会议是挂实物的。
于是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召开了。成立了特委班子。王幼勇任特委书记。“肥肉”任宣传委员,铁匠向永远任组织委员,傅素云任妇女主任。王幼勇作报告,报告内容是根据上级批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的活动由地下转入公开,主要任务是发展和壮大农会组织,以各级农会组织为依托建立革命武装。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
会散后,天还下雪,王幼勇指示大家将洞里打扫干净,物归原样,不留痕迹。“肥肉”笑了,说,扫个卵子。王幼勇说,那不行。从今天起我们到一个地方要秋毫无犯,这是纪律。大家就扫洞,将洞里烧的灰扫出去埋掉,将红幔子归原。王幼勇批示大家分头隐去。
众人分批散去。
雪纷纷扬扬地下。王幼勇和王幼猛和王幼刚一起走。王幼猛激动了,喘着气说,哥,你现在是特委书记,我是你的兵。王幼刚说,哥,我也是你的兵。王幼猛说,哥,我跟你再告个密。王幼勇问,什么密?王幼猛拿出一撮艾,说,娘吸的不是烟土。王幼勇一愣,问,娘吸的是什么?王幼猛说,娘吸的是陈艾。陈艾也香。王幼刚说,哥,是真的。王幼勇朝家的方向,跪下了,说,娘,儿对不住你!
雪地里,王幼勇站起来,眼睛盯着王幼猛和王幼刚。
王幼猛和王幼刚吸了一口凉气,问,哥,你为什么这样望着我们?
王幼勇说,记住!告诉你们,有些密是不能告的,要让它一辈子烂在肚子里!听见没有?
大雪茫茫。
傅素云赶上了王幼勇。王幼勇问,你怎么不走?傅素云笑了,说,从今天起,我的公开身份与你一样,是石槽冲平民学校的教员,协助你的工作。王幼勇问,是组织决定的?傅素云拿出一张纸说,这是文件,还有老师给你的一封信。临行前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转告王幼勇,要想大别山的革命取得成功,离不开他,同样也离不开你。
十五
娘那天夜里劳累奔波,彻夜没睡。
吃过夜饭,娘的心就空得慌。
天井漏着寒光,儿女们丢下碗筷就到王氏祠堂平民学校上课去了。家里剩她和一个管家。管家也要走,管家边管王家的帐,边种自家的田。有事就来,事做完了,就走,不在王家住。每年的工钱讲好了,只拿一半。管家说,主家,没工夫陪你,我回去了。娘说,你走吧。路不好走,我给你打个火把。管家说,主家,不麻烦你,我自己来。管家就到灶下点了一个火把,出了门,走进夜色里。
娘望着管家消失在夜幕里的背影,叹了一口气。一进三重的老屋里只剩一盏灯和灯下她的影子。小女儿幼馨平常最离不得她,脚前脚后地挨着她转,这些时放下碗筷就夹着油印的识字课本随着哥姐和垸人疯走了,说是学知识。王氏祠堂像是收魂的地方,把他们的魂儿都收走了。娘不明白那地方怎么这样的吸引人?白天娘拿过小女儿识字课本看过,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人?娘发现那识字课本一点也不深奥。是大儿幼勇编的,娘家侄女素云用钢板铺着腊纸刻的,油墨草纸印的。娘家侄女素云的字如其人,清秀可人。但课本内容极其简单,无非是人在世上走,为的身和口,工人织布无衣穿,农民种地没饭吃之类的。娘看不出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要说她的七个儿女都上过学,都认得这些字,而且不止认这些。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到夜里,还要放下碗筷落了魂一样地朝那里疯跑?
娘坐不住了。娘也要到祠堂去听听。娘提着烘笼,带着一个小板凳,打着火把去了。到了王氏祠堂,娘就把火把踩熄了。王氏祠堂的大门敞着,一进三重的大殿里挂着汽灯,挤满了人。娘没进去。娘将带来的小板凳放在窗子下,提着烘笼坐下。没有人发现她。祠堂里正在教歌儿,他的大儿站在讲台上打拍子,娘家的侄女素云踩着风琴教众人唱。居然还有风琴,肯定是县民众教育馆拨下来的。山里人没见过这洋乐器,很新鲜。娘听那调儿很熟,很好听。原来是《孟姜女》的调儿。娘对这歌儿很熟悉。娘从小跟着娘坐在绣房里绣花,娘就教她唱。词儿她记得全。《孟姜女》的词分四季,每段四句。第一段是春季:春季里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娘发现调儿没改,词儿改了。词儿改成:人生在世几多秋,若不革命怎出头?奉劝人人入农会,好为穷人争自由。她的大儿指挥,她的娘家侄女踩着风琴教,一祠堂的人跟着风琴唱得热血沸腾。娘情不自禁跟着开口了,娘不是唱词儿,而是哼调儿。祠堂里有人喊,再来一遍好不好?众人齐声喊,好!于是又热热地教,热热地唱。唱得祠堂瓦面的雪化水,滴下来丁当地响。唱完了她的大儿就在黑板上将那词儿写下来,指着字教众人一个个地认。都认识了,就又唱。这回不是教,而是大家一齐跟着素云的风琴唱。唱完。她的二儿叫了一声好。众人一齐拍巴掌。掌声雷动。
这时候夜就深了。娘听见她的大儿对众人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回去睡觉,明天晚上再来吧。众人意犹未尽,男男女女结着伴,兴高采烈地说,脚半天出不了祠堂的门。娘掇着小板凳急急地起身走了。来祠堂学的都是些青年男女,娘不想让年轻人看到她。娘急急地回到石槽冲,垸子黑漆漆的,只有天上的寒星明亮。娘回到自己的房,关上门,点亮灯,脱了鞋偎在床上,做出睡了的样子。偎在床上的娘静心听,听她的儿女们推开大门回来。这样的时候会有两声问候。进门的儿或女,会对娘点灯的房问一声,大,睡了吗?娘会答一声,睡了。这是做娘的味儿,也是做儿女的味儿。然后儿女们各进各的房,门关了,灯熄了,留下长长的,深深的夜,让娘的心平静下来,落到腔子里。偎在床上的娘耳朵等着那味儿的到来。娘听见深夜垸中的门纷纷的响,纷纷的问候声响起来落下去,静下去了。同人一齐回来的狗,也不兴奋了,归了窝,不再出声音。娘就是听不到她要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