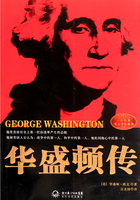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母题,在象征的意义上,它和中华文化具有直观的同一性,其触发的心理效应,作为经验形态是趋同的。也因此,作家们以和谐为美学的追求。然而,文化母题作为自由象征的一种形式,“和谐”并非“同一”,而是变化、差异、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生命如此,文学与艺术亦如此。生命的旋律,总是从摆脱单一的、原初的、无序平衡态(即所谓“一”),朝着多种多样的、丰富杂多的有序平衡态(即所谓“多”)进化,其整体运动的结构形式是不平衡中寻求新的平衡,恰像一首不断变奏的交响曲。同样,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联中,也总是在“同一”的基础上探索艺术上差异与变化。
同一文化母题往往是相似的生命力的运动形态所留下的轨迹或图案。不过,由于文学创造者——作家是以个体的精神劳动方式分别进行书写的,必然会呈现出多样而又千变万化的视点、方法和形式;也由于作为书写对象的母题,本身不是凝固而是自由的一种象征,面对“万物”而开放,染乎“世情”而多变,不可能固定于一种模式,一个基调。换言之,母题并不守恒。它一旦从“一”中产生出来,就自然地溶解于“多”之中,从而扩大、丰富甚至转化着它的意义与美感,艺术叙说与抒情也不断有新的生长点。
于是,同一文化母题可以有不同的文本变奏。这种变奏大致因以下四个不同的原由而开展。
(一)因视点不同而变异
面对同一文化母题,有时因海外华文作家观念和视点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切入点和生长点,也可以写出不同的故事,新的神话。这时,中国文化母题在他(她)们笔下,可能成为作家的再创造。
人所共知,中国民间文化中有“灶神”的传说,也构成大量母题中的一个单元。所谓“灶神”,说的是一个姓张的农夫,因为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原配妻子郭氏的帮扶,家境日益殷实。但是到了后来,张受妾室李夫人的蛊惑,沉溺于酒色,成了甩手掌柜,甚至听凭李夫人把勤劳的郭氏赶出家门。不久,他的家产被挥霍一空,李夫人也跟别的男人跑了,张孑然一身,流落街头。在饥寒交迫中,不幸的他被人救起,安置在一个厨房里。当他发现救他的人原来是郭氏时,羞愧难言,误钻进了火塘,被大火烧死了。这位姓张的农夫的灵魂来到天上,玉皇大帝看在他心存懊悔的份儿上,便封他为灶神,让他掌管人世间的运程。
不难发现,这则民间传说本身就蕴涵了父权意识。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是主体,女人只是陪衬,最多是帮助男人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具。男人犯浑可以原谅,那位张姓农夫,虽然受到了一些惩罚,但最终他仿佛经过了一次火的洗礼仍然能金身不败,成了神仙,女人只是退化到背景的位置。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对这一传统文化母题并非简单的复述,而是作了视点相反的解读和重构。在她的长篇小说《灶王奶奶》①① 谭恩美:《灶王姐姐》,帕特南公司1991版。后中文本译作《灶神之妻》。中,作者借主人公张维丽之口,否定了“灶神”母题中的父权意识:“我为什么要让一个抛弃妻子的人来掌管我的运程?”作为反抗,张维丽把灶神妻子当作神灵供奉起来,并命名为“莫愁娘娘”,希望能呵护好生病的女儿。谭恩美无疑以此改造了一则原本为男性利益服务的传统神话,变男为女,将一位女性选为“灶王奶奶”,呵护家人一生平安。
《灶王奶奶》的故事是在厨房里的餐桌上两个人之间展开的。张维丽和珀尔是一对母女,住在旧金山。小说开始时,珀尔四十岁,年迈的母亲在珀尔眼里固执、怪僻,爱用一套又一套的“老话”(珀尔称之为“格言”)教训人,对她什么都关爱有加,絮絮叨叨个没完。珀尔患多发性硬化症已有多年,心情很坏,但她一直故意不把病情告诉母亲。张维丽考虑再三,决定将自己的经历说与女儿。终于,珀尔被说动,来到母亲的厨房,边品着母亲准备的中国点心和香茶,边听她讲占整部小说四分之三篇幅的故事。
张维丽从1925年的中国上海开始讲述,对珀尔,那些人与事遥远得像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星球。张维丽小名维维。一天,与她朝夕相处的老母亲神秘地失踪了,维维对此充满了好奇和疑惧。不久,她被送到乡间小叔家寄人篱下,没有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也没有了父亲。维维18岁时寄希望于婚姻,嫁个好人家好丈夫,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不想现实正好相反。为摆脱与一名跋 扈的军人文甫的婚姻,她进行了艰难的抗争,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得以改嫁。张维丽英文名叫路易·维妮,如今是个老寡妇了。她一生经历了遭父母遗弃,丧子(头三个孩子都死了)、丧夫之痛,且受尽欺凌。讲这些旧事时,她说她“一直想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珀尔听了母亲张维丽的故事,也讲出了自己的病情。可是,这时,全书的故事已接近尾声,张维丽的故事造成的气氛似乎冲淡了开头有些悬念的珀尔的病情。按照《纽约时报书评》上一篇文章的说法,这是因为小说不仅仅讲的是一位女性的个人灾难性的经历,还暗含着她所处的社会中的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及背后的力量俯拾即是。《灶王奶奶》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环境到底是怎么命定的,个人的抉择在其中是什么分量。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往人间的使神,他的任务是查探世情,然后上天禀报,玉皇大帝凭此决定如何降福。民间还相信灶王爷姓张,并有一妻。但在《灶王奶奶》里,丈夫们都算不上是造福之辈,惟最最悲苦的母亲享有禀报的资格。坐在中国人惯常用来祭灶王爷的厨房里,张维丽面对自己神秘的老母亲,是在直接向玉皇大帝诉说呢,还是在用她自身来证明她的疑惑甚或绝望?
值得注意的是,《灶王奶奶》中那位女性的保护神,生前也只是一个因循父权制传统的贤妻良母,张维丽尊崇她是因为与她有着相同的命运。她们俩同为父权文化中完美女性的典范,却都受到男性专权的轻视和迫害。张维丽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姨太太,为了爱情与情人私奔后,威严的父亲命全家为她举丧,视她为已经死去的人,家中谁也不许提起她。张维丽因母亲之故经历了被寄养的童年,出嫁后,那位性格粗戾的丈夫又是集父权制残忍冷酷于一身的暴君,他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包养情妇,在他眼中,妻子乃至任何一个女人,只是一己泄欲的工具,全然不顾女人的痛苦乃至生命。女性在这个以父亲和丈夫文甫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被无情地剥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可以说,没有比张维丽的一句话更能反映女性被异化被工具化的真实状况:“我想我们在他(文甫)眼里全都一样,就像一把给人坐的椅子或一双用来吃饭的筷子。”
当然,张维丽没有谦卑顺从到底。面对族权、夫权给她的身体和心灵造成的非人道的伤害,她要求与文甫离婚,甚至不惜步母亲的后尘,弃名誉于不顾与情人私奔。可是,她的反抗未能超越客观的被动性,充其量只是一个消极的反抗者。当她最后忍无可忍决意离婚时,她仍幻想着依靠父权来摆脱与文甫的婚姻。然而,此刻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并不能给她任何帮助。这时,一位英雄似的男性——美籍华人吉米进入了她的生活,成了扶持她跳出苦海的救世主。可见,《灶王奶奶》中张维丽的反抗过程,总是在向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求助,而并没有能自己救自己。女主人公的这种命运,可以是中国式的,但也是带有普世性的女性际遇。
显然,谭恩美借助中国文化母题,却又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改造了“灶神”的传说。同一个神话故事,由于视点与观念的不同,笔下的故事已不再是古老的、人们熟悉的传奇,而是结合了新历史和新现实的再创作。这种母题的艺术变奏,诚如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朱虹所言:“他们(按:指海外华人作家)更关心的是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和形成自己的特点。他们更在乎追求小说的艺术性。他们使用中国的题材,甚至利用记忆、耳闻乃至想象进行创作。他们运用外语来表达他们想要描述的中国和中国人。与其尽力为中国代言或代言中国,还不如转而用中国的题材表述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同时又在这种表述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当然,他们所关心的仍是艺术表现本身。”①① 朱虹:《海外华人作家——新的一代》,《华文文学》2006第1期。
(二)因情态不同而变异
海外华文作家同大陆文人一样,如上一章所述,更重山水精神。这与中华文化传统中把山水作为人格修养或寓心明道的象征有关。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影响甚远;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以生命自由与自然的和谐为美的人生也是许多人、特别是文学艺术家们的精神寓所。柳宗元在《钴NFDAA潭西小丘记》中,把山水陶冶情怀的妙处写得淋漓尽致:“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此山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耳谋、瀯瀯之声与自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诗文中一般都有山水精神的体现,如杜甫诗《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以泰山之雄深高绝,象征他对磊落人格与远大志向的追求,可以显出杜甫受到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深刻熏陶。李白的《敬亭独坐》:“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山如老友,几可把臂共语,山是人格化的,与李白的孤高绝俗的品格同调,从中可以体味出庄子的生命与自然相和谐的道的精神。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并非山水诗人,但他的山水诗要较一般山水诗人还多,就是藉山水精神抒发怀抱所致。李白一生大半在浪游中度过,遍历名山大川,所作山水诗更多与怀才不遇的放逐情怀相关。
实际上,在中华文化母题系列中,“山水”与“乡愁”“放逐”相契。山水也总是与放逐者为伴。“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是被放逐的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自我放逐的陶渊明的超然自适的情怀。明人袁宏道所作《徐文长传》,对一扫近代污秽之习的狂人徐文长的放逐情怀描绘得极为生动:“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揽溯漠,其所见山森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于诗。其胸中又有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神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①① 袁宏道:《徐长文传》,《古文观止》第57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这样的悲怆和绝望,与可惊可愕之山水是何等契合!放逐者心境之时空错失感、自我迷失感,乃至生存漂泊感,总是可以在自然的山水中找到其感应对象的。作为自然的存在,有着运行不息与生生不已的力量,草长莺飞,运行水流,春山夏岚,平川幽谷,无不给人一种生命的感觉,使人体悟到一种生存状态的暗示。因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以高山流水等音乐,或通过“以盈尺写圜中之境,使人怀物外之思”的山水画,或借“得之心而寓之酒”的山水游记,或吟诵“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之类诗词,表现他们的放逐情怀,从而构成中华人文精神的一大景观。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涤我胸。”对于现代海外华人来说,沧浪之水任怎样流动,已载不动许多久处樊笼的忧愁。为了“复得返自然”,欲寄愁心与明月,这“明月”可以是想望中的故园山河,那“愁心”却变成灌注在山水中的新的东西。不过,投怀自然,以山水母题而言,仍然会在不同作家心怀中,大体上变奏着三种不同情态的“山水”。
一种是故乡的成为文化历史象征的“山水”。如长江、黄河、泰山、黄山等等充满文化精神积淀的名川大山,这在他们心中是理想的、回忆的存在,常常唤起的是故园情思和做为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华儿女的一份骄傲。钱歌川先生从纽约归国,即到桂林瞻仰我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灵渠,就是因为这条秦时开凿的运河,不但在我国,在世界上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他写道:“灵渠开凿成功,到现在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在清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它对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巩固国家的边防,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至于它在水利史上的成就,时至今日,仍然放出灿烂的光彩,足以使国人感到自豪。因为是渠的建造,运用了惊人的技术,实在值得我们钦佩。”他急于把这一中华伟业告诉世人知道的心情,溢于言表。对于那些尚不能亲自徜徉在祖国雄奇壮丽山川的海外游子来说,这一份文化遗产,是贮藏在他们胸中的,时时在回忆与遥望中出现,成为他们精神的支柱。这也是海外华裔作家多有遥忆大陆山水的诗文创作的原因之一。即便是游历秀丽不再的旧时山河时,作家们也会品味出几分故园的山河、塞外的凄美来;甚至他们面对墙上一幅复制山水画,便会想起举杯邀月的诗人,想起绝学无为的闲道人,想起归于自然怀抱的陶渊明、王维、谢灵运……即使身处异国,渡的是野狼河,看的是草裙舞,观的是好莱坞,听的是交响曲,旅美学人暨散文家杨牧心中想到的还是故乡的“寒风,细雨,和院子里等待抽芽的两棵大榆树”。他说:“一年来的默想,使我觉悟到原来异乡风月,春秋,雨雪使我惊讶的,不仅是那种陌生的满足而已,而是对于另一块土地,另一段岁月的回忆和思念。……若是你曾经独自在家乡一条熟悉的山路里行走,若是你曾经被一片巨岩吸住了脚步,若是你曾经到过深涧里等待天晴——你若也曾有过这种经验,你就会有一天突然在艺术和音乐和文学的领域里迷醉,越沉越觉得生命的充实和空虚。”①① 杨牧:《在山岗下》,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