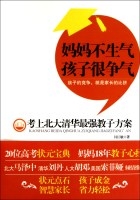因此,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围城”母题的基础上,人性和人类本身无法摆脱的困境以及对于困境的努力突围,成为这一母题范围里具有现代意味延续和扩展的一个分支。聂华苓在谈到《桑青与桃红》时曾说:“这部小说中我想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的寻根,而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人’被困在各种陷阱中反复地挣扎于被困和逃离之间,这种状态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存在,就是human condition。”①① 转引自李静:《域外文学与流亡话语》,《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有关“被困”意象的建构在小说中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第一组意象,被困古迹之中的破木船暗示着国势衰落导致异族人的现实处境,而对于主人公桑青来说,她刚逃出旧式家庭的小牢笼,却又一下子陷入民族苦难的大牢笼。第二组意象则暗示了一个“围”字,沈家大院处于中国皇权所在地——北京城之中,这个城正陷入政治力量的围攻,儿子沈家纲与孤身投奔“围城”而来的桑青却在这种炮声轰鸣的末世氛围中举办婚礼,继而又开始了漫长的现实逃亡。小说写出了聂华苓那一代逃亡者在1949年转折期时所面临的人生困境。第三组意象中,“小阁楼”是一个凌空之所,它经受风吹雨淋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顿,视域狭小。因为沈家纲亏空公款,正遭警方通缉,逃离“围城”的桑青与沈家纲这时却不得已逃上了“围楼”。在异国他乡逃亡的桑青没有方向,似乎永远都在路上。这种对于人生困境无处不在的书写和茫然困惑心态的寓言式表达,恰恰暗合了“围城”的故事母题,母题的演绎与变化当然是与文本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无法摆脱的人生及人性困境的“围城”母题,对于异质文化环境中生长的留学生和新移民文学来说,始终是作家进行创作时不能摆脱的。移居国外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原先旧有的文化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式,在异质文化环境下,统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时空和文化语言的距离和错位不可避免,并且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契机。严歌苓上世纪90年代去的美国,异质的生活与文化给了她很大的冲击,其创作在原本就敏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浸染了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开始吸收了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的透视,也包括西方社会看待“东方人类”的历史文化视点。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源流,主导了严歌苓海外创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性”本色的深层关注。她屡屡以错位渲染着一种苍凉凄美的氛围,表现着无根华人们的寂寞与隔离,并以丰富微妙的笔触去试图沟通异质文化中人性的冲突和心灵的局囿,并希图冲破文化的樊篱和人性的隔膜。通过“写心理”而意在“探人性”,完成对身处多元文化横向交叉时所遭遇的文化和人性困境的揭密。如《少女小渔》中的意大利老头经小渔善良品性的熏染,由“畜生”而为“人”,由猥琐而慈祥庄重颇有爱心,显示了作家对人性沟通的良好期许。此外,《橙血》、《海那边》、《心经》、《屋有阁楼》等作品,也都表现出作者善于从隐秘性心理角度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还原出人物的真实本相。而严歌苓对人物心理的剖白几至臻于完美的境地,在她笔下常是整篇以人的心理推衍,心理与行为、事件互为推动交织成故事情节的发展。具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抒写,令严歌苓的创作达到移民文学少有的高度和深度。
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等待》可被看作是一个寓言,一个呈现人类生存两难处境的悲伤寓言。也就是说,我们短暂的一生,除了等待,别无他事。小说讨论了人类现实的生存状态。《等待》这部作品最为打动读者的地方,是它充满了人道关怀和批判精神,它对于人心细腻、敏锐的层层深入,尤其对于痛苦的惊人的感受力。跟《等待戈多》不同,戈多永远不会来,而《等待》却是在激情耗尽之后等到了,但是这个结果跟自己的想象又大相径庭。回头看时,丢弃的那个却又显得美好起来。孔林千辛万苦跟淑玉把婚离掉,可是在最后却发现吴曼娜完全跟她年轻时不一样,而在淑玉那里却显出家庭的温暖与光辉,不由生出悔意。莫非我们就永远逃不出这个两难的处境?《等待》向读者展示的,是人在认识自我方面所做出的艰难努力,它的艺术魅力,大部分也是由于它所达到的人性的深度。
(三)身份认同与“围城”内蕴
“身份”(status)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重要课题,因为它直接表明一定社会结构中人的不同地位,体现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质。海外移民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尤其敏感。移民作家在异国语言的喧闹中,仍然从事汉语写作,既是抵抗失语、失忆的努力,也是对母语、母体文化的依归和坚持。文化人类学家W·H·古迪纳夫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指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成员用以认识、联系、解释社会现象的模式①① 参见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40页。。作为潜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合理性依据,文化支配、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决定着一个文化系统内部人们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生活样态。留学生、新移民作为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的个体和主体,首先面临的是陌生的背景和语境,随之而来的是自己尴尬、独特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学文献中已经被广泛使用,这里的“身份”不仅指新移民为了取得永久居留权——绿卡,解决自己的合法公民身份;而且指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包括五种主要成分:即价值观念、语言、家庭体制、生活方式、精神世界①① 张裕东:《从何着手研究文化身份》,参见《中国文化与世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不同层次文化心理结构,是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地理生态系统环境对社会群体长期作用的产物,形成一种系统的文化范畴。一旦跨入到另一个与自己的民族文化心态迥异的国度时,差异即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来。进入异质文化的“围城”,必然在精神状态、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造成不适,感到困惑,找不到自身的位置和明确的身份定位。由于特殊的身份和文化背景,留学生、新移民在体验人类的共性上可谓得天独厚,两难的文化处境使他们具有了一种文化空间上的张力,既对所在国文化有着深刻的思考,又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视角,他们越靠近西方文明,越难以抛弃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围城”的突破(有时候是主动的行为,有时候也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和边缘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向核心部分的靠拢,都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得到表现,亦是“围城”母题在文学创作中的传承和新的演绎。有研究者指出,可以这样看待文学中的乡土情结、怀旧情调:它们都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反向确认行为①① 黄耀华:《台北人的历史叙事及文化身份认同》,《华文文学》,2001年第2期。。走出旧有的文化围城,进入另一个新的文化围城,身份的改变,使人能够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和对比,对脱离开来的旧有的本土文化,因为有了新的参照,反而能够找到新的审视点,来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
加拿大的华裔作家张翎在展开居住国文化与祖裔文化之间关系的阐释时,注重以混合交错的文化视角,跨越家园地域之限,时空变幻移位,表达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与确认。她的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2001年),实际上也是将主人公置于生存夹缝处的文化围城中。小说的起因是主人公蕙宁的突然失踪。解开这个失踪之谜,原来是蕙宁到了加拿大以后遭遇文化冲撞后的一系列迷惘,求学何其艰难,生存何等困苦,爱与恨何许纠葛,忠与叛何处不在,使她在异域的文化围城中失却了生来自信的自我,终于不告而别地“蒸发”了。她的失踪具有反向性,其实就是企图在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新结构并认证自我的身份。这一“失踪”之举,说明了当被一座异城的围城所困时,往往向“内”、向“回”地转向文化的本土性,找回母性的声音,以老“家”抗争新“家”的围城。
海德格尔曾经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不能没有语言而存在,语言本身打上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戳记,它赋予人的永恒记忆是人生的见证,它使人找到了一个位置一个身份。谭恩美是当代受瞩目的华裔美籍作家之一,她以第二代华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用英文写作族裔经验,并藉由其母亲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建构和想象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看到谭恩美的《喜福会》①① [美]谭恩美着,程乃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中,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体系指涉意义的冲突与交融,如何影响着母女两代移民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和指认,造成母女间了解与误解,以及恩恩怨怨的悲喜故事。语言是文化差异中最为显着的一个表征符号,进入到一个新的语言系统中,人才能进入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可谓“文化围城”的重要入口。谭恩美的第一本小说《喜福会》和2001年的作品《接骨师的女儿》都在美国一度风行,她一贯的写作风格是交错运用不同的叙述观点来说故事,串连起母亲和女儿、中国和美国、过去和现在。《接骨师的女儿》重点集中在同一族系里三代的女人身上,透过层层铺陈,揭示其中母女关系的爱恨情仇,并非仅来自母女间的代沟,还来自语言障碍、文化差异、阶级落差以及美国化深浅程度不同种种因素,进而导致其价值观上的相异。
谭恩美小说里的女人们一生中都在进行自我探寻的旅程:如何在母女关系与双重文化价值观中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及摸索出适切的身份认同。小说叙述女儿们如何透过母亲的指引在双重文化的困境中表达自我;而母亲们希望创造更好的机会和环境让女儿能在美国出人头地,并且能同时拥有中西文化的优点。虽然双重文化的背景提供左右逢源的机会,然而也可能落入不中也不西的窘境。小说里的女主角都还在摸索如何在双重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最利于自己生存的方法,她们或许还没有充分找到自我,但至少从母女渐渐互相妥协和解的情节里,读者看到了希望。
纵观《喜福会》等一系列华裔文学作品,可以看到华裔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过程:从第一代移民的极度留恋到第二代移民的极度排斥,再到最后的文化融合。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华人所面临的更多的是隔阂及难以认同。强烈的冲突使华裔美国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置于痛苦与迷茫之中,一方面他们固守着与新大陆文化难以同化的母文化,无法消除对美国文化的排斥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被“新”世界所接受而成为美国白人社会的“他者”。然而这一代人面临着更为痛苦的事:文化的冲突也反映在他们与子女的隔阂上,反映在华人移民家庭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中。华裔家庭的第二代及以后几代人生于美国长于美国,从幼时起接受的便是美国本土教育,祖先的文化在他们心里只是遥远而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与拒绝融入美国社会的父母相反,他们竭力归依、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伍慧明的处女作《骨》(1993)获得成功,表明美国读者又一次接受华裔美国小说。《骨》的故事发生在旧金山唐人街,故事情节围绕梁家展开,人物是妈妈和利昂以及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莱拉、安娜和尼娜。同其他许多华裔美国小说或其他许多移民作品一样,《骨》关注中国第一代移民与出生在美国的后代之间的矛盾与和解:一方面要求承认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美国文化,另一方面要求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不过,伍慧明回避了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而是采取对两者的包容。
另一位华文作家弗兰克·秦在《唐纳德·都克》里,描述的显然是一个在真实社会中业已实现的梦想:通过塑造一个经历了从自卑到自信的在美国的中国城成长的十二岁中国男孩,弗兰克·秦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声音,试图实现他恢复中国文化传统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唐纳德·都克的思想历程象征了整个华人移民从无条件认同,到需要实现自己民族文化价值所经历的意识觉醒的心路旅程。
在小说的开始,我们看到的唐纳德是一个完全被“种族主义”内化的男孩,他讨厌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华人身份,对于有关中国的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在躲避华人社会的同时,他也为其他华人所排斥,甚至在家人眼里他也是一个“异类”,是一个华人社会的旁观者。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但他无论如何也抹不去身上的民族烙印,无法抵御的中国城的影响,成为他接受真正教育的关键。此外,通过梦中连续不断的英雄人物关公及梦境中横跨大陆铁路铺设的先驱者的出现,唐纳德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最终促使他脱胎换骨的神话之旅。他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力量,正如卡尔·荣格所说的,是人的无意识深处的一种无意识的文化沉淀。唐纳德十二岁生日的到来正与中国农历新年相遇,从而暗示了最终与他的中国“根”重新结合,预示着他生命中新的年代的到来。唐纳德加入到舞龙的庆祝队伍中这一场景,象征了他融入到了刚刚发觉的珍贵文化传统中。在中国新年的欢庆仪式的喧闹中,唐纳德最终拥抱了中国文化,从而成为弗兰克·秦笔下亚裔美国人典范的化身:学习保留祖先文化,抵制文化殖民。当唐纳德发现“你无法通过放弃中国人而成为美国人”时,小说结尾也表眀了文化认同的态度,和谐统一应当取代对立冲突,才能走出文化的“围城”。
人类无论是在现实社会生活或是在抽象的精神世界中,往往会宿命般地不断重复陷入某种“两难”的困境: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的“围城”状态,人的生命、人性的“围城”状态,不同文化背景下关于身份认同的“围城”困境,以及人类对于种种困境的“突围”等等,都在世界华文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形象的演绎和深刻的诠释,因而使“围城”这一隐型母题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引人注目的内蕴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