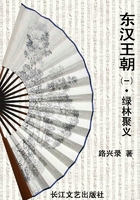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第一节) 内容形式二元论
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照说各种形式主义应当观点一致,其实不然。这个问题即使在“新批评”内部也引起了值得我们重视的激烈争论。
兰色姆认为,最能符合新批评“本体论”要求的是他的“构架/肌质论”。他虽然很早就谈论这问题,但直到在1941年的演说稿《作为纯思辨的批评》中才对这个理论作了详细解释。他说一首诗的构架(structure)就是能用散文加以转述的东西,是使作品的意义得以连贯的逻辑线索——“诗的逻辑核心,或者说诗可以意释而换成另一种说法的部分”。作品中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则为“肌质”(texture)。兰色姆指出,构架的逻辑不可能严谨到像科学技术文献的地步,其作用只是在作品中负载肌质材料,但关键问题是文学作品的肌质与构架无关,肌质是分立的(local)。
为什么兰色姆认为他这种理论符合“本体论”要求呢?因为兰色姆认为诗的本质,其精华,及其表现世界的本质存在的能力,都在于肌质,而不在构架,肌质才是具体的“世界的肉体”。科学文体只有构架,它即使有细节描写,也是附属于构架的,不能分立。诗的特异性就在于其肌质与构架分立,并且其重要性超过构架。“诗是一些局部细节的结合物,在这些细节上附丽着一些独特的兴趣。”而科学论文的全部细节没有自己单独的“兴趣”,全部为其主旨服务。因此文学作品被“肌质化”(textured)为一种本体存在,“如果一个批评家对诗的肌质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等于在以诗而论诗的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只是把诗作为散文来讨论。”因此,他指责许多批评家只着眼于分析诗的构架,“对诗的逻辑内容加以重述,不能算追求本体的活动。”
如果构架与肌质两不相干,诗的“本体”只在肌质,那么要构架又有什么用呢?兰色姆说这两者唯一的关系是互相干扰——肌质干扰构架的逻辑清晰性,因此作品像是在作障碍赛跑,诗的魅力就在这层层阻碍中产生。
这种看法叫人想起华尔特·佩特著名的“多余论”(surplusage)之说,佩特认为“艺术家怕多余话,就像赛跑手怕自己的肌肉”。什克洛夫斯基也有相似的见解,他称作“难化形式”(затруднённаяформа),认为诗人是在“用发声器官跳舞”,诗人“尽量转弯抹角,使想说的话表达得更困难些,从而迫使读者更花力气也更有效地把握世界”。因此,兰色姆关于构架/肌质关系的奇怪说法似乎是许多形式主义者的共同见解。
严格地说,构架/肌质关系与内容和形式关系这两个问题并不完全重合。但是兰色姆说构架“可以是诗中的科学,或者,如果有意识形态的话,是它的伦理”。在更早的时候,他说构架是“诗无法逃避的对实在所发表的逻辑陈述”,这么说构架就大致相当于内容。兰色姆又说,肌质“并非内容,而是一种内容的秩序”,也就是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构架/肌质关系与内容/形式关系有类似之处。
因此,兰色姆说构架与肌质无关,也意味着内容与形式无关。这就是兰色姆的学生们都反对的“两元论”。
另一位美国批评家温特斯则从更传统的立场坚持形式内容两元论。他认为一首诗首先是一个“陈述”,其次才是被带感情的文词写出的陈述,因此诗中出现的是概念/感情二元关系。因此,诗的精华完全能够意释(paraphrasable),他甚至认为无法意释的是首“不好的”诗。
布鲁克斯起而驳斥他,说这种“意释误说”(heresy of paraphrase),是历来文学批评的最大毛病,因为意释就是把诗分裂成形式与内容两部分,而他认为诗的散文意义并非框架,而是“脚手架”(scaffolding),是读者理解了一首诗后就应拆去的工具,“把诗的结构归结于意释,即是把结构归结到诗之外的东西”。布鲁克斯这种看法,似乎非常正确,实际上在理论上是需要仔细推敲的。“可意释性”(Paraphrasability)是语言学中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意释的要求是用另一种说法传达完整内容,那么任何语言行为,只要稍带感情,就都不能意释。这样谈论诗的非意释性就完全没有意义。看来比较合适的说法是诗的可意释性比其他文体小得多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
兰色姆的三个学生坚持用有机论(organicism)来反对二元论。布鲁克斯声称:“有机结构的一般观念是我们近年理论中真正革命性的东西;我们最好的批评实践就是立足于此,而且据我看来,这也是我们复兴诗歌研究,乃至复兴全部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大希望所在。”而兰色姆却坚决反对有机论。
这场争论几乎从《逃亡者》时代就已见端倪。此后,双方各执己见,而且波及一系列作品评价问题。艾略特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刊出不久,兰色姆就批评它“散乱无章法”,结果与艾略特的支持者退特发生争论;温特斯批评庞德的《诗章》(The Cantos)无逻辑结构,结果与庞德打起笔仗。
艾略特认为诗可以只凭“想象逻辑”也就是“形象思维逻辑”串接起来,后来有不少人赞同此观点,称之为“暗示性联系”、“内涵联系”、“质性进展”等。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说,它相当于形象思维可排除逻辑思维的观点。谁也没有说清艾略特式的“想象逻辑”与正常的逻辑究竟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实际上这种“想象逻辑”只不过是正常逻辑省略环节变形、跳动后的产物;新批评派后来大量的诗歌语言分析工作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瑞恰慈曾经认为诗只要能激发感情,逻辑的安排没有必要。在语言分析上比瑞恰慈仔细的燕卜荪就认为导师这看法错误。即使《荒原》这样一度被认为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法”的作品,在艾略特自己加了一系列注释以及批评家多年的工作后,我们也看出一个完整的逻辑构架。可见新批评派内争的焦点实际上不在要不要逻辑构架,而是这个构架与整个作品如何结合,也就是对有机论的理解问题。
有机论是西方文论中历史悠久的命题,许多人都支持有机论,却言人人殊,反而把这个术语的意义弄得很模糊。兰色姆坚决反对有机论,指责他的三个支持有机论的学生根本没搞清各种有机论之不同:把“亚里士多德式”、“黑格尔式”、“坡式”三种有机论混为一谈。兰色姆这个指责很有眼光,虽然他没有对这三者的区分作出解释。我们仔细检查后可以看出,新批评派的有机论的确如兰色姆所说的三者兼而有之,虽然他们最有意义的探讨是接近黑格尔式有机论。
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新批评派与三种有机论的关系。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式有机论——整体论
第一个提出类似有机论观点的亚里士多德,主要着眼于作品形式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种理论认为:作品各部分,从整体看非但是不可少的因素,而且所站的位置也是不可移动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为了美,一个活的有机体,或任何一件由部分组成的单一体,不仅必须使这些部分有一个整齐的安排,而且还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依赖于两个品质:大小与秩序。”这里的大小之谈,听来很像古人的迂阔之论,但我们分析下去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是有道理的。
此后,一直到托尔斯泰,大部分人的“有机论”实际上都是指亚里士多德式有机论,即使没有提出“有机”两字的文论家如贺拉斯(Quintius Horatius Flaccus)、普洛丁(Plotinus)等人,也强调形式各部分的互相依赖关系:诗中各部分的组合关系如有机体的器官,移动或否定其任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改变或破坏了作品的意义。
或许别林斯基的表述是这一派中最清晰的,他指出“现实本身是美的,但它之所以美,是在本质上,因素上,内容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因此,艺术作品可以比现实更美好,“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偶然和多余的东西,一切局部从属于整体,一切朝向同一个目标,一切构成一个美丽的、完整的,单独的存在。”别林斯基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种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有机论是指艺术作品形式的构成特点。
新批评派的有机论经常属于这一种。布鲁克斯和沃伦指出,诗的各种成分不是像砖砌墙一样堆起来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整体性的。他们以彭斯的诗句作实例:
月亮沉入白色的波涛,
我的岁月也在下沉,哦!
他们问:能不能把最后这个似乎无所重要的感叹词移一下位置?
我的岁月,哦,也在下沉!
回答是:“不行,原诗把这嗟叹放在行尾的强调位置上,表明诗人把整个句子写完才感到诗的全部力量。”也不能把“白色”改成其他颜色,因为“白”暗示了死亡和沉寂。
因此布鲁克斯认为可以把诗比作一个有统一性的构造物或一幢建筑,各部分的重荷互相对抗,内部的应力互相平衡。因此必须强调“诗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各种因素在这整体中起作用”。“一首诗应当被视作各种关系组成的有机系统,诗的品质决不在于某一可单独取出的成分之中”。
这种“有机论”,说实话,已是老生常谈,而且,说一件艺术作品(不管是如何完美的杰作)各部分如此完美地组合成整体,一字一句或一点颜色一个音符也不能改动,是不符合实际的夸张。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尖锐地指出:小说中某些部分并非改不得,而且事实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在不断修改,我们没理由相信传世的文本已经至善至美。美学家佩珀也指出,有机论中应有定量分析:一个“有机整体”究竟能容纳多少材料?结合得多紧?正如大树吹去几张叶子,大动物死了几个细胞,不会影响其整体性和生命力。这使我们想起前面所引亚里士多德的话:讨论有机论要注意作品大小(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太大太小都不美,是囿于当时希腊文艺创作实践而发的议论),大型作品必不可缺的部分也不可能过小。
而且,从文学作品文本本身的性质来证明整体性,是不可能的事。某些美学家从格式塔心理学出发,认为整体性是感觉组织作用的结果,事物的“整体性”及其知觉完全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原始的组织作用。这样解释造型艺术比较行得通,用在文学上依然有困难。
一部分结构主义者试图从读者的阅读程式上来解释有机整体性问题。俳句仅三行十五音节,绝句仅四行二十音节,惠特曼有一行诗,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几万行的史诗,几百万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从作品自身具有完整性是说不通的,“整体性”也是读者的阅读程式与作品结合的产物,作品的完整意义多少是要靠读者来补足的。这个问题因牵涉面较广,我们将在第四章第四节给予深入分析。但笔者个人觉得结构主义这立场是正确的。说任何艺术品都是(或必须是)自我完整的有机整体,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也不符合艺术实践。
俄国形式主义者很早就怀疑这个整体性观念是一种文学保守主义。当时参加俄国形式主义活动的马雅可夫斯基就认为过分重视整体和有机性观念,是旧式的象征主义理论,它意味着把读者的功能缩减成被动的,感受性的。他的立场和后来布莱希特的看法相同:三十年代布莱希特在与卢卡契争论时就认为,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整体,那就是虚假的,因为整体性妨碍读者认识客观世界的缺陷和社会的不合理。他的看法应当说很有道理。
(第三节) 黑格尔式有机论——内容形式统一论
黑格尔式的有机论主要阐明内容与形式如何结合,这牵涉到他的哲学体系中的许多问题,所以甚至有论者认为有机论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一部分。正是因为部分新批评派用黑格尔辩证法来为有机论张目,才引起兰色姆的极大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