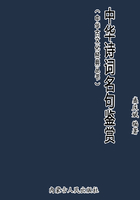发生伦理转向的科目,基本上都是以追求“真相”为己任,关于“真相”独立存在的观念早就过时,但是一般心理学,历史学等,依然认为被追寻出来的“真实性”中包含着“有效性”(validity)。而文本的有效性,则借重文本在批评中的核心地位,此时,真实性就变成了“文本的可信度”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玄,但是新批评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兰色姆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晰。在1941年那本给这一派命名的书《新批评》中,最后一章“呼唤本体论批评家”,兰色姆用绝大部分篇幅与查尔斯·莫里斯讨论文学艺术的本质。莫里斯遥遥呼应早逝的皮尔斯,那时正在发展符号学的美国学派。在三十年代末,无论是莫里斯或是兰色姆的形式论都尚未成形,但这场讨论充满真知灼见:莫里斯从符号逻辑出发,认为符号的“符形”,“符意”,“符用”三个方面,对应三种“话语形式”,即科学,艺术,技术。“符形”与“符意”距离较近,“符用”(符号的使用价值)则是完全另一个层面,因此艺术与技术距离遥远。兰色姆却认为艺术讲究形式,说明它是一个制成品,“更远离科学,而接近技术”,因为艺术“既要认识事物,又要创造事物”,对现实产生影响。兰色姆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现代诗人们)证实了本体的真正效用”。
应当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见:几乎提前半个世纪,兰色姆预见到形式论将会朝文化—伦理意义转过头去,着眼于文化效用。正是形式分析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基础,今日理论的文化—伦理关怀,是建筑在对艺术文本形式之上的,是从文本里细读出来的意义。
这不是我在重解文学理论史进程,这是切实的问题:就拿当今“后经典叙述学”最热衷讨论的“不可靠叙述”来说,就是新批评的论战对手却同属形式论阵营的“芝加哥学派”提出来的,反讽是新批评最关心的课题。可靠与否依赖阐释解读,新批评虽是形式论,其立足点却在解读。
五、新批评的“中国化”
中国人读现代理论,总是面临一个令人恼怒的老问题:“西方文论”正在让我们作为“现代文论”来接受。
中国人对什么西方理论都能客观评价,在总体接受的前提下,做有选择的变通。贫富差基尼系数,无罪推定,罪犯人权,最低工资线,宜居城市标准,甚至台风命名。但是文学理论不行,文化理论不行,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这个问题,已经纠缠一百多年,在此无法讨论此问题背后的情结。我只说一下可能的解决办法,最后提出我的一个方案。
有没有可能把“西方文论”中国化?
当然能,从王国维到钱锺书,几代中国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证明绝对是能的。用先秦名学说符号学,用陆王心学阐发现象学,用禅宗解释精神分析,用毛宗岗金圣叹小说点评支持叙述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创见,而且确实推动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很多人发现新批评特别适合中国化:杨晓明论梅尧臣“诗有内外意”是张力论,李良清以中国传统诗学的“气势”说张力;周裕楷论宋人“工拙相半”是“包容诗”;陆正兰以钱锺书“拟声达意”与“姿势语”相比较。这种工作常被人指责为“比附”或“局部中国化”,我觉得此种苛责完全没有道理。迄今为止,中西比较文学最切实的成果,依然来自这些点点滴滴但是切切实实的研究累积。
但是整个批判理论体系有没有可能中国化?如果不能将整个体系变成中国文论,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从“西方”这个体系讲起。但是假定我们真的把整个体系成功地中国化了,也不能解决这个体系在全世界的地位。我在伦敦大学开了多年的“比较文学理论”课程,把现代理论分成二十讲系统讨论。有些人提出来,应当加进“东方理论”,我欣然同意,我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加了“禅宗美学”一课。但是有些学生和老师就提出来,为什么不能讲阿拉伯苏菲神秘主义?为什么不能讲撒哈拉南部族信仰?这样一来,就没有体系可言,只能像个拼盘。
也有中国学者反复提出,“中国化”就是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原则,就是说:如果某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与我们当今的“精神需要”隔膜,就不必去弄通。这个原则的提出者实际上认为新批评有用。我个人认为,“拿来主义”这个指导思想虽然好,恐怕实行起来不容易,反而造成困惑。原因倒是简单:要切实弄懂了,认真应用了,才知道是否合适,而我们对哪个理论,可以声称弄透了,可以决定取舍了?今日不需要,是否明天也无用?
因此,我在此提出另一种思考方式:我们面对的这个体系,叫做“西方文论”是有道理的,例如新批评的主要提倡者,热爱中国,经常引用中国哲理,而且长期在中国任教,但是无法否认他们是欧美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过分纠缠于肤色,称之为“现代文论”可能更合适。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是一种现代思维,它的确是欧洲文化土壤上自动长出来的东西,原因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出现了这个气候——现代性思维。而那个时候,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国,尚未出现这种气候,正如在二十世纪之前的欧洲,也还没有这个气候。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整个当代思潮,借用了大量“东方价值”,用来批评西方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渐渐认同的一套价值观。例如女性主义,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权利,多元文化,反无限制科技等等。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向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禁区”的人,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与佛教的众生有灵力戒杀生有显然的相应;对残疾人、智弱者的关怀,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老年人权利,当然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致。至少,因为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
因此,当今情况变化了:当代中国文化,与批判理论声气相求,问题对接,论辩也对得上榫口。批判理论从来没有如此让中国学生激动,让中国学者感到有针对性,理论热的大气候已经出现。只要文化气候成熟,批判理论不仅可以与传统中国文论对接,更可以与当代中国对接。当代中国,已经开始召唤这样一种对接。
也就是说,“批评理论当代化”,与“西方文论中国化”,或许能同时进行——实际上也在同时进行。可能不久,我们就可用前一个命题,代替后一个命题。
出版这本书,并且名之曰《重访新批评》,是因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国内不少年轻学者对新批评方法感兴趣,用之于中国文学,做出了出色的文本分析和理论拓宽,他们用批评实践证明了新批评方法,的确有一定的生命力。
甚至有一度时期,新批评的影响被夸张了。1985年,广东文学讲习所所长谢望新在《学术研究》上总结当时批评界情况:“现在较一致的看法,中国‘新批评派’大概有三派,一派是上海吴亮为代表的‘审美派’;一派是鲁枢元的‘心理派’;再有一派是林兴宅等人的‘系统科学方法派’;也包括(刘再复等人)‘主体派’,如果把朱光潜、李泽厚他们较早借鉴外国美学的方法也算作一派的话,那就是四派。”如此说也未免株连过多,不过一时新批评在中国可能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青年学者姜飞的长文《英美新批评在中国》(原为陈厚诚与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一书的第二章),出色地总结了新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其中对中国文论界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代代批评家如何讨论新批评,做了出色总结。此文更精彩的地方是细评了中国批评家的“新批评式”批评实践,尤其赞赏乐黛云,刘再复,流沙河,吴福辉,王富仁,朱徽,周裕楷,康林,赵勇,吴方,程地宇,魏家骏,王连生,南帆,杨晓明,李清良,吴文薇,马力鞭,姜耕玉,林炼,陈旭光等人的出色努力。本书理应把这些师友的杰出成就一一介绍,但是篇幅不允许。幸好姜飞此章注了详尽出处,有心者还是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