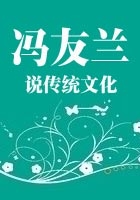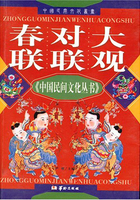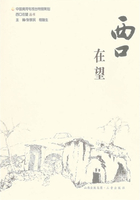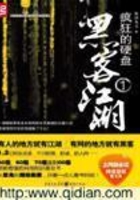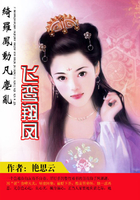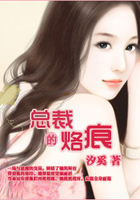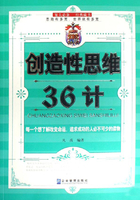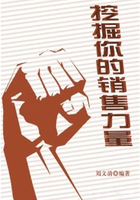贺 丹 杨盛翔
从器物的角度来看,欧洲与东方之间的交流远远超过阻隔。但是,欧洲与东方的器物交流虽几乎从未完全中断,却历经波折。事实上,正如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期,欧洲与东方的器物交流也约在同一时期迎来了转捩点,其中至关重要的无疑是新航路的开辟。该时期的欧洲国家出现了一批与东方联系密切的城市和专事远洋贸易的官方公司,东方物类由此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地,日益融入了欧洲各阶层的日常生活。
物类的价值包括其自有价值和由之承载的文化价值,故而,东方物类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方物类的使用、审美等价值的直接影响;二是由东方器物传递而来的东方文化价值的间接影响。二者互为表里,对于近代欧人生活方式、审美观念、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嬗变影响显著。
一、东方物类丰富了欧洲人的饮食文化
若无来自东方的馈赠,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仍将忍受索然寡味的菜单。东方提供了大量西欧所需的调味品、蔬果、食物和茶叶等饮品,使得欧洲人的餐桌焕然一新。并且,随着餐桌器皿的引入,上菜顺序、餐盘摆放、用餐举止等餐桌礼仪愈发考究,欧人在饮食习惯和生活的行为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香料
香料在古代生活中不可或缺,可欧洲却天然远离东方香料产地,远行的罗马旅人和军队曾一度品尝到东方香料的芬芳。东方香料在中世纪晚期的再次出现大大愉悦了欧洲人的味蕾。在中世纪,香料已经成为非常贵重的商品,价值几乎与黄金相当。胡椒、豆蔻、生姜、桂皮等经过漫长的商路抵达欧洲市场,均以药剂师的天平予以称量,甚至以粒计价。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和城市中,香料还作为货币使用,胡椒就曾被用来记账、估定税收,以及买卖土地和置办嫁妆。
众所周知,打破威尼斯对东方香料的垄断是新航路开辟的重要原因。1498年在卡利卡特被人问及需要什么时,达·伽马留下了那句著名宣言:“基督教徒和香料”。这首支抵达印度的西欧船队满载生姜、肉桂、胡椒、丁香等香料于1499年凯旋,在其抵达里斯本的当月,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便急不可待地在给西班牙共治者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通报信中夸耀在印度发现了充足的香料。而转投西班牙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尽管殒命菲律宾,船队中唯一剩下“维多利亚”号却从摩鲁古群岛满载丁香凯旋,不仅补偿了舰队的损失,还获利颇丰。那时几乎所有提及亚洲的欧洲著作家都要谈到香料群岛。
新航路开辟后,香料开始大规模地涌入欧洲,从而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口味。今日的西餐精于调制,但中世纪西欧烹饪技术却因香料匮乏而乏善可陈,盐和蜂蜜构成了主要的调味品。生姜、胡椒、豆蔻、肉桂、丁香等东方香料被源源不断运回,极大地丰富了西欧人的食谱,带来了烹饪术的重要突破。当时,几乎每道菜里都会加上香料,香料还被用来制作各种花样繁多的沙司。不仅是主食,甜点和酒类中也加入香料而变得饶有滋味,香料变成烹饪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撒上胡椒的禽肉、用生姜提味的美酒、拌入肉豆蔻的酱汁等,让欧洲人欲罢不能;除了味觉上的改进,我们还会在当时的烹调手册中看到“加藏红花上色”、“拌点藏红花使搅拌物上红”之类的调色指示。先前独揽东方香料贸易的意大利人最早着手改进烹饪技术,此时的法国人则继承了意大利人对满足味觉神经的追求,法国大餐的雏形于此时形成,为来客提供经过精巧烹饪的食物成为法国贵族彰显身份的重要法门。
今天的史家在总结西欧国家14到16世纪的烹饪发展时认为,这一时期的特色正是使用了东方香料,上流阶层将越洋而来的香料恣意投进食物以满足自己对色香味的全面渴求。到17世纪,当市场上的香料已较为充裕,欧洲人的味蕾业已满足时,食物中的香料用量才开始下降。但以法国为例,研究显示,该时期法兰西厨师虽然在香料用量上有所收束,但胡椒、丁香油和肉豆蔻等香料却得到了更频繁的使用。东方香料至此已完全融入西餐文化,成为欧洲人司空见惯的日常风味,无人再去刻意贪食它的异域滋味,熟练使用香料的厨师们已经开始绞尽脑汁挖掘其中的别样风味了。
(二)蔬果及粮食作物
相比于香料甫一登场的惊艳,蔬果及粮食作物的西传看似平淡许多。众多东方的蔬果和粮食作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引种到西欧,悄然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
对此最有贡献的是阿拉伯人。在盘踞南欧的数个世纪里,阿拉伯人为西班牙带来了新的葡萄品种,希腊罗马人又把葡萄移植到高卢和莱茵河两岸。菠菜也是由阿拉伯带到西班牙的,依照11世纪末西班牙的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上所说,当时西班牙就有人种植菠菜。菠菜随后从西班牙传播到欧洲各地。阿拉伯人引进的新品种作物还包括柑橘、石榴、柠檬、甘蔗、棉花等。然而欧洲人其实极少注意蔬果准确的东方起源,随着时间流逝,它们更进入了欧洲本地水果的名目下,东方身份根本不再为普通人所知。例如地中海沿岸通过波斯、亚美尼亚从中国引进了桃和杏,欧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称桃为“波斯梅”,称杏为“亚美尼亚梅”。
欧洲的甘蔗种植及制糖技术是从阿拉伯传入的。公元8世纪,甘蔗传入西班牙,首先种植在皇家花园里。随后,甘蔗种植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扩展至东部地中海沿岸的巴伦西亚和葡萄牙南部。十字军东征又促进了甘蔗种植和制糖业的传播。糖作为重要的添加剂,和香料一样,使食物更加美味。它的另一大效用是直接促成了可可、咖啡、茶这类咖啡因刺激性饮料的流行。咖啡和茶的东方原味一开始并不能取悦欧洲人,加糖后的咖啡和茶却立刻风行开来。在18世纪,糖最终在整个西欧完成了由奢侈品向大众消费品的蜕变。随着欧洲制糖业的发展,糖的产量不断提高,各式各样的甜品、糖果纷纷出现。糖与香料的广泛使用,直接造就了欧洲人延续至今的饮食习惯。
一起出现在欧洲人菜单里的还有稻米。16世纪的一本葡萄牙菜谱中提到了一道日常甜点——牛奶布丁,烹调材料中便有稻米。作为今日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起源于中亚的干旱山谷,其栽培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欧洲从古代开始就从印度洋方面进口大米;在中世纪时期,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稻米贸易十分兴旺。中世纪,阿拉伯人将水稻引种到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的稻种早先便沿着商路进入了意大利,15世纪水稻种植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北方,比萨周围的平原1468年有了稻米,在伦巴第平原则是1475年。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提倡种稻,在伦巴第普遍推广了水稻栽培技术,他的模范农场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水稻最终在近代早期成为了欧洲南部沿海地区普遍种植的一种重要粮食作物,并通过阿尔卑斯山口出现在维也纳的市场上。
东方输入的蔬果和粮食作物丰富了欧洲人的餐桌,逐步在欧洲人的饮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蔬果类植物同时也有药用价值,这有助于改善欧洲人的健康状况。
(三)饮料
17—18世纪,深刻改变欧洲人生活习惯的东方饮料当属茶叶。关于茶叶出现在欧洲的时间,国内外学者莫衷一是。但比较确定的是,欧洲最早提到茶叶的人是威尼斯作家G. 拉穆西奥(Giambattista Ramusio),他在16世纪中叶出版的《航海和旅游》一书中提到chai catai(中国茶)一词,并且对茶的产地、使用方法和功效等做了基本介绍。16—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对茶叶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如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都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及茶叶。而茶叶最早见于英国文献记载是1615年,那是东印度公司职员威克汉先生于1615年6月27日在日本写给在米阿考的伊顿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一包最醇正的茶叶”。
真正将茶叶作为商品输入欧洲的是荷兰人。1610年,荷兰人在中国浙、闽、粤沿海城市购买的商品中就有茶叶,这是茶叶运回欧洲最早的记载。最初入欧的茶叶是绿茶,1640年荷兰人又从中国运回了红茶。据资料显示,欧洲人早期也从日本购入了茶叶,荷兰汉学家居斯塔夫·施莱德尔博士在1650—1651年的海运货物清单中发现,日本茶以提亚(Thia)的称呼进口到了阿姆斯特丹。在荷兰,茶叶初期被放在药店出售,到17世纪70—80年代才出现在食品店中。随着茶叶的不断进口,茶室也应运而生,荷兰人不仅习惯于早午晚喝茶,而且还学得了中国以茶待客的礼仪。
欧洲诸国中受茶叶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属英国。中国茶叶作为重要的进口商品大量输入英国则是在17世纪70—80年代后。茶叶在最初进入英国本土后并没有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1658年9月伦敦出版的一份名为《政治快报》(Mercurius Politicus)的报刊上刊登了一则鼓励饮用茶叶的广告,伦敦的一所咖啡馆店主托马斯·盖勒维在出售茶叶的广告中说:“优质的中国饮料,得到了所有物理学家(笔者怀疑此处是译者将医学家physician误读成了physicist)的好评,中国称之为茶,在伦敦皇家交易所的苏丹人咖啡馆有售。”
茶在英国一度被置于奢侈品行列,茶更是于1664、1666年两次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礼物贡给查理二世。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99年获准进入广州直接购买茶叶前的近一个世纪里,都只能寄望于前来爪哇、长崎等国际市场的数量有限的走私商贩。到18世纪20年代末,茶叶更是代替了丝绸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大大增加,其售价在英国也相应地逐步下跌。
到18世纪下半叶,饮茶才逐渐在英国社会普及。茶叶从最初在咖啡馆代销转变为在专门的茶店出售,甚至可以在街边随处见到小商小贩售卖泡好的茶。茶叶的输入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习惯,下午茶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茶叶在欧洲人饮食中的重要性,搭配蛋糕甜点等食品的下午茶不仅使人振奋了精神,而且补充了能量。不单单是下午茶,英国人一天之中分多次饮茶。纵使是在英国乡间,茶也不分早晚成了唯一的饮料,习惯了茶碱的人们甚至在晚餐时也大量饮茶。18世纪下半叶时,普通工人阶层花在购买茶叶和糖上的开销约占家庭总开支的十分之一。可见,此时茶在英国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瓷茶具作为饮茶礼仪的载体也随着茶叶的西传一同进入西欧,茶叶贸易造成的另一效应就是中国瓷茶具成为欧洲百姓家庭的日用饮具。1760年丹麦的东方贸易公司共订购中国欧式日常用具28类共3284000余件(套),其中茶杯就有3073000余件。我国著名的宜兴紫砂壶也曾在17世纪由荷兰人首先输往欧洲并广受好评。
饮茶先在荷兰和英国蔚然成风,后迅速传至西欧各国上流社会,最终在近代晚期成为风靡西欧各阶层的流行饮料。欧洲人对中国茶进行了改造,掺入糖、奶、柠檬、冰等配料,使之符合自身口味。红茶和绿茶在英国最为盛行,法国人最常饮用的是红茶、绿茶、花茶和沱茶,一般采用冲泡和烹煮的方法,与英国红茶的冲泡法类似。英格兰人午后进茶点的习惯约于1840年始于贝福德公爵夫人,后来下午茶成为了英国的一大国民习惯,甚至在其他各国流行开来。对于下层工人阶级来说,茶叶这种微量咖啡因饮料在添进牛奶和白糖后即成为有效的提神饮料,“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儿干下去”,可以说,英国工业的腾飞与工人的汗水和茶叶密不可分。就这样,来自欧亚大陆彼端的中国茶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改变了西欧各阶层家庭的日常生活。
此外,茶还与家庭、女性饮料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咖啡馆是品行端正的妇女们的禁区。相反,饮茶虽然在男性中也很流行,但是被看作是贵族妇女的身份标签。亚洲的茶叶成了女性的性别符号,英国社会曾一度认为男性饮茶会导致气质的女性化。“女性”、“茶(及茶具)”、“私人空间”、“奢侈商品”四个词语紧密结合起来,构筑了人们从消费角度对于当时女性的想象。上层社会逐渐把由主妇主持的茶礼视作必要的待客之道,就像喝咖啡之于男性那样,品茶与女性美德和家庭伦理相联系,成为文雅社会赖以运转的关键齿轮之一。
风行西欧社会的饮茶礼仪是欧洲“文明化”的重要缩影,17世纪以来,由主妇运用典雅的东方风格瓷器主持的茶道成为一天中维系家庭成员感情和教授孩子礼仪的重要时刻。通过这一教育,资产阶级新贵们努力在自己和后代身上培养出适度、自制等有益的职业性格,绅士淑女的典型形象正是在这些重要细节中一代代建立起来。
二、东方物类引领欧洲的生活、艺术风尚
17—18世纪,随着东西贸易量的骤然增加和文化了解的深入,东方艺术风格在西欧大放异彩。这一时期,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oiserie)。Chinoiserie一词惯常的中文翻译为“中国风”,也有译为“中国热”。中国风是指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室内设计、家具、陶瓷、纺织品和园林设计方面所表现出的对中国风格的奇异的欧洲化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风的物质诠释不限于中国器物,日本的瓷器、漆器与印度的印花棉布的艺术理念均被归入这一门类,某些出口到西欧的中国漆器在形制上仿效日本风格,但也往往被欧人纳入中国风的概念中。但另一方面,中国风虽然实为多元文化的产物,但最能体现中国风艺术本质的仍为中国外销艺术品,这既由于中国艺术品的输入量大、种类齐全,也因为在17—18世纪欧洲人眼中,最为耀眼、最能吸引注意并激发想象的,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一)东方物类带来的收藏之风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收藏文化在西欧各地渐次繁荣起来,东方物类的大量输入是西欧收藏风气兴起的重要原因。瓷器、香料、宝石、丝绸等许多东方艺术珍品为西欧上流阶层和富裕市民专门收藏,我们试以瓷器为例来回顾当时的这一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