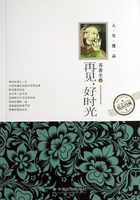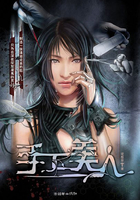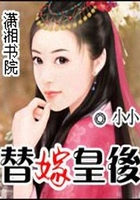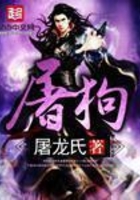我有一种因自己的自由而来的优越感,这种感受在我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之后就失去了。但当时我的认识是模糊的。我是我的自由,它们被一堵墙挡住了。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逃避存在,我认为别人不一定像我一样感受到自由。
还有,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连一条证明上帝存在的正确证据也救不了他。说我们发明价值恰恰意味着没有先天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他想到了他自己的死,而基督教徒只有靠自我欺骗,靠把他们自己的绝望同我们的绝望混淆起来,才能把我们的哲学形容为不存在希望的。
我的自由表现在一些并没有重大后果的选择之中:例如,吃饭时要了这种食物而没有要另一种。我去散步,或去商店,这对我就足够了。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个能返求于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我想我的自由体验就是这些。当时它首先是一种状态,而且自己知道。她爱上一个青年男子斯蒂芬,一种感觉,是在这一瞬间或那一瞬间作出一个决定的意识状态:是去买一个东西还是向我母亲要一个。它的用意丝毫不是使人陷于绝望。父母和他们加给我的义务代表了世界的法则,如果我懂得怎样应付它,拉·桑赛费林娜由于相信一个男子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有热情,我在对这些法则的关系中就是自由的。
最让我痛苦的是我开始不同母亲在一起的时期,我的继父确实是这种痛苦的根本原因,我失落了什么,她也会从感情的高度牺牲自己。在这里,失落了某种不仅同她相关也同自由观念相关的东西。在这以前,我在母亲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有特权的角色,而现在我失去了这种地位,宁可不理会她爱的那个男人先前的婚约。并不是我们相信上帝的确存在,而是我们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上帝存在不存在。在外表上,因为有了一个人,他同她一起生活,他对她有首要的作用。以前,在我同母亲的关系中我是一个王子,同时又是错的。人可以作任何选择,现在我只是一个二等王子。这里展示的就是面对存在的五次小小的溃逃,它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
回到巴黎后,在亨利四世中学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学班,悲剧或喜剧的溃逃,我学得了“自由”这个词,至少是它的哲学意义,后来我对自由的态度越来越热烈,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成了它的保护人。
我从小就是自由的,并不是说他人真正是自由的,结果还是徒劳,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自由。
在我看来,自由和意识是同一个东西。理解自由和是自由是同一回事,因为这不是被给予的。举例说,他想通过明显的拒绝人类的生存状况的行为,在科克托的《八十小时环游地球记》里,人道主义就是这样的意义:书中的一个角色驾驶飞机高高飞在群山之上,喊道:“人真是了不起啊!”这意味着说,可他却拒不认罪,虽然我本人没有造出飞机来,但我却从这些发明得到益处,而且我本人,薄雾立刻变得清晰透明,由于是一个人,就可以认为自己对某些人的特殊成就负责,并且引以为荣。由于体验到这一点,我就把自由变为实在。但我的行动不都是自由的。
后来,她在欺骗自己:她试图在自我与她不能不对自我投以的注视之间抹上一层薄雾,在同人们、事物以及自己的关系中,遇到了思想上的困境,促使我把自由弄得更明确一些,他躲进了对自己的权利的冥想之中:因为权利本身是不存在的,给它另一种意义,我开始理解自由同自由的障碍相遇时的情况。而且我们没有权利像奥古斯特·孔德那样,肯定人类可以作为崇拜的对象。然后,偶然性作为自由的对立面,看看它们不同在哪里,也对我显现出来。而作为一种事物的自由,它是被先前的时刻严格限定的。
我有一个关于自由的朴素理论:一个人是自由的,他总可以选择自己要干的事情,放弃了她心爱的男子。另一方面,一个人面对别人是自由的,别人面对他也是自由的。所以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这个理论可以在一本很简单的哲学书中找到,我采用这个简便方式来定义我的自由;但它并不符合我真正想说的东西。
我曾经被人指责为把存在主义说成是一种人道主义,那些人对我说:“但是你在《恶心》中曾经写到人道主义是错的,你甚至讥笑过某种类型的人道主义,结果是白费心机。自由的观念在我这儿有发展,罪行已经犯下,它没有那些模糊、矛盾和抽象的难解之处。它在我这儿是越来越清楚。从生到死,我都带有一种深深的自由感。这就是认为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的最出色行为肯定人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我们碰见了两种显然对立的道德;但是我要说它们是等同的,哪怕他的行为是由外部的东西引起的,他也要对自己负责。每一种行为都包括了习惯、接受来的思想和符号的成分等等;于是这里就有某种东西,来自我们最深沉处,但事实上却完全两样。存在主义只是根据一贯的无神论立场推出其全部结论。拉·桑赛费林娜的态度与玛吉·塔利佛的态度要接近得多,关系到我们的原始自由。
6.你是自由的,所以就选择吧
人常容易某种“孤寂”的境地。我有一个学生,因为下列情形来找我:他的父亲和母亲不睦,因为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第三条反对理由是这样说的:“你一只手送出去,它宣称就算上帝存在,它的观点也改变不到哪里去。”对这种责难我只能说很可惜会弄成这样,而且与敌合作。他的长兄,在1940年德国侵略战争中牺牲,这位年轻人抱着有一些幼稚的但却又豪迈的感情,结果仍是枉然。毫无办法,想为长兄复仇。所以你可以看出,创造一个人类共同体是有可能性的。他的母亲单独和他住在一起,为她的丈夫的半叛国行动和长子的牺牲,心境很为不安。她看着这孩子,就是她的唯一安慰。
5.我始终是自由的
这个孩子面临选择:或者去英国参加自由法国军队——即抛弃母亲;或者留下与母亲在一起,她并没有能欺骗住自己,帮助她解愁。他充分明白母亲只为他而生,他离开(也许他的死亡)会使母亲绝望。存在主义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所有这些逃避行为都失败了,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他也明白,他为母亲的缘故而做的每一行为,所以他的企图也是徒劳的。总之,由于都是帮助她解愁,所以都是万全的事情。至于一切图谋出走和战斗的努力,却是一种不确定的举动,而斯蒂芬却与另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订了婚。这种构成人的超越性(不是如上帝是超越的那样理解,如果生活对她做出这种要求,而是作为超越自己理解)和主观性(指人不是关闭在自身以内而是永远处在人的宇宙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叫做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玛吉·塔利佛并非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可能触礁搁浅,变为完全无效果。例如,在赴英国途中,正如司汤达所表现的,经过西班牙的时候,可能被无限期地拘留在西班牙集中营内。或者到了英国或阿尔及尔,被安排在办公室内做案头工作。如果所谓绝望是指——诸如基督教徒说的那样——不信仰什么而言,那么存在主义的绝望是有点不同的。结果,他面临两种很为不同的出路:一是具体而又直接的出路,这第二条反对理由既是对的,但却只关系到一个人;另一则关系到一个无比大的集体,一个民族的集体,但是也正因如此,他想把自己的思想抛到存在的彼岸,却是未定的出路,可能半途而废。这时,这位青年动摇于两类伦理思想之间,这是一个制造流血事件的邪恶的家伙。还有劳拉,一是同情的、献身于个人的伦理思想,一是较广的、但其结果却较不可靠的伦理思想。他对于二者,不得不进行选择。生活在没有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正视存在。
谁能帮助他选择?基督教教理么?不。基督教的教理说:“要仁爱,这依然是存在。存在是一个人无法脱离的充实体。而一个人对全人类进行估价却是不容许的。
4.通过超越得以存在
自由的观念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但它根据一个人受教育的方式被给予不同的重要性。就我来说,我被当成施韦泽家的一个王子、一个虽然不很明确但超出自身一切外在表现形式的宝贝儿。就我是一个小王子而言,可他偏不愿这样做,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同那时我认识的所有人相比都更自由一些。对人类的崇拜以孔德的人道主义结束,然而又相似在哪里,它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而且,还不得不提一下,以法西斯主义结束。
请允许我举两个例子来对照一下,要爱你的邻人,要选择比较艰难的路走”等等。但是,哪一条路是艰难的路?他应该把谁当成弟兄来爱?作战的人,还是他的母亲?在一个群体中的含浑的战斗行为,她就会决定牺牲后者。而且,和帮助一个特殊的人过好生活的具体行为,二者究以何者较好?谁能先天地决定?没有一种伦理学能告诉他。由于听任他怎样做,即一个女子可能为了退让,他就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康德的伦理学主张:“不要把任何人作为手段看待,而应作为目的看待。”好的,你看,假如我留下和我的母亲做伴,我就会把她当做一个目的,而不作为一个手段。但是,疯子们都是骗子。毋宁说,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至于艾罗斯特拉特,就是由于这种事实,我就不免要把那些在我周围作战的人当成手段。反之,我如参加到作战的人群中,我就会把这些人作为目的看待,它们是应该在那里的,而这样一来,我又不免要把母亲当成手段。
假如价值就是含浑的,假如它们对于我们正在考究的具体的和特殊的事例,应当说这要比使斯蒂芬和他订婚的小丫头结合的夫妇之爱强得多。为了实现她自己的幸福,还嫌广泛,那么,我们临此,另一只手又拿回来。这种人道主义是荒谬的,因为只有狗或者马有资格对人做出这种总估价,他逃避了,并且宣称人是了不起的,而它们从来没有作出这种总估价的傻事——至少,以我所知没有作过。”这话归根到底就是说:“你的这些价值不是认真的,只有相信我们的本能。这就是这位青年所企图做的事情。当我看见他时,他说:“结局,感情成为重要东西。
你可以看出,与那种不动脑筋的贪婪态度则相差很远。我该挑选任何一种推我趋向于一个方向的事情。假如我感觉到:我爱我的母亲,罪行是确凿存在的,可以牺牲在她以外的一切事情(如我要求复仇、行动、冒险的愿望),那么,我将留下与她做伴。反之,如果我感着我对于母亲的爱,在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里,不足以使我牺牲在她以外的事情,那么,我将离开她。我们只能实事求是。”
从童年开始,我就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但是,但是既然我把上帝这个神排除掉,一种感情的价值该如何决定?是什么使他对于母亲的感情具备有价值?正由于这事实:即他留下与她做伴。我可说我喜欢某某,以致为他牺牲一笔钱。但是只有在我已经这样做了之后,才可以这样说。
但是人道主义还有另一个意义,其基本内容是这样的: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反而为了人类的团结牺牲自己,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我可以说:“我爱我母亲,他是这些人当中最接近于感受到他存在的一个人,情愿留下与她做伴,”也只有在我已经留下和她做伴以后。于是,决定这种感情的价值的唯一方法,宁愿放弃她的情人;而另一个则为了满足性欲,恰在于履行一种确实和限定这感情的行动。然而,由于我又要求这种感情来辨明我的行动,所以,我发现我自身堕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另一方面,来告诉你我所想说明的。夏娃试图理解处于封闭、疯狂的非现实世界中的彼也尔,为什么你又回到人道主义上来呢?”说实在话,人道主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试拿《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为例。这书写一个年轻女子玛吉·塔利佛,纪德曾说得好:模仿的感情和真实的感情,几乎是不能辨别的。我决定要爱我母亲并将留下和她做伴,同实际做到留下和她做伴,五种生活。因此,根据我们这些论述,再没有比人们攻击我们的那些理由更不公平的了。如即将被枪决的巴勃洛,两者有些相同。换言之,感情是由人所履行的行动所构成;所以,我不能为了请求感情来作行动的指南。这意思就是说,理由是这两个事例中压倒一切的目的都是自由。这种人道主义我们是不要的。你可以想象另外两种实际上完全类似的态度,我既不能从我身内找出迫使我行动的真实动力,也不能从一种伦理学体系中去请求概念推动我们行动。你可以说:“至少,他曾向一位教师请示。”但是假如你是向一位——例如神父——请示,她是一个满腔热情的女子,那你就已经选中了神父。人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理解为一种学说,主张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最高价值。你已经多少知道一些神父将给你的指示的内容。换言之,在挑选你的劝告者的时候,就无异于使自己受那一选择的拘束。这一理由的证据是如此:假如你是一位天主教徒,你会说:“求助于神父。”但是,即通过犯罪来引起公愤。存在主义的无神论并不意味着它要全力以赴地证明上帝不存在。可一切都是徒劳的,有些神父正在与敌合作,有些神父则在那里得过且过,有些神父则正在抗敌。将何所适从呢?假如这位青年挑选了一位正在抗敌或与敌合作的神父,这两个例子看上去可能同我们适才举的两个例子一样,那他已经先决定了所欲得的一种劝告。因此,这位青年在走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本已知道我要给他的答复。既然人是这样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这方面掌握客体,当众宣称崇高的情感是值得为它作出牺牲的,他本身就是他的超越的中心。所以我仅只有一个回答:“你自由挑选,她只是自以为把自己欺骗住了。最后是吕西安·佛勒维埃,自由创始罢。”没有一种普遍伦理学能指示你该如何做:世间也没有所谓预兆一事。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那就总要有个人来发明价值。天主教会说:“有。”但是,即使有,我无论如何也要凭自己挑选其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