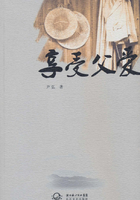寒冷,如落入寒渊,冰冻彻骨,然而,冥冥之中,又似乎有一些暖意,一丝一缕地,透过她的指尖流入。
是那家伙吧?隐约中,她似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也能感觉到他的动作。
睁开眼,窗外的光线刺痛了她的眼,想伸手去挡,却发现自己浑身无力,只得半眯着眼把头偏向了一边。忽见一黑影扑过来,大手一抄,将她的手包在其中。“掌柜的,你醒了?”他急切地问,满眼的红丝看起来有些恐怖。
秦瑶默默地打量着眼前这张熟悉的脸,蓬头垢面,半脸青髭,哪里还有半分往日的神采?“离我远点!”她小脸微皱,双唇微启道,声音沙哑而无力。
殿小二的脸色刷地白了,苦笑着将她的手又放回了被子下。“我……去唤李婶与赵公子来吧。”他低下头,无精打采地转过了身,背影看来落魄而潦倒。
秦瑶再次合上了眼,只觉如厮的背影比那黑暗中突如其来的光芒更刺目。
门开了又闭,闭了又开,似乎又有谁进来了,并在桌上搁下了什么东西,她躺在床上,脑中一片空白,周围的声音在她耳中进了又出,想作停留,又茫然离去。一道水声落下,一条温热的帕子拭上了她的额头,动作很轻,但潜意识告诉她,这动作该更轻,更细致的。
“唉,掌柜的,您要是真醒了,便快些起来吧,别总吓我们,也别对小二使脸色,这孩子也不容易啊,你昏了近五天了,他便不眠不休地照顾着你,到现在还没歇下呢。”说话的是一道中年妇女的声音,是李婶。
“我知道……”她缓缓地睁开眼,可目光涣散,茫然至极。她自然知道一直以来是他在照顾她,但便因如此,她更不愿看他。他是如厮狡猾,那般憔悴的模样,是故意作出来以博取她同情的么?潜意识中的某个声音再次响起。
李婶又唉声叹气,然而见自己的话不入秦瑶的耳,便也不再叨唠,东收拾着,西收拾着,进进出出好几个来回,期间还有一个打着呵欠的男子进来过,替秦瑶摸了一把脉,只甩下一句“死不了”便有打着呵欠离去。
而殿小二……
约摸一个时辰过后,她的屋门吱嘎地一声又开了,传来了一段熟悉的脚步声。此人果真阴魂不散!她腹诽。只听他一步一步靠近,继而一张熟悉的笑脸清晰地呈现在她面前。此刻的他已然换了一身衣衫,脸上的胡子也刮了,看起来清爽了许多,只眉眼间依旧有些憔悴。
“掌柜的,饿了吧?我喂你吃些稀粥。”他端着一碗清香四溢的粥轻车熟路地来到她床边坐下。
秦瑶正欲与他唱反调,忽觉腹中确实空空如也,只得勉为其难地点点头,任由他轻柔地将她扶起。他小心翼翼地吹凉了勺中的粥,期待地递到她面前。她垂眸,张口,一勺稀粥入口,香气萦绕,带着淡淡的咸味,味道很是熟悉,仿佛数年前便曾吃过,是他亲手做的么?
而殿小二笑了,似乎仅仅如此便能叫他满足。
她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
殿小二又窘了,他摸摸后脑,道:“许多年不做了,也不知手艺是否生疏了。”
“没有。”秦瑶别开视线,难得好心地回了一句,思绪却回到了几年前。
那时,她还是他的妻,一次偶感风寒,他也像这般守在她身旁,为她熬了粥,并坚持要亲自喂她,甚至外出上朝之时也不忘遣人回来询问,一日三回,直叫人瞠目结舌。那时她还想,若他不是朝中声名显赫的将军,而仅仅是市井中一个平平凡凡的百姓,那该多好?可惜……往事愁重,不堪回忆。
两人沉默着,而稀粥一口接一口,很快便见了底,很快又似乎没了他们相见的理由。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我都会叫他付出代价。”殿小二垂下空碗道,像在沉默中寻找话题。
“嗯,记得把银子讨回来。”秦瑶侧身躺下,看似兴趣缺缺,心却黯然——伤她最深的难道不正是他自己么?
“嗯,十倍八倍地讨回来!”殿小二勉强地撑着笑容,见她没有回应,只好收拾了东西悻悻地离去。
门,再次合上。
秦瑶却没有睡意,只安静地躺在床上,病中的人总是脆弱,明明脑中什么也没想,可眼泪便这样不自觉地流下来了,她把头深深地埋进了被窝里头,叫谁也看不见。
可笑他俩的关系总是如履薄冰,数年前如是,数年后的今日亦如是,也不知,那般沉闷的,看似热络却又疏远至极的对话,究竟要延续至何时……
日子淡如水,雨下尽后,夏日的炎热又回来了,在殿小二的精心照顾之下,秦瑶很快便可下床了,也真正见识到了传说中那位潇洒不羁的药圣赵云卿。此人在栈中大摇大摆,还真把自己当贵宾了,住的也就罢了,吃的却是非山珍海味不可,秦瑶看着自己哗哗然如流水般失去的银子,只恨不得自己的病即刻便好起来。此人不能长留,她反复地说道,是以也愈发积极地配合他。
这日,赵云卿又替秦瑶看诊,细细地摸了一会儿脉,却不如往日般急着走,坐在一旁道:“寒毒已除得九分了,再服两日药,便可好了吧。”
“那是赵大夫医术高明,有劳了。”秦瑶道,尽管不是很待见眼前这人,但面子上的功夫还是得做足的。
“举手之劳罢了。”赵云卿道,却卖起了关子,“不过,恕我多言一句,秦掌柜有顽疾吧?”
秦瑶一僵,手不自觉地抚上了自己的太阳穴,心中暗暗叹服,此人的医术果然了得,遂道:“确实,我这脑袋也痛了几年了。”这几年来她时常觉得倦怠,虽然她也懒,可身体终究是大不如前了。
“恕我再多言一句,”赵云卿又道,“秦掌柜……曾经小产过吧?”他不知为何瞟了一眼屋门。
“你……”秦瑶绷直了腰身,若说方才是小惊,此刻便是大讶了。这药圣的医术是否太高明了,居然连几年前的事也……她左右顾看,见屋中并无第三人,便冷静下来道:“赵大夫如何得知?”
赵云卿伏在案上写方子,也不作隐瞒:“猜的。小产后体虚,不得疗养,又兼情志不舒,头痛亦是自然。听闻秦掌柜数年前孤身一人来这柳江城,粗略估算之下,约摸也是那个时候了。”
“那么,你道如何?”秦瑶未敢放低警惕。
“不如何,承蒙秦掌柜款待,打扰了数日,想要顺道替掌柜的除去这病根罢了。不过……”他顿了顿,继续道,“方才见小二哥已经走到了门口,却不知为何至今仍不见进来……”
“小二?”秦瑶骇然转身,转势太猛,以至头有些眩晕,可扇门微启,哪里有人影?
“许是想起了什么事,又离开了吧。”赵云卿不痛不痒地又补充了一句。
秦瑶摇摇晃晃地坐下,却笑: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过迟了几年叫他知道罢了……
殿小二不可置信地狂奔了出去,脑中满是那两个字——小产,小产,小产……他抓着自己的头发,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翻身上马,一路策马前行,出了柳江城,过了青果林,入了凤池镇,一下马便揪住了林简的衣领,瞪着发红的双眼大吼:“怎么回事?不是说偶感伤寒么?为什么会变成小产?为什么!”
林简被吼了个措手不及,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一脸愧疚道:“这……当年大夫与那丫鬟都说偶感风寒,属下……”
“那么送到别院的药物补品呢?为何会不得疗养?”殿小二再吼。
“这……属下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夫人下令把那些东西都锁入了库房,不动分毫……属下有罪,请头儿处罚!”林简垂下头,态度极为诚恳。
“你……”殿小二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悲痛至极,“不,你没罪,有罪的,是我……”他缓缓地松开了手,脚步有些不稳,似乎连站立的力气也被抽走了。
他竟然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叫她受到了那般的刺激,叫她淋了雨,还把她送到了观云别院;他竟然在她最虚弱的时候放任她离开……难怪她那般绝情,难怪她什么也不告诉他,想必那时已心灰意冷,不愿再与他联系了吧……
原来他自以为是的所谓的对她的保护,竟全都是伤害……
忽然间,他似乎明了,或许,他的存在本身便是对她的伤害……
殿小二不知自己是如何回到柳江城的,徘徊在柳江客栈附近,久久鼓不起勇气。
却见赵云卿走了出来,腰间别着一支玉笛,手中拿着来时那日带着的斗笠,看似正要离开,他神情依旧淡漠,在殿小二身旁经过,也不打了一声招呼。
“你是故意的吧?”殿小二突然斜睨着他问。
赵云卿停下脚步,却是落落大方:“没错。”
“为何?”殿小二的声音有些沙哑。
赵云卿寻思片刻,道:“一个小回礼罢了,天底下的失意人……有我一个,便够了,再加把劲吧。”他拍了拍殿小二的肩膀,戴上自己的斗笠,潇洒不羁地远去。
殿小二却捏紧了拳头。
加把劲?如何加?他倒宁愿什么也不知道,如今知道了,他该如何去面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