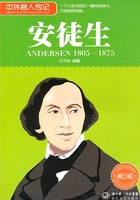天色阴沉,嘀嘀嗒嗒地下着雨,夏日的暑意仿佛都被这水气给掩盖了,身子单薄的人甚至还得多添了一件外衣。
“大夏天的,都断断续续下了一整天了,怎么还不停!”李婶抱着一盘子站在后院的屋檐地下抱怨。
李叔则蹲在厨房门前磨刀,“嚯嚯”地一声声,他眉头微蹙看,看起来亦是心烦意乱。
客栈歇业已经两日了,这两人的脸上却从未露出过笑容,倒恨不得找些什么来叫自己忙碌起来。
“别只管着抱怨,水开了。”李叔低着头沉声说了一句。
李婶顿然悟过来,赶紧跑了进去,嘴里却依旧在抱怨:“哎,都怪这雨声!”
秦瑶已经昏去三日了,药圣还没来,她全身冰凉,只叫握着她的手的殿小二心如刀绞,他双眼布满红丝,下巴处胡渣青青,也不知多久没阖眼了。
斜风怂恿着雨水飘进了屋中,殿小二赶紧跳起来将窗户牢牢地合上,生怕那飘进来的水气侵袭了床上的人儿,一会儿又觉屋里闷得紧了,又轻轻地推开了一条小缝,叫那新鲜的空气徐徐灌入。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一整天,这窗户也开开闭闭地不知被他折腾了多少遍。
他探了探桌上的药碗,觉得已经不烫了,便仰头含了一口,低头覆上了秦瑶的双唇,药汁缓缓地流入,所幸的是,她还能咽下这药汁。
药汁尽数流入了秦瑶口中,殿小二却舍不得起来了,望着她纤长的睫毛,流连着,轻吮着,她唇瓣冰凉,他口中仍满腔苦涩,可这些又岂能比得上他心中的苦?他回顾着近来发生在两人身上的一切,却始终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叫他们渐行渐远?他为她抛弃了一切功名利禄,甚至,连尊严也抛弃了,难道还不够么?
蓦地,他像想起了什么,猛然地抬起了头,抚着额头感慨:“唉,我究竟在做什么!”他懊恼地静坐着,双眼一睁一闭之间,目光自然而然地又往秦瑶脸上飘,片刻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端起药碗,再次以口渡药。
端着热水进屋的李婶正巧看到了这一幕,不由地大吃一惊:“哎哟,小二,你这是……怎能趁掌柜的病危,占她便宜呢?”
殿小二亦被吓了一跳,险些将碗中的药洒出,却搁下了碗正襟危坐,若无其事睁着眼。
李婶与他对视了一阵,只得摇头叹道:“罢了罢了,掌柜的这模样,也只有这办法了。你也该去歇歇了,待我替掌柜的擦擦身子。”
然而殿小二却依旧端坐着一动不动。“我来!”他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
李婶不得已又惊了:“你这……男女授受不亲,如何了得?若掌柜知道了,指不定真把你赶出客栈。”
殿小二还是不动,目光清澈,坚定不移地看着李婶。
李婶只得又道:“小二啊,我知道你心疼掌柜的,不想假他人之手,可这……唉唉唉,好吧,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不插手便是。”她摇头晃脑地搁下热水,知趣地走了出去。
殿小二却不见得高兴,望着水面上袅袅腾升的蒸气,目光黯淡了,须臾,又是一声长叹,他用帕子沾了水,拧干,小心翼翼地擦着秦瑶的手,仿佛在擦着一件无价之宝,连甲缝也不落下,而后便是她的脸,她的颈……他把手深入被中欲解她的衣衫,可手才碰到她的腰带便停住了。
“唉,掌柜的,您要是再不醒来,我可真把你的衣服给扒光了。”他故作轻松道,仿佛床上之人只是在跟他开玩笑,只要他稍微一捉弄,她便原形毕露。
可他终究得失望的,怏怏地撤回了手,垂头丧气地步出了屋门,许是找李婶去了吧。
傍晚时分,栈外来了个身披蓑衣戴着斗笠的男子,此人便是江湖中大名鼎鼎的药圣赵云卿,他长身玉立,腰间别着一支玉笛,年纪不算大,但神情却很是淡漠,一进门,也不打招呼,便径直问:“中毒之人何在?”李婶喜上眉梢,急忙将他带入秦瑶的屋子。
屋中,赵云卿与殿小二相视了一眼,皆未作言语,殿小二识相地让开了床边的位子叫他看诊。
赵云卿摸了一会儿脉,眉头蹙了又松,松了又蹙,看似遇上了什么难题。
殿小二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既不制止,也不过问,只是目光中带着浓浓的警惕。药圣之名他自然听过,都说他独行于江湖,行为乖张,但凭喜好,确不是那等奸恶之徒,只是,此人若与孔令岳相关,便得另当别论。
只见赵云卿自怀中掏出了一个精致小木盒,打开木盒,里面装了数十支长短大小不一的金针。他抽出其中一支金针,正要替秦瑶施针,殿小二攻其不备的出手了。
“阁下意之如何?”赵云卿瞥了一眼挡在自己面前的手,看神色似有些不悦。
殿小二笑问:“素闻药圣光明磊落,如何要替那等鼠辈办事?”
“鼠辈”赵云卿有丝不解。
“总躲在背后暗箭伤人,不是鼠辈是什么?”殿小二又道,他依旧不相信孔令岳那套“把药弄混了”的说辞。
赵云卿思索片刻,忽地嗤笑一声,不知是否认同了,却道:“我不过还他一个人情罢了,你们的恩怨与我无关,我行走在江湖只做两件事——救我想救之人,杀我想杀之人。若因我的药而伤及了无辜,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阁下若不想延误救人的时机,还请收手吧。”
殿小二垂眸,迟疑着松开了手,左右如今能救秦瑶的也只有眼前这人了。“方才是在下多疑了,多有得罪。”
赵云卿不回话,只拿起金针继续施针,三针落下,却问殿小二的内力属阴或属阳,殿小二只道属阳,便令其配合着他的针法与秦瑶输送真气。
一晃眼便去了半个时辰,赵云卿将金针拔出,总算告了一段落,而两人额上都已挂了汗。
“如何?”殿小二收回了内力,心急如焚地问。
赵云卿道:“寒毒深入,要治起来不容易,但方才你我已将其逼出体表,余下只须药石便可。我会在这栈中待到她痊愈之后再离开,只是,我要最好的客房与最好的菜肴!”
殿小二一听秦瑶有救,早已喜出望外,他搂住秦瑶道:“无妨,只要能救她,整一间客栈空出来让你住亦可。”
赵云卿有意无意地瞥了他一眼,漠然地收拾了金针,离去。
窗户不知何时被打开了,一颗脑袋探了进来,眼中闪着崇拜的光芒。“杀想杀之人,救想救之人,多潇洒,多令人羡慕啊!”
殿小二皱着眉头地瞪了他一眼,默默地为秦瑶盖上被子。
杜潮守所言有理,孜然一身,潇洒来去,赵云卿确实叫人羡慕。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江湖中又何曾真正缺少那些惬意之人?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知谁近来曾说过的这句话突然间浮现在他脑中,他不自觉地看向了秦瑶,又看向了自己。
庸人,指的是他们么?
“秦瑶,我只是不明白,为何你对当年的事如此耿耿于怀?为何你偏偏纠结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