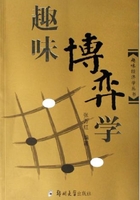“你!快进来住店!”顾红翎站在栈门处吆喝,吓得栈外路过的行人一溜烟似的跑了个没影儿。
秦瑶不由地轻叹,只觉头又痛了起来:她这究竟是招客人还是赶客人啊?
不过,这顾小姐的到来还真的为客栈招来了一些生意,当然,大多数客人都是来落井下石的,过去受尽了她的欺凌,如今正是报复的好机会,又岂能错过?遂变着法子折腾她。两日下来,栈中不知传出了多少句诸如“本小姐给你斟茶递水你还敢拿乔?”又或“你们这些杂碎,日后最好别落在我手里!”此类的话。
秦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她,左右这遭过去了,这事便再与她无关了。这大小姐倒也坚强,不若别个大家闺秀般哭哭啼啼,李叔跟殿小二漠视她,李婶对她恶言相向,甚至把栈中新近才洗过的被褥也扒出来让她再洗一遍,她还是咬牙撑着,抹干了眼泪干活,愣是没有再提离开,待熟悉了环境,居然又嚣张起来了,竟千方百计地与秦瑶作对。
就好比此刻,栈中暂无客人,殿小二抱着几坛酒自内堂走出来,顾红翎见状,立刻迎了上去,斜睨了一眼秦瑶,状似亲密地伸出手,想要接过他手中的酒:“二哥哥,我来帮你。”
殿小二不悦地皱起了眉头,避开她的手,斥道:“我说过,大堂是我的地盘,回你后院去!”
顾红翎却似不懂察言观色,继续道:“二哥哥,你又何必见外?前几日若不是有人阻拦,你我二人此刻已然是夫妻了。你又何必恋着那人老珠黄地女人?我比她漂亮,更比她年轻好几岁,二哥哥,你真的不考虑?”
秦瑶听着两人的对话,忽觉一阵烦躁不安,重重地拨了一下算盘,开口道:“顾小姐说得不错,我确实人老珠黄了,老得连活儿都干不利索了,所以……后院的茅厕最近有些脏了,能劳烦您去洗干净么?”
“你,你居然要我去洗茅厕?”顾红翎不敢置信地提高了声调。
秦瑶却一脸平静:“怎么,身为客栈的工人,不过是去洗个茅厕,难道很委屈?令尊既然让你在这儿历练,我自然不敢怠慢。”
“你!”顾红翎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你……秦瑶,你好样的!”她嗔了一声,一路推桌掀椅地跑了进去。
殿小二自动地闪到一边,以免被殃及,一扭头,对上了秦瑶的视线,他张了张嘴,道:“那个,此事与我无关。”遂背过身,继续干活,看似在逃避秦瑶的眼神。搁下手中的酒后,他的动作有片刻凝滞,像在考虑着什么,一回头,却看见秦瑶又在揉太阳穴,不禁双眉一蹙,眼中露出了一丝心疼。他犹豫了一阵,问:“李婶说,你近来时常头痛?”
秦瑶抬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嗯。”
“是因为,我逼得你太紧么?”他忽然又扬起头,上前两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
秦瑶顿了顿,讥笑:“你倒挺有自知之明,怎么,要放弃?”
殿小二再次愣住了,目光瞬间又黯淡了下去,他沉默了良久,最后,却只扬起了一抹轻笑。 “怎么可能?”他轻轻地吐了一句,便钻进了内堂。
大堂顿时安静下来,秦瑶却无心再看帐,呆然地望着堂中散乱的桌椅。“也不知道把大堂收拾好才进去!”须臾之后,她抱怨似叹了一口气。
顾红翎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水桶,怒气冲冲地撞开了茅厕之门,还没跨进去,便屏着呼吸退开了数丈,强忍着胸中汹涌的“暗潮”,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给我仔仔细细洗干净了!”路过的李婶吆喝了一句,依旧没有给她好脸色。
顾红翎皱着脸嘟囔了一句,只得掏出一条帕子包住了鼻子,拿起工具继续向茅厕“进攻”。
刷子沾了水,一下下地刷了起来,然而墙上的污垢颇厚,许久也不见干净。顾红翎一边刷一边低咒:“该死的老女人,居然公报私仇!”她厌恶地盯着刷子,水换了一桶又一桶,可墙上污垢依旧不尽,她心中的不满越发多了,最后干脆竖起刷子发起狠来:“居然要姑奶奶我洗茅厕?好!我就要你一辈子蹲在茅厕里出不来!”
她装模作样地又刷了几下,拿水随便地冲了冲,便收起了工具溜出了客栈。
“伙计,给我拿一包巴豆粉!”她一股劲儿跑到了附近的王家药铺道。
药铺的小伙计被她吓了一跳,诺诺然道:“好……好嘞,顾小姐稍等。”转身便入了里屋。
这小伙计一进去便是老半天,顾红翎等得极不耐烦,不住地往里头张望,忽见人影一晃,出来了一个人,这人却不是那小伙计,但也不陌生。
“是你?你在这作甚?”顾红翎疑惑地问,对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男子还有些印象。
孔令岳扬起一抹浅笑,拱手道:“难为顾小姐还记得在下,孔某实乃三生有幸。”
顾红翎皱了皱眉,似乎有些反感:“我问你在这做什么呢,谁让你说那些了?”
孔令岳依旧笑道:“这……恕孔某失礼。日前一位故人托药铺的王掌柜与在下带了些灵药,在下此番正为此事而来。”
顾红翎乜斜了他一眼:“早说便是,啰嗦个什么劲儿!”
孔令岳闻言,但笑不语。恰逢那小伙计走出来,顾红翎一把夺过巴豆粉,也不道别,扔下几个铜板便脚步匆匆地离去。孔令岳看着她的背影,摇着头无奈地放大了脸上的笑容。一侧身,却问:“如何?”
小伙计道:“回庄主,事情已办妥,庄主大可放心。”
孔令岳满意地点点头:“好,回去找管家领赏吧。”又把扇自语:“这位顾小姐,倒比我想象中更可爱!”他抬头仰望青空,不知在勾勒着什么。
是夜,秦瑶的头又痛了起来,便叫李婶替她煎一碗药来,顾红翎一听,不禁大喜,只道天助她也,遂趁李婶不注意,偷偷地将巴豆粉投入了药中,更亲自把药端进秦瑶的屋子里。她面上还是堆满了不情愿,可心里却满是期待,想要一睹秦瑶捂着肚子呼痛,急奔茅厕的模样。
“药!”她重重地把碗搁在桌上,而后站在一旁恶狠狠地瞪着秦瑶,戏演得十足。
秦瑶睨了她一眼,不疑有他,端起药慢条斯理地喝了下去。奸计得逞,顾红翎的朱唇不自觉地扬了起来,险些败**谋,好在秦瑶并未留意。
“还不走?”秦瑶莫名地抬头看她。可她哪里舍得错过好戏?磨磨蹭蹭地半天也没踏出房门。
忽见秦瑶脸色一变,手捂住了胸口:“这药……”她一脸痛苦,仿佛说两个字也要夺取她极大的力量。
顾红翎得意了起来,心道:总算来了!却又纳闷,这腹泻该捂着肚子才是,她为何捂着胸口?
秦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额上满是汗珠,忽地发出了一声闷咳,竟吐出了一大口黑血。“你……”她的声音极为虚弱,似乎想要伸手指着顾红翎,可手才抬了一半,人便倒了下去,顺带着打翻了桌上了药碗,“哐啷”地一声,仿佛碎在了人的心里。
顾红翎慌了,事情完全超乎了她的预料。她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实在不解,区区一包巴豆粉,为何会……“你,你怎么了……”她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可是无人回答。
殿小二闻声赶来,见此情形不由大骇,冲过去便将秦瑶揽入怀中,焦急地呼唤着:“秦瑶!秦瑶!”可怀中之人依旧不省人事,她浑身冰冷,面色青紫,唇角还带着血迹,只呼吸仍微弱着。“究竟怎么回事!”他怒喝,双眼大睁着,里面布满了血丝。
顾红翎早已吓得不敢吱声,只站着一旁哆嗦。
李婶亦随后来了,甫进门便大惊失色:“作孽!方才还好好的,怎么喝了一碗药就变作了这模样?得赶紧叫老头子去请大夫。”便又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
片刻后,大夫来了,脉上一诊,脸色亦变了,问道:“秦掌柜可是服了些大寒之物?”
“只是服了些治头痛的药物,还是大夫您亲自开的药方呢。”李婶道。
大夫检查了药渣,不住地摇头:“不可能,定是有些别的药物!你们可曾在方中添了什么?秦掌柜体寒,如今再服下大寒之物,便是雪上加霜,性命岌岌可危啊!”
“确实不曾添什么。”李婶摇头道。
殿小二却目光犀利地看向了顾红翎。顾红翎更慌了,支支吾吾地开口:“我……我……我只是在药中投了些巴豆粉……”
“果然是你!”殿小二眼中迸出了浓浓的恨意,叫人望而生畏。
却听大夫道:“巴豆性热,按理不应如此。”
殿小二更怒了,又瞪向顾红翎:“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顾红翎吓得脚一软,跌坐在地上,只得带着哭腔将药铺之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我的真无心要她性命,我只是……只是想让她尝点苦头……”
“都下药了,还无心,小小年纪,心肠怎么如此毒辣!”李婶大骂。
“巴豆本是毒药,致泻也就罢了,若过量,照样取人性命,你这姑娘真是,怎能拿这些来开玩笑!”大夫似乎也看不惯顾红翎的行径,却只能摇头轻叹:“如今这状况,老夫怕是无能为力了,只能开个方子续秦掌柜几日命,小二哥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大夫提起药箱,唉声叹气地随着李婶走了出去,顾红翎仍在抽泣,殿小二气愤地一拳打在身旁的柱子上,像在仇恨,又像在自责,他咬牙切齿地吐出了三个字:“孔、令、岳!”仿佛已经断定了是他从中作梗。抬头看见顾红翎仍在,不禁再次怒喝:“滚!秦瑶若是出了任何差池,我要你碎尸万段!”
顾红翎一听,只惊得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脸上泪珠滚滚——她是真的无心取秦瑶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