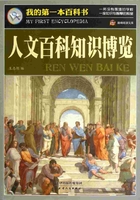她把云敛给的契约都给了赵文艳,赵文艳看见那些契约时,顿时红了眼眶,得知是云敛给她的之后,起初并不肯收,在景笙强硬态度下才说是帮景笙保管,同时递给了景笙一个小腰牌,说以后遇到东家的店铺都可以用,还硬塞给了她些地契。
景笙推脱不过,最后选了这两张。
海外瀛洲,《十洲记》上记载瀛洲在东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为玉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洲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山川如中国也。
想来是个不错的地方。
岭儿见了地契,知道景笙并非玩笑,事实上在这些大事上景笙一向不开玩笑。
“小姐,你不去和老夫君他们道个别?”
“若有时间。”
“小姐,那我现在就去租船。”
“好,记得在城西的西江渡头。”
景笙颔首,提笔继续作画。
不知多久,画上的人已渐渐描摹成型,景笙便又点了各色颜料浅浅上色。
墨色的长发流泻,五官淡淡却恰是适宜,浓不得一分淡不得一分,玄衣修身,那人静静握着剑,站在桃花树下,艳色花瓣雪样旋舞却抢不过那人一分颜色,只见那人目光盈盈望来,弯起的眼角笑意流转,栩栩如生一般流光溢彩,直叫人……怦然心动。
能让人只凭一幅画就对画中人心动,画者从中注入的深情可想而知。
画完收笔,景笙坐在台前,怔怔望着画。
按了心口,景笙大口呼吸两声,挪开镇纸,取下画卷好,出了门。
定国将军府外,张灯结彩好不喜庆,无不昭示着主人喜事近了。
景笙深吸口气,敲敲门。
门房大妈开了门,见是她,丝毫不意外,反是预料到般道:“公子正在书库,景小姐可以去那里找他。”
景笙握紧了装着画的画轴,迈步而入。
道路很是熟悉,景笙走着,看着,不多时,已到了书库门口。
景笙抬手正要敲门,书库的门已被推开。
不期然望去,正是刚要出来的沈墨,月白长衫,仍是温润公子,气度清华。
两人视线蓦然撞见,都是一震。
几瞬之后,沈墨先反应过来,移开目光,眼神有些飘忽:“景小姐是有事来找我么?”
连称呼都生疏了么?
景笙强迫自己抑制住心里越演越烈的痛心,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轻描淡写:“是有事。”
“那不妨就在这说吧。”
“能不能……到书库里说?”
那里是她的世界,那里有他们的回忆,那里至少能她些勇气,不然她怕站在这里在他面前自己根本开不了口。
沈墨迟疑了一下,垂下睫,反手关上门:“还是去厅里吧。”
甫一入厅里,景笙便看见了满目刺眼的红。
厅中的美人榻上,鲜红欲滴的大红喜服正整整齐齐的放着,一旁还有尊贵无匹的九龙四凤冠,无数翠云珠花镶嵌,珠宝十二钿静静摆放。
只一眼,景笙就知道,那是给谁准备的,又是什么时候穿的。
再向右,是堆的满满当当的贺礼,各种锦盒、宝盒精致华美不一而足,高高一座,煞是惊人。
她看向沈墨,沈墨却不在看她,沈墨实在聪明,这些……是用来让她知难而退的么?
那一瞬,景笙心里自嘲声涌上,负面情绪淹没,几乎要放弃,然而,手指触到画轴,她没法不忆起这画中的心血,和她……不愿放手的心。
自取其辱又如何?
景笙把画举到胸前,缓缓递了过去,一字一顿:“小墨,这是给你的。”
沈墨何其聪明,这副画里的感情,她不信沈墨看不懂。
等了好一会,才听见沈墨的声音:“这是补给我的生辰礼物,还是……贺礼?”
这一句话,比之利剑也不差,足把人心刺了个对穿,景笙蓦然抬头,眼睛里凝着复杂到分辨不清的情绪,深情,痛心,受伤,甚至还带着一丝丝的绝望,几乎叫人不忍观。
然而,沈墨并没有看她。
“生辰礼物的话就算了,贺礼的话……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景笙听见自己的声音,如此涩然:“你不看看是什么么?”
“我想……大概已经不用了。”
景笙终于压抑不住:“为什么不用了?沈墨,告诉我,你是真的心甘情愿要嫁给太女一生一世么?”大概连景笙也没有发现,这声音里带着多少的恳求和挣扎。
依然是良久的无言,沈墨叹了口气,转过身,白玉般修长的手捻起喜服一角,那一双拿剑的手此时却显出一种无力的感觉:“嫁给太女为正夫大概是全皇王朝大部分男子毕生的愿望,又有什么心不甘情不愿的?”
景笙音调增高,却又一句比一句的忐忑,直到最后,声调已复降下,温柔又温弱。
“小墨,如果不是心甘情愿为什么还要嫁?”
“小墨,你信我么?”
“小墨……跟我走好不好?”
沈墨凝视着大红的喜服,视线似乎胶着在上面。
一个模糊的音节从沈墨口中溢出,音调却显得很奇怪:“走?”
景笙点头,脸上挤出笑容,语气恳切,眼睛里隐约有些不顾一切的味道,声音却意外的定了下来:“……明晚戌时,我在城西的西江渡头等你,不见不散。”
“景笙,我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不负责任的人……你的家人我的家人呢?”
景笙看着他,目光丝毫没有退却,而是又重复了一遍:“小墨,你信我么?”
身上的伤口和着心痛阵阵袭来,景笙浑然未觉:
“我可以担保无论是你的家人还是我的家人都不会出事,只问你愿不愿意。”
“我等你……”
景笙漫步走了出去,走得很慢,步伐也不复寻常不紧不慢。
沈墨一直没有回话。
待景笙的背影彻底消失在了转角处,沈墨的视线才移到景笙送来的画轴上。
手指抚在画轴上,沈墨静静呆看了良久,才从里面取出画来,展开摊平,画卷上自己的模样一点点显露出来,再熟悉不过。
极是用心的画,极是用情的画。
可是,现在才让他看到,会不会已经有些迟了。
景笙,非要到这种时候你才肯稍作表态么?
不争不求不取,可谁真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沈墨的指尖流连过画面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是他,然而又不是他。
画面里的人眉目清朗,丝毫没有忧愁,气度不凡,笑容沁人心脾,可是现在呢,不用看沈墨也知道自己的现在的样子绝不是这样的。
他已经走不了了。
景笙不知道,压在喜服下一起送来的,是君宁岚给她战报,边关又有两座城池沦陷,延边的善王托病不肯出兵相助,边关守备初齐旻瑜一线,皆节节败退。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没有他母亲之事,他也无法离开。
景笙,你过得太好,也过得太简单。
镜中花水中月,我沈墨,不是。
若是太平盛世,我便随你去了又如何,若是你早些说明,我……
不,已经什么都迟了。
沈墨闭了闭眼,捧起画,轻轻移到烛台边。
桔红的焰光瞬间吞噬过洁白的画纸,火舌妖娆舞动,犹如一张张狰狞的血色大嘴。
在众人簇拥下从容作诗的身影,在风中举笛轻吹白衣猎猎的身影,在雨中独行写意漫步的身影,在书库里安静垂头阅读的声音,在火焰里跳跃闪烁,清晰如昨。
劈劈啪啪的灼烧声后,画纸燃尽,一切都化成灰烬。
血色薄暮里,从此天涯不见。
景笙,你走好。
“小姐,小姐,船已经租好了,明晚我们就能动身离开了。”
“我知道了。”
景笙脸色沉静的收拾包袱:“我们回景府取些东西,解决麻烦,再去找君公子——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帝都,然后便去西江渡口等着。”
“小姐,你是……想要和沈公子私奔?”
景笙脸色微变,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下:“别问那么多。再去给我买些桐油、生肉骨头和烟花。”
待岭儿买完,景笙便想着,还欠着赵文艳几幅字怕是以后都没时间再写了,反正恰是途径,景笙路过古墨斋,刚要进去,便看见门边闪出了一道抱着剑的身影,将她拖到一边:“景小姐……”
“流萤姑娘。”
流萤扫见景笙的包袱,微拧起眉:“景小姐这是要去哪?”
节外生枝多险途,景笙道:“自然是回景府。”
“只怕不是……”流萤吸吸鼻子,“桐油,生肉……景小姐难道是想……”想通关节,流萤那张万年不变的冷酷脸庞终于也微微变色。
景笙打断:“是,我不过是不想让家人为难,希望流萤姑娘多见谅。”
说罢便要走。
不想流萤却道:“你买那些来做替身,错漏百出,不如真找具尸体。”
景笙没想到流萤会说这个,只好无奈道:“在下良民一个,上哪里去找真尸体?”
流萤转身,站到景笙面前,突然敛了一身的气势:“我帮你找,你离开带上我。”
“为什么要我带你离开?”
流萤把那块云敛给她的令牌又丢还给了景笙:“一直以来我都在为这块牌子的主人效力,云主子既然给了你,那你就是我的主人。起先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你若呆在帝都做你的安乐庶女根本不需要我我也不想陪你过家家,可你要是离开……”流萤漆黑的眼睛里掠过一丝茫然,“若不跟你走,我也不知道该去哪……”
景笙把牌子又丢还给她,道:“这块牌子你还是另择良主,它不适合我……若你真的能帮我找到尸体,你想跟着我也无妨。”
闻言,起初流萤接过牌子面色微青,听到后半段,却是勾起唇:“好。”
景府,秋竹院。
院里古槐青柳依然,君子兰开了谢,谢了开,此时耷拉着枝条,有些奄奄。
有人自墙头翻出,屋子里两具女子的尸首静静趴在地上,陈设有些乱,书桌上的字刚刚写了一半,墨迹还未干,换下的衣衫在庭院里晾着,地上还有衣服滴下的水滴。
一只燃着的火折子顺着墙角边丢下,火焰沿着细碎的火药燃烧进屋中,屋子的地面上有看似不慎落下的衣服,和纸张,再仔细看,那些衣服纸张上都有着一圈不自然的水渍,散发着奇怪的味道。
火燃到衣服边,嘭一声炸开,火焰瞬间蓬勃起来,围绕着整个屋子疯狂的燃烧。
老夫君急急忙忙披着衣服从自己的房间里赶来的时候,整个秋竹院已经成了一片火海,接连的几个厢房也或多或少跟着燃了起来,只是亏得是在傍晚,都还未入睡,看见火焰便都跑了出来。
家丁们不断从井里打水,浇在屋上,然而杯水车薪,火焰仍是越烧越大。
等火焰熄灭时,天色已是蒙蒙亮。
接连的几个厢房都烧得惨不忍睹,自然最惨的还是火焰源头秋竹院。
老夫君带着人拨开秋竹院的残骸,只见一切陈设都已烧得面目全非,当然最面目全非的是那两具显然是被火焰阻隔趴在门口却怎么也出不来的焦尸。
老夫君只看了一眼,就吓得晕了过去。
管正君更是连进都不敢进来。
即将出嫁的景言躲在姐姐景清身后偷眼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想幸灾乐祸一下,又觉得那大好的活人就这样硬生生给烧死实在骇人。
唯独景清一言不发,也无甚表情。
这个妹妹,实在比她想的要决然的多也大胆的多。
走了也好,在这破落的景府里能成什么气候?
时间后推上几个时辰,帝都一条幽暗的小巷弄里,三个女子从拐角闪了出来。
其中一个仍在喋喋不休:“小姐,小姐,这招真是太厉害了,任谁也想不出我们其实还没死,尤其是当她们看见尸体的时候,哈哈……”
景笙只是应着,没说话,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突然靠在边上最冷酷的女子止住了脚步,神色一凛,大喝一声:“是谁?”
巷弄的另一侧一道颀长的人影慢慢走出。
细长的眼瞳被晦暗的月色映射出一种瑰丽的色泽,景笙无故觉得有些凉风袭来,那头的人已经开了口:“景小姐,你可让我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