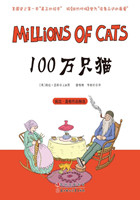景笙连猜也不用猜:“君公子回到帝都了?不知牧流芳的尸首?”
“已经运到帝都,不日将挂在城中示众。”君若亦看了看景笙,眼色一转,“你的请求我已经转告了太女,太女已经答应了。”
景笙本该欣喜,此时却有些笑不出来:“那多谢了。”
君若亦闻言,抿了抿唇,眼却看向远方,“连火遁都想得出来,你是真的想和他私奔?”
景笙一顿,停了一会才点点头。
“一走了之,真是没担当透了。”
景笙回道:“阳关道独木桥,个人选择不同而已。何必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他人?”
君若亦皱起眉,没等他说话,景笙又苦笑开:“抱歉,君公子,我心情不大好……”
“你现在不该是春风得意喜上眉梢?”
景笙没回话,只是笑笑,笑容里却有些勉强。
君若亦的神情微变,突然又柔了下来,手一扬抛来一个小包袱,丢给景笙。
景笙接过打开一看,包袱里是一个晋王府的令牌,和一份新的户籍通关文书,生辰八字出身地都与她本人不同,就连名字都……景笙无语的看着名字那一栏的两个斗大的字——金胜,不过无论是州府还是地方的印鉴都一应俱全,清晰明了,甚至不知君若亦哪里弄来的金府的印章,家主和金胜父母的印章都在上头。
景笙默默把包袱收好,对君若亦抱了抱拳:“也许此后再不相见,但君公子于我的恩,我会记得。也祝君公子和齐小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熟悉以后,景笙倒是很少这般态度。
君若亦点点头。
景笙想想,翻翻自己装东西的包袱,想寻些东西作贺礼,然而,还没找到,一个蓝色的锦盒掉了下来,景笙弯腰拾起,才想起这里面放的是什么,隔了太久,连她自己都已然忘却。
君若亦眼尖,已经看见:“你还没送给沈墨?”
景笙笑笑,微有些涩然:“是啊,我一直忘了。”
“你若不要,那给我好了。”
“倘若君公子不嫌弃……”
景笙将锦盒抛却而去,君若亦接了盒子,没打开,转身从巷弄又离开,细微的风声里是君若亦的声音:“走了也好,帝都将乱,到时候倒还不如呆在外面。你若有心,乱世里谋份职位,养活家小,不是难事,倘若再用点心,以你的能力,也许飞黄腾达也不一定。”
景笙却是一直苦笑,笑得连她自己都觉得实在……一言难尽。
城西,西江渡头,戌时。
西江渡头是座小渡头,载客一向不多,人烟也稀少。
此时,江岸边雾蒙蒙的夜色已经沉到底端,淡淡水草的气息弥漫过江面,天色阴沉乌压压一片看不清月色。
岸上也寂静无声,偶有人烟经过,也距离颇远。
江面停泊如今着一艘小船,桅杆上风帆半垂,舱内星火点点。
白衣女子站在岸边,独自孑立,忽起的风吹拂她的衣角,她却似浑然未决。
一双淡色的瞳仁望着地面上袅雾朦胧的景象,没有半分情绪,只是沉默的眺望。
“小姐,来吃点东西吧,才刚刚戌时呢,你已经站了一个时辰了。”
那边却没有回应。
岭儿想从船舱里起身,被一边的流萤拉住,流萤音色低沉道:“别去打扰她了,让她一个人安静的等着吧。”
望了望景笙的背影,岭儿的一猫腰,又躲回了船里。
船家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子,模样很是粗犷,此时正坐在船尾,抽着一根旱烟,淡淡烟气飘散。
似乎情景瞬间就这般定格,不再动静。
乌云渐渐在天空中聚拢,合起,而后簇成一团阴霾的暗色。
那是即将下雨的迹象。
果真,不多时,丝丝缕缕如牛毛般的雨丝斜入空中,带着丝丝凉意落了下来。
一点一点渐渐聚集起来,越来越密集,雨丝也越来越大。
景笙站在细雨中,察觉到素白的长衫淋上雨水,贴在肌肤上,很是难受,可她却没想过动弹。
随着雨声渐起,船舱里的岭儿也发现了雨滴,连忙从行李中拖出一把油伞,自舱内向外撑起,两步并作一步走到景笙身边,将伞撑到两人头上。
“小姐,下雨里,你快进舱吧,进舱等也是一样啊。”
景笙扬扬嘴角,而后摇头。
知道某些时候自家的小姐有多固执,岭儿便不再劝阻,只是撑着伞,陪着景笙一道站在岸边。
半个时辰过去,岭儿的手臂渐酸,只是看着景笙,又撑着手臂咬牙坚持,只是即便如此,伞还是不自觉的颤动起来。
景笙转过身,握过伞柄,声音在夜色里有些模糊:“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等就好。”
岭儿执拗地看着景笙,景笙已经转回头去,除了看着远处仍是看着远处,再无其他反应。
岭儿叹了口气,跺跺脚,硬是站在了景笙身后。
雨渐渐滴落,从一丝丝到一串串,淅沥的雨声犹如鼓点,咚咚直响,水沫刹那横飞,狂风急骤呼啸而过,吹得枝桠乱颤,远处叶片摩擦着摔落,飘零至江面。
大雨已然倾盆而下。
小小的油伞已无法护住两人的身体,岭儿从舱里又拿了一把伞。
船家已经躲进了自己的船舱里熟睡,岭儿身上也湿了一半,流萤见状,对岭儿叹道,“还是我去吧。”
流萤出舱撑伞,便看见景笙握着伞,一动不动,雨滴顺着衣襟滑落也似未觉。
倒也难以想象,那个半点武功不会就敢独自去擒牧流芳的女子竟然……这般痴情。
不知撑了多久的伞,体力好如流萤也觉得臂膀渐渐酸疼。
油伞几乎已浑无用处,身上的衣服已然半湿。
遥远的更鼓声一声声传来,那是三更的更鼓。
流萤蓦然惊觉,她们已经等了两个多时辰。
只带了两把伞,可是船舱里听见更鼓的岭儿已经再等不住,顶着雨水冲出了船舱。
“小姐,你别再等了,快回去吧,三更都过了,沈公子不会来了。”
景笙伫立在岸头,白色长衣被风鼓动的猎猎作响,发丝也被雨水浸染,一缕缕无规律的贴在鬓边,凌乱非常。
“小姐,小姐……”
不知道多少声,景笙才缓缓开口:“你再让我等一会,等完,我才甘心……你们先回去吧。”
“小姐,沈公子真的不会再来了……我们先去船舱避避雨吧!”
景笙只是摇头。
三人便在两把几乎无多少遮蔽功效的伞下,傻傻站着。
好在,又下了半个时辰,雨渐渐停了。
乌云散开,风声舒缓,沾湿的外衫被风吹过,冻得人直起鸡皮疙瘩。
景笙的身体晃了晃,却还是站着。
岭儿终于撑不住,到了舱里睡去,流萤又呆了一会,也回了舱。
地平线上,血色薄暮,东方既白。
景笙扯起干裂的嘴角,连苦笑的力气都抽离了去,眼睛里的疲惫一直深进心里。
“沈墨……”
她说,那声音已经沙哑细微到听不见。
“你果然真的……”
其实,已经有预感了吧。
沈墨心比天高,沈墨从来不似她庸碌,沈墨要太平盛世,她什么也给不了。
景笙慢慢转身,差点一个踉跄摔倒,略停了停,稳住身形,景笙缓缓走回船舱,掀起帘子,一头栽了进去。
船驶出渡头,在河上徐徐行驶。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际一碧万顷,河面风平浪静。
到瀛洲只坐船是不够的,她们要先坐到皇王朝最大的临海大都东城,然而搭乘大型商船,沿着广江一路顺流而行,直行数十日才能到达瀛洲边岸。
可是现在她们显然已经等不及了,岭儿见景笙倒下,只以为是熬夜困乏,身体承受不住,便把景笙扶进船舱里歇息。
知道入夜景笙也没有醒来,岭儿发觉不对,再去看时,看见景笙神智昏聩,脸色潮红,汗水顺着额角留下,便知不妥,伸手一探,景笙的额头竟是烫的吓人。
到东城的路只行了一半,此时船身四周均是一望无际的水面,岭儿忙去问船家,得到的答复是至少要再过一天才能找到陆地靠岸。
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却没有足够的药材,岭儿只好到船边打了凉水,一遍遍拿毛巾把景笙擦汗。
船在河面上继续飘行,景笙的烧仍没退去,闭着双眼,但眉头一直紧锁,嘴唇翕张,似乎在说些什么,只是声音太小,即使凑近了岭儿也听不清。
其实即便听不清岭儿也能猜个十之八九,沈公子没来,小姐该有多失望,该有多难过……
岭儿忘不了景笙站在岸头,身影笔直而寂寥,仿佛就要离去般的模样。
那一句几乎是绝望的话浮现在岭儿的脑海里,小姐尽管一直都与人相争,可是骨子里却比谁都骄傲,能让她那样放下心防去等待,去守候,该是有多动心,又该是有多伤。
拿起毛巾,放进水盆里浸湿,不过片刻,汗水仍然一点点流下。
岭儿着急,便出去让船家开快些,或者抄近路什么。
船家看了看河面告诉岭儿,近路是有一条,不过那里河床较深,河水较之湍急,也比较危险。
岭儿着急景笙的病,二话不说多塞了些银两给船家。
那船家女子也不含糊,掂量了两下银子的重量,塞进衣襟里,撑起船桨就转了船头。
然而,没料到的是,才天晴不久,天色竟然又阴沉起来。
雨水比想象中来得更快,而且也比上次更大,不到一刻,乌云滚滚遮天蔽日,河面也一下子险峻起来。
她们租的船只并不大,虽容纳下四人起居绰绰有余,可是在宽阔的河面上,船只便如一叶扁舟,仅仅是靠风帆和船桨来控制方向。
看见此时的天色,船家也慌了起来。
“糟糕,起了风浪!”
从船舱里抽出两支船桨甩给流萤、岭儿,三人竭力用船桨稳住船身,黑云里一阵阵阴风卷着浪潮打上船面甲板,已经能看见有水流被冲击的涌上船面。
大量的雨水侵袭入船内,不一会,除了船舱里,船面已完全湿透。
船身也开始幅度很大的摇晃,船帆被吹得发出阵阵骇人的响声,水面上一浪高过一浪,甲板上的东西也开始东倒西歪起来。
岭儿一手扶着船缘,一手撑着船桨,看看近在眼前的变换天色,又看看船家异样的神色,当下丢掉船桨,扶着船缘摸到船舱里面。
“小姐,小姐,出事了,你快醒醒,可能要翻船了。”
景笙的神智仍不清醒,岭儿也顾不上,用力摇着景笙的肩膀,声音几乎有些惶急的哭腔“小姐,小姐,我们只怕是遇上风暴了,你快些醒醒啊!”
晃了好一会,甚至连船舱也跟着晃了起来,景笙的眼皮抬了两下,干涩的嘴唇里吐了两个沙哑的字:“什么?”
岭儿赶紧倒了口水,喂给景笙,一边飞快的把现在的情形告诉景笙。
景笙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脸上依然是不正常的红晕。
谁知刚一坐起,船身一个倾斜,景笙的身体随之摇晃,幸亏及时用手撑住,差点没一头撞上舱壁。
流萤不知何时也掀帘走了进来,此时的她几乎半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长发和衣角滴落在地面,整个人显得十分狼狈,但神情却严肃起来:“这船怕是撑不住了,船家说离岸现下约莫只有两三里的路,游过去快的话半个时辰足够了。”
“可是小姐现在还病着,根本不能下水,怎么办?更何况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不能下水的物件。还有风浪这么大这么急,下去保不住不等游到岸边就被一个浪打进水里,再出不来……”
又是一个浪打进船里,船身剧烈摇晃,怕是再来几下就要翻了。
流萤稳了稳身体,道:“没时间了。”
说着丢下剑,一把拽起景笙:“我背着景小姐下去,带她游到岸边,你收拾好东西跟上。”
“可是……”
“没有可是。”
景笙勉强集中起注意力,可是流萤和岭儿的对话声还是越来越远。
直到流萤一下纵身跳进水中,景笙才被冰凉的河水猛地惊醒。
那些冰凉的液体贪婪的汲取着她身体的温暖,冷热交替的感觉让景笙苦不堪言,可她也确实不敢开口,流萤的身体在水中依然灵活,一潜一潜已游出去十来米,景笙的身体随之起伏,不时有些河水涌入鼻翼,景笙伸出疲软无力的手掩住鼻子,只在出水时用口呼吸。
天空已经彻底暗的看不清前方一丝。
尽管被背着,但水浪的冲击实在太大,景笙只用一只手来抱住流萤显然并不牢靠,流萤在游泳应对海浪的同时还必须不时把景笙的身体托起,以防脱落。
这样高强度的运动,即便体力好如流萤,也渐渐有些体力不支。
雨水还在不停的落下,雨声越来越大,,雨滴也越发密集,景笙开始咳嗽,呼吸渐渐有些紊乱,头痛的几乎无法思考和维持清醒,抓住流萤的手慢慢松了下来。
流萤咬住牙,想再快些。
突然一道巨大的浪潮涌起,流萤睁大眼睛,一手死死拉住景笙的衣角。
大浪整个吞没了这片河域,波涛如怒,甚是骇人,待浪过去,河面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百里外,浅滩沙地。
三个穿着布衣的女子卷起袖子从滩上拖出两个已经昏迷不醒的人。
待拖到一处平地上,三人围在一起,研究着两个衣着褴褛到看不出原本模样的人,一个面容冷森,闭着眼睛也让人觉得这人不好相处,另一个则恰好相反,闭着眼睛也让人觉得骨子里透着一种淡淡的温和之感,唇角微微扬起,让人禁不住心生好感,只是脸色苍白如纸,没有一点血色。
其中一个说“喂,喂,你瞧着这两个是死是活?”
另一个嘿嘿一笑,贼手就伸向两人:“是死是活先别管,我们先搜搜这两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最后一人猛地排开前者的手,不赞同地摇摇头:“老李,你还不接受教训,当家的早都说了,不许乱摸老百姓东西更不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要劫就去劫那些官家的,而且公子也会不高兴的。”
那老李听了也不乐意了:“老张,你别老拿着鸡毛当令箭,我们可是海贼!我们本来就是贼,还约定那个不是可笑么?老刘,你来评评理,她回回这样,碍着老娘的财路,可还上了瘾了!”
老张听了也不乐意了:“有本事这话你和当家的说,和公子说?”
“唉,你这人怎么回事,还和我杠上了!”
说着,老李就要动手,老刘连忙上前劝架。
这一番折腾,倒是没人发现,那个面容冷酷的女子已经悄然睁开眼睛,河水顺着她的嘴角一点点流出,她的手掌不自觉地握紧,眼睛却瞄向一边仍在昏睡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