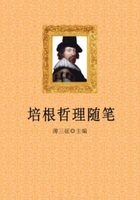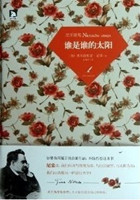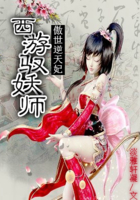《信心铭》是在继承达摩、慧可的清净心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取道家尤其是《庄子》的“齐物”、“逍遥”思想而成的。全文以“真如法界不二”即以宇宙万物本体同一的思想为宗旨,强调万物之间相即齐一,又以修持者契合如此的“至道”为禅修的最高境地。契合“至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人的心地的本真状态。为此,《信心铭》提出“息见”、“不心”、“任性”的自然主义心性论。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注释:《信心铭》,《大正藏》第48卷,376页中。],这是《信心铭》全文开宗明义的总论性的话。拣择,即选择,区别。这句话是说,把握“至道”的最根本之点就是不作分别。也就是既不作“有”的分别,也不作“空”的分别。“系念乖真”[注释:同上书,376页下。]任何执持对立的一端都是不符合“不二”原则的妄念、妄见,都必须消灭。消灭二端对立的妄见,也就是显发出真实的心性。这就是“不用求真,唯须息见”[注释:同上书,376页下。]。要做到“息见”,就是要不生执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注释:同上书,376页下。]。“将心用心,岂非大错!”[注释:同上书,376页下。]“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注释:同上书,376页下。]“不心”,就是不生心。如果“生心”、“用心”、“心异”,就会形成分别,产生是非,执著取舍,有所得失,从而违背“真如法界不二”的宗旨,也就无从契合“至道”的境界。要做到“息见”、“不心”,也就是要“任性”。文中说:“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注释:同上书,376页下。]“性”,指众生的本性、真性。“任性”就是随任性的自然,就是“归复自然”[注释:同上书,376页下。],这是不作分别,非有非空,无去无来的心性本然,是人心冥合至道,断绝烦恼的理想境地。这种追求心的原初状态、心性的自然表露,以及任运自在的自然主义的禅修生活准则,越来越为后世大多数禅师所奉行。
道信和弘忍的念佛心与本真心思想
一、心心念佛与念佛净心
达摩禅传至道信、弘忍时,历史已进入了隋唐大统一的时代。道信(580-651)、弘忍(601-674)分别住在蕲州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的破头山(双峰山)和冯茂山(东山)弘法。黄梅地处长江中游,东西南北,往来称便。历史的良机和环境的优越,推动了道信、弘忍经过50多年的努力,使门徒分别多达500人乃至700人。道信和弘忍这一系史称“东山宗”,成为当时禅法中重要中心和尔后禅宗的直接源头。
道信、弘忍的禅法,史称“东山法门”。这一法门的核心是“一行三昧”。所谓“一行”,意思是定、正定,即将心定于一处或一境,不使散乱,保持宁静、安定的状态。“一行三昧”就是指心专于修习一事的正定,或者说是借一种修行,使心安定下来。通常有两种,一是一心念佛的念佛三昧;二是一心观照万事万物无差别相的三昧。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论述了他的法要:“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6页下。]可以说这是东山法门禅法的纲要,其中包含了心性理论和修行实践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先论述他的“一行三昧”修持法门,即一心念佛的念佛三昧。《文殊说般若经》对于念佛三昧如是说:
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注释:此经全称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引文见该经卷下,《大正藏》第8卷,731页中。]
这里的“相貌”指形相,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取相貌”,是根据般若的思想,不执取形相差别,而归于无差别相。经文主张入一行三昧的方法是静坐、定心、不取相,专念一佛名,如此坚持不懈,就会使心安定、清净,也就能由念一佛而见一切佛。这种一行三昧是般若无相学说与唯心念佛相合的修持方法。
弘忍在继承道信法门的同时,又比道信更鲜明地倾向《大乘起信论》的一行三昧。《大乘起信论》主张以离念(念,指无明)即远离无明归趣于无相的修持工夫,求得心灵返归原初的清净状态,所以也很重视一行三昧。此论的一行三昧,就是念念离念,“念念”指时时刻刻。意思是时时刻刻专注于排除离开无知妄念,也是更重视原初一心的修持与寻求。
《续高僧传》卷20《玄爽传》描述了道信的禅法是“唯存在摄念,长生不卧,系念在前”[注释:《大正藏》第50卷,600页上。]。《楞伽师资记》载弘忍的禅法是“萧然净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注释:《大正藏》第85卷,1289页中。]。从总体上看,道信、弘忍师徒禅法的基本路数是一致的。他们的法门,一言以蔽之,就是静态渐修的坐禅、念佛和观心、守心。
伴随着东山法门的弘扬,道信、弘忍在达摩禅演变史上树立了新的家风。主要表现为:一是定居山林。达摩、慧可修持的头陀行规定,不得留恋久居一地,而要过随缘而住的云水生活。道信、弘忍改变了这一传统,
“择地开居,营宇立象”,长期定居于黄梅。他们开创道场,建造寺院,弘法传道,聚徒数以百计,形成一个庞大的教团。由于久居山林,潜修山中,不仅形成了山林佛教的禅风,而且在禅修的同时开展生产劳动,采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方法解决了僧众的生活问题。二是法门洞开。在弘忍以前,禅师不轻易传授禅法,只是有选择地个别秘密传授。自弘忍始,法门大启,根机不择,不分学徒条件的优劣,一律实行普遍而公开的传授。三是传菩萨戒。据《楞伽师资记》载,道信撰有《菩萨戒本》,说明他在教导禅法的同时又传大乘戒。这种禅戒结合的做法为弘忍所继承。四是重在念佛。与以往凝神壁观不同,道信转而引用念佛三昧,提倡“心心念佛”,依念佛而成佛。弘忍同样主张“念佛净心”,认为通过佛名,能使人心清净。
道信撰写的《菩萨戒本》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二书均已佚失,然《楞伽师资记》全书约一半是讲道信禅法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一书的内容已为引录,故可作论述道信禅法及其思想的根据。现题为弘忍述的著作,有《最上乘论》一卷,此书与敦煌本《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一卷为同一种作品,但《楞伽师资记》断定为伪撰。由于《最上乘论》所述的内容,与弘忍的思想比较一致,似可作论述弘忍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明净心与念佛心
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是奠基于心性理论基础上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引古训说:“古时智敏[注释:近人印顺法师认为”智敏禅师大致为智顗禅师的误写“,见其所著《中国禅宗史》,57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若如此,则道信的禅法颇受天台宗止观学说的影响。]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原及诸体用,见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一解千从,一迷万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8页上。]这段话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持原则。在解知方面,特别重视知心的根源及其体用的意义。又说:“坐时当觉识心初动,运运流注,随其来去,皆令知之。”[注释:同上书,1287页中。]这是说,坐禅时要觉察自己原初心灵的冲动,知其来去变化。也就是超越单纯的坐禅冥想,而着意关心探索本原性的一心。道信主张以心为原,教人向内心用功,为此他还特别用“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话来强调“心”的重要作用。这里道信是引用4卷本《楞伽经》的品名“一切佛语心第一”,而《楞伽经》品名的“心”字是核心、中心的意思,该品名标示了佛教核心思想在《楞伽经》中都具备了。道信则断以己意,把“一切佛语心第一”发挥为“诸佛心第一”,把“心”说成是人心的心,强调“心”的重要,强调要重视“心”的修持,以此强化向内用功的禅修路线。
道信除了依据《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以外,还广泛地吸收了其他佛教经典思想,以致他对心内涵的论述也比较庞杂。从《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来看,心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众生原初本有的角度界定心是明净心(清净心),二是从众生现实修持角度提出的心是念佛心。以于明净心,道信又通过融合《楞伽》和《般若》两经,来肯定如来藏性与寂灭性两方面统一的特质。《楞伽经》是讲如来藏的,《文殊说般若经》是讲空的。然而《文殊说般若经》又认为真空与妙有不二,从空寂中显示真性,所以说:“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注释:《大正藏》第8卷,729页下。]“如来界”,是如来性、如来藏、佛性的别名。“我界”即众生。这是说如来藏与众生,平等不二,众生都具有如来藏性。在道信看来,上述两经是互融互补的,如来藏性与空寂性是无异无别的。他说,若能做到,“观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注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9页上。]。这也就是说,清净与空寂本是一回事。
道信还分析了明净心的体用两个方面。心体是指心的体性,“体性清净,体与佛同”[注释:同上书,1288页上。],人心本有的体性是清净无染的,与佛是一样的,即众生心性的本质与佛无异。这是一种众生都有佛性的思想。在道信看来,这也是众生信佛入道的前提,如果众生没有清净体,没有佛性,入道成佛又从何谈起?心用是指明净心的作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如法(原作‘惑’)皆如”[注释:同上书,1288页上。]。“法宝”是佛、法、僧三宝之一的佛法。“万法”,一切存在。明净心的作用是产生与佛法相符合的觉悟,同时这种心的作用又表现为无所波动工“恒寂”状态,即不对万物作出高下分别,而是“万法皆如”,一体平等。如果对万物作出种种区别,就违背佛法,不符万物的实相,就是妄念。
道信在体用观念基础上,阐发了明净心的体性与作用,为念佛心提供了理论根据和修持规范,为引导人们追求内心世界的明净空灵提供了方便法门。
道信提出了“念佛心”的概念,并加以阐释,宣扬“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的命题。这既是把念佛心与妄念、佛与凡夫对立起来,也是把念佛心与佛、妄念与凡夫统一起来,具有重要的宗教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那么,什么是念佛心呢?为什么说念佛心是佛呢?所谓念佛心,就是前文所引的“系心一佛,专称佛名”。意思是排除一切妄念,专于念佛,心心相续,以求心中见佛。这实际上是主张念佛与念心的同一。道信的念佛是称名、观想等多种念佛活动,念心就是观心。也就是一方面以念佛生无量无边功德,一方面以观心灭妄念,求得心地清净。这两方面是同步的,甚至是同一的。这样,念佛心也就是“名无所念”[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7页上。],是不作区别、无所执著的心,是心的本然。念佛心排除妄念、烦恼,不执著对象形相,就会“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7页上。]。念佛心的佛是无形无相的,念佛心的心也是无形无相的,从修持的更高意义上说,念佛实是无所念,连念佛心也不生起,只保持原本的净心,才是真念佛。这种无所念的念佛心,是禅修成佛的基础:“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7页上。]“方寸”,心。“道场”,成佛的依处。“菩提”,觉悟。身心活动,不外乎自心,一切活动,都是成佛的道场,都体现了成佛的觉悟。所以,“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7页上。],“念佛心是佛”。真念佛时,佛与心的形相俱泯,佛与心相融无别,佛就是心,心就是佛。这也就是“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7页上。]。
道信对念佛心的功能作了多角度的揭示。首先,他认为念佛能知诸佛的无差别境界。“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辨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注释: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7页上。]念佛时观想一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佛佛是相通的,由念一佛就能见一切佛显现面前。其次,念佛能使心净。《传法宝记》描述了弘忍等禅师的法门是“念佛名,令净心”,这是继承道信的禅法。念佛使心专一,集中,单纯,安定,也就会进一步使心清净。而心清净也就是佛性、本觉。再次,由念佛进而体悟到所见诸佛都由自心活动,即都是唯心所现。佛从心生,要求成佛,念佛心实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也就进一步开拓了“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注释:《观无量寿佛经》,《大正藏》第12卷,343页上。]的法门,以求达到即心即佛的体悟。
道信以念佛与念心相合而一构成念佛心的观念,把众生的现实心灵与原本清净的心灵沟通起来,从而也就为从念佛过渡到成佛提供了桥梁,并以此与具有妄念的凡夫区别开来。
三、自心与本真心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把禅修要领归结为“守一不移”,《最上乘论》断承了这种观点,进一步强调“守心第一”,并认为所守的心是“守本真心”。
道信说:“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注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转引自《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卷,1288页中。]又说: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注释:同上书,1288页上。]所谓“守一不移”是首先观照众生自身只是“四大”、“五蕴”和合的假名,空净而了无一物可得。然后以这种“看净”的观点与方法去审视一物,如此摄守不移,以进入自心寂静的境地。这样,学禅者也就能够不需要通过什么中介而“明见”,即直接体证自身的内在佛性,从而得定发慧。《最上乘论》在此基础上说:“此守心者,乃是涅盘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注释:《大正藏》第48卷,377页下。]“十二部经”即各类佛经。这是把守心的重要性提到学佛和成佛的高度,甚至认为是佛的本师,这也就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心的作用。
《最上乘论》对守心作了这样的说明: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注释:同上书,377页上。]
认为心是“自性圆满清净心”。此心的规定性有三:本来清净,不生不灭和无有分别。《十地经》曾有这样的比喻,说众生身中都有佛性,犹如太阳,圆满光明,但为云雾遮覆而使天下阴暗。《最上乘论》引用这一比喻说,清净心是为妄念烦恼所盖覆而不得显现,只要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清净心就会自然显现。这是通过云雾遮住太阳的比喻为说明心的“本来清净”,把需要论证的论点视为不证自明的。关于心的“不生不灭”,该论说:
《维摩经》云:如,无有生;如,无有灭。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净。清净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从缘生。又云:一切众生皆如也,众贤圣亦如也。一切众生者,即我等是也;众贤圣者,即诸佛是也。名相虽别,身中真如法性并同。不生不灭故言皆如也。[注释:《大正藏》第48卷,377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