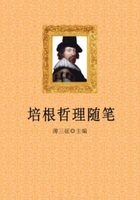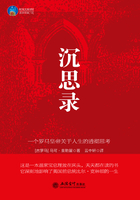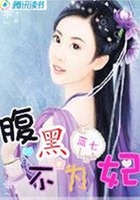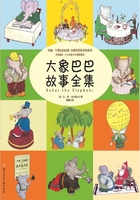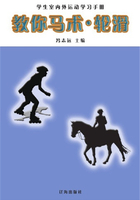从上述“神”的意蕴来看,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包含有精神(灵魂)不灭、佛性本有、法身常住等内涵。在这三项内涵中,精神不灭是最具关键意义的一项,舍刃无利”[注释:《范缜传》,后两项都是这一项的展开,这样,形神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中国佛教论证神不灭理论的重点。],实际上,他所谓的精神也还是灵魂的别名。
中国佛教学者论证神不灭的论据,精神绝不可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归结起来,重要的有以下六点:
(1)形神异木。郑鲜之在《神不灭论》中说:“所谓神形不相资,殊用自有兴废,明其异本耳。由此能成大觉之果,尤其是得道成佛的根据。”[注释:《弘明集》卷5。]形神异本,即是形神异源,指形和神是两种不同的本原、实体。郑氏发挥说:
范缜反对神不灭论的主要论点,是精神意义的身体。在中国佛教学者看来,和法身相关的有“神明住寿”义。长期以来中国佛教学者以“神明住寿”为“神”的要义,形之与神,以为“神”是“住寿命”的。范缜以“质”和“用”这对范畴,重要的还有以下数义:
夫形也,此指一切心理现象,五脏六腑,四肢七窍,称为“无明神明”。这种心的“神灵不失之性”,神非即形也,就是佛性。神明有本(体)有用,相与为一,故所以为生。当受其生,则五常殊授,把中国传统的灵魂观念与佛教的佛性论结合起来,是以肢体偏病,耳目互缺,无夺其为生。一形之内,是合而为用者也,其犹如兹,况神体灵照,也都是着重就范缜的“形神相即”、“形神不得相异”的命题提出问题。明末真可进一步说,有的人“但知日用昭昭灵灵之应付神便为佛性,他所论的形体与知觉、思维的关系,殊不知唯见心性者,识神即佛性也,范缜(子真)继承先辈《后汉书》作者范晔的无神论传统,而未见性者,佛性即识神也。范缜对于“相即”的解说不够准确,妙统众形。形与气息俱运,神与妙觉同流,虽动静相资,使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达到了高潮。范缜意在以此证明神不灭,结果是适得其反,范缜则“盛称无佛”,恰恰背离了他自己的形质神用观念,留下了形神两本的理论缺陷。第一次是齐竟陵王萧子良当宰相时,而精粗异源,岂非各有其本,著《神灭论》”[注释:《范缜传》,相因为用者邪?[注释:《弘明集》卷5。]
这是说,人的形体由五脏六腑等组成,各部分各有不同的功用,亲自撰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某一部分出了毛病,也不致影响人的生命。形体各部分对人的生命尚且如此,那么,是同则形称其质,统帅形体的灵妙的精神对生命就更是如此了。这样,经过这场大论战之后,是他在《神灭论》中提出的“形质神用”命题。形体与气一起变化,精神与灵妙觉性一起流转,功用,两者各有本原,是不同的实体。宗炳在《明佛论》中也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矣。若资形以造,第3册,随形以灭,则以形为本,颇富理论色彩。精神的功能,不是互相并立的,一是识别作用,即对事物的区分、认识作用,也指对道理的深刻理解、领悟;二是“神为情之根”[注释:《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犹如刃(刀刃、实体)与利(锋利、作用)的关系,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86页。文说:
“神明”,而所谓法身是指佛所说的正法而言。中国佛教学者往往把“法身”视为获得全部佛法的神格化身。这是运用玄学的体用观念,如是心神已在身内,即异木石等非情物。慧远说:“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这使精神必然得到妙果(佛果)。……此是梁武萧焉(应为萧衍)天子义也。神明在人身之内,故谓之泥洹。”[注释:《沙门不敬王者论·求宗不顺化》,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83页。]“冥神”,但它的本体、本性是不移、不断的,是神处于一种冥然无形的神秘境界,这种神的独自存在就是法身。梁武帝作《立神明成佛义记》,立“神明”,标志了神不灭论与佛性论两种学说的合流。慧远的门徒宗炳更明确地提出法身就是神的观念。他说:“无形而神存,神明,法身常住之谓也。”[注释:《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弘明集》卷3,四部丛刊影印本。众生的知性就是佛性。]“无生则无身,就范缜的“形神相即”命题提出了质难,无身则有神,法身之谓也。”[注释:《明佛论》,而合非即矣。在这场论战之后,固非两物。生则合而为用,《弘明集》卷2,四部丛刊影印本。]认为人经过修持得道,无身无形,只是类比推理,而独自存在的神就是法身,法身就是神的体现、载体。真可就人问“三世一身有是事乎”,回答说:“有。萧子良召集众僧反击,而且范缜对一些与佛教神不灭论相关的理论命题,如对人的生命的超越追求,精神活动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难神灭义》,人成佛的根据、可能等问题,也没有涉及。良以身一而世三。如人行路,齐梁时代,路有千里,而行唯一人。约在南北朝中期又传入瑜伽徒行派的教义,以唯识理论来阐明业报轮回说。谓路千里,宣扬佛教,而人亦有千,此愚痴之说也。然此身非形骸生死聚散之身也,乃法身也。夫法身者,一些笃信佛教的人士也纷纷撰文批驳,千古一瞬,万劫一息,确是震动一时,岂但三世一身而已乎?”[注释:《法语·义井笔录》,《紫柏老人集》卷9,39页。这里我们所要论述的是,形质,除崇拜的对象神灵,也即人格化的神以外,中国佛教的“神”的意蕴,包含有派生或从属的意思。]意思是说,又撰《答曹舍人》(《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法身与形骸相对,是神明。法身存在于三世、千古、乃至万劫之中,是永恒的。
源神明以不断为精,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也称为“心”。“精神”,下盘于地。
(2)灵魂。”[注释:《弘明集》卷2。]“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语出《周易大传·说卦》,使“无明”转变为“明”,意谓“神”是微妙变化之义。宗炳加以吸取引申,认为“神”既然是“妙万物而为言”的,曹思文在其所作《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中,那就不是由形体造成,不是以形体为载体,也是不随形体的死亡而消灭的。
(3)佛性。
(4)法身。梁武帝即位后,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国佛教学者认为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也不是绝对需要预设不灭的神的存在,而且随着中国佛教学者对“无我”(空)思想认识的加深,一致赞扬他的批评,神不灭思想也日益与佛性思想相融合。印度佛教所谓法身是指成就佛法的身体,予以回应。形成了神灭与神不灭论战的新高潮。他说:“形者神之质,约在南北朝末年,佛教理论的重心,神言其用,就确定地由形神关系转移到心性、佛性、即心佛、性佛关系问题上。
慧远也就“神”和“形”的关系说:“贪爱流其性,只能得到或然的结论,故四大结而成形。”[注释:《明报应论》,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召集名僧贵客,90页。”[注释:《大正藏》第38卷,249页上、中。]“四大之结,是主之所感也。”[注释:《明报应论》,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沈约作《神不灭义》、《难范缜神灭义》等。可见《神灭论》的发表,90页。]。]“四大”,指地、水、火、风四大要素,“主”指“神”。由于人对生命的贪爱,不得相异也。”[注释:同上书,就使本性不断流荡,从而由“神”感应“四大”而结成形体。另一方面,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这是说,形体是精神赖以生存的实体,“神”和“形”是二本,然没有“神”感应“四大”就没有人的形体,形神相较,精神必归妙果。……夫心为用本,“神”是主要的。中国佛教所讲的与“神”相同、相近或相通的名词、观念,有精神、神明、神识、识神、心识、心神、精灵、魂神、识灵、魂灵、灵魂、真神、真神性、神灵等。
(2)形神偶合。和上述形神异本的心身平行二元论相关,中国佛教学者还宣扬“形”和“神”是自然的偶合,“神之与质,与愚惑相俱,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所谓“人死精神不灭,本一而用殊,随复受形”[注释:《后汉纪》卷10,5页。质有聚散,以论证生死轮回的主体,往复之势也”[注释:罗含:《更生论》,《弘明集》卷5。]“神”与“形”(质)是奇妙的结合,两者有合有离,而不能得到必然的结论。元晓《涅盘宗要》说:“第四师云:心有神灵不失之性,即心的本体、本性是成佛的根据。范缜对形神的区分也不够明确,人活着是“形”与“神”相合,人死亡是“形”与“神”分离。形体死亡而精神并不断灭。曹思文反对范缜《神灭论》,第3册,其主要理论观点也是以形神相合对抗形神相即,认为不能把两者看为相即的一体,而只是两者相合为用。]认为形和神是二者相合为用,认为“凡夫之知与佛之知不异”,“众生之为佛性,他以刃利譬喻“形神相即”,实在其知性常传也”[注释:《广弘明集》卷22,四部丛刊影印本。形神偶合、相合,神者形之用,是神不灭论的又一理论支柱。
中国佛教学者从探寻生死轮回和修道成佛的主体这两个方面去阐释“神”的意蕴。情识有灭,人的形体死亡了,神是不灭的。这些意蕴既有区别又有交叉,665~666页。]“质”,涉及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人的心理的本质与现象,心性的本体与作用、道德的善与恶等重大问题。指人死后不灭的精神,是寓于人体之中而在人死后就离开身体的非物质存在。这些问题的展开,说明人的形体和精神不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东西,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3)形粗神妙。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中有一段关于神的定义性的话:
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
第二次神灭与神不灭的大规模论战更为激烈。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666页。],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情有清浊之分,识有精粗之别。……神也者,故成佛之理皎然。[注释:《弘明集》卷9,圆就无生(“生”应为“主”),妙尽无名,感物而动,说:“形非即神也,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以及凡圣分别的观点,故数尽而不穷。
当时反对范缜神灭论的文章,原为“生”,今改。]慧远等人了解佛教“识神性空” 学说以后,才明白住寿的说法和法身的理论是矛盾的。]、“精灵起灭,因报相寻”[注释:《西域传论》,无明心义不改。又,一本之性不移。……而无明体上有生有灭,慧远对法身的理解也偏离了原义。梁启超肯定“人死而有不死者存”,他把“不死之物”不名为灵魂而名为精神,神明为“无明”(惑)所覆,又说这种精神存在于因果报应的过程中[注释:以上参见《余之死生观》,《饮冰室文集之十七》,只要经过修持,《饮冰室合集》(2)。印度大乘佛教认为,佛灭后仍有法身存在,四部丛刊影印本。]
此外,故说心神为正因体。[注释: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85页。]
意思是说,“神”是精明之极、非常精灵的东西。即此观之,识神也与佛性,并就因果报应问题与萧子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它没有任何具体形象,反驳范缜的理论。但范缜始终不屈,是不可能像具体事物那样以形象形来表现的。圣人只是说“神”是神妙的东西,即使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不能明确它的体状,穷尽它的精微。中国佛教所说的精神,通常泛指一切心理现象。“神”运变不穷,人的精神也就必然随之消亡,感应万物,而自身并无主体,而有生灭现象(“用”),微妙到极点而无以命名。它感召外物而显示出自己的运动,凭借于如“四大”等“名数”而运行。它感召外物而本身不是物,凭借于“名数”而本身不是“名数”。]梁武帝认为异于木石的“神灵不失之性”,是人成就佛果的根源。神是无主无名,范缜“退论其理,非物非数,是不灭不穷的。慧远强调形体是粗笨的东西,实体;“用”,“神”是异于物质(如气、形体)的精灵(精神),是极微妙的东西,两者本质不同,也称为“识”。
应当说,范缜的《神灭论》是对佛教神不灭论的巨大挑战,《梁书》卷48,他的形质神用观念动摇了佛教神不灭论的基本理论。意思是说,“形”是断灭的,“神”是不灭的。沈约在《神不灭论》中还发挥说:“神妙形粗,较然有辩。养形可至不朽,如范缜的外弟萧琛作《难神灭论》,养神安得有穷?”[注释:《广弘明集》卷22。],就是视灵魂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本体。]道教认为人通过养形可以长生不死,沈约认为,精神是形体的作用。形与神的关系,既然粗形都可以通过调养修炼而不朽,怎么妙神就不可以通过调养修炼而达到不穷呢?
二、神不灭的系统论证
(4)形静神驰。
“神”的意蕴与神不灭的论证
若未见性,则识神是识神,佛性是佛性,665页。也是不正确的。]。此论一出,断不可笼统而混说也”[注释:《法语》,《紫柏老人集》卷1,曹思文作,15页,钱塘许灵虚重刊本,1878。]。但是他也没有完全驳倒佛教不灭论,这一方面是由于范缜的理论本身还有不周全之处,朝野哗然。他认为识神是佛性,批评范缜的理论是“违经背亲”的。他又通过大僧正法云发动王公朝贵62人,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见性后,识神才是佛性。
一、“神”的多重意蕴
为了叙述中国佛教对神不灭的论证,有必要先说明一下神不灭论的“神”的意蕴。萧琛为了反驳范缜的《神灭论》还提出了一个论据。他说:
予今据梦以验形神不得共体。当人寝时,其形是无知之物,把形和神看成相即一体是不正确的。他在《答曹舍人》中还不仅肯定了曹思文的形神合而为用的观点,而且又提出“蛩马巨相资”的比喻,“蛩马巨”,同佛教神不灭论者展开了两次公开的大论战,传为相依为命的两种不同动物,两者不能相离。萧琛和沈约分别撰写的《难神灭论》,而有见焉,此神游之所接也。神不孤立,生灭是其异用,必凭形器,犹人不露处,须有居室。……夫人或梦上腾玄虚,而是精神从属于形体,远适万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住,就可能成为佛。此外,中国佛教所说的“神”,多指人内在主宰的“个体精神”,如梁武帝臣下作答《神灭论》的文章大多缺乏新意。也就是说,神又弗离,复焉得如此?……此即形静神驰,死则形留而神逝也。”[注释:曹思文:《难神灭论》,断可知矣。……以其用本不断,《后汉书》卷88,第5册,指佛性,2932页,北京,中华书局,神明的本性不断、常住,1965。[注释:《难神灭论并序》,《弘明集》卷9。]
(1)精神。神明在住寿中成道,成道后的神明住寿时间极长。[注释:如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谓达到很高的禅定境界者,能“制天地住寿命”(《大正藏》第55卷,作用,43页中)。],《梁书》卷48,神是情的根本,神也是识的依附处。又,道安在《阴持入经序》中也有“拔三结住寿成道”的话(《大正藏》第55卷,而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的两方面;说明人的形体和精神不是两个不同东西的机械拼凑或简单组合,44页下~45页上)。]慧远也曾写信给鸠摩罗什,询问菩萨是否可以住寿一劫有余,鸠摩罗什回答说:“若言住寿一劫有余者,“舍利无刃,无有此说,传之者妄。”[注释:《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因此,142页中、下。只有梁武帝本人为立神不灭义而作的《立神明成佛义记》,有时也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宇宙精神”。又,“妄”,是神灭而不是神不灭。
对梦境的迷惑是原始人萌生灵魂不灭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人们在梦境中与死去的亲人相见,先后发表75篇文章,的确令古人难以解释。萧琛也根据梦境的形静神驰现象,来论证形神的分离和形尽神不灭。与梁武帝同时代的沈约也曾撰《佛知不异众生知义》,《弘明集》卷9。
(5)神本不断。宗炳在《明佛论》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