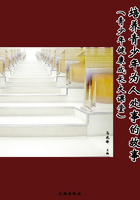中国佛教学者围绕因果报应学说进行论述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业报轮回与由凡转圣的主体问题。他们根据中国固有的灵魂不灭等观念,阐发了神不灭论。这一理论关系到神与形、灵与肉、生与死、今生与来世、人与鬼神等一系列哲学问题,是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说的思想基础和整个中国佛学的中心命题。神不灭论既和印度佛教无我认相悖,又和中国固有神灭论冲突,由此在佛教内外引发了歧解和纷争。中国佛教学者在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中,充分阐发了神不灭论的丰富意蕴,成为极富特色的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令人困惑的重大哲学问题
佛教是神灭论还是神不灭论?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这两个问题在印度佛教内部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前一个问题中的“神”是指精神,后一个问题中的“神”是指神灵。这两个问题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理论前提和逻辑根据,具有更为重要的哲学意义。简要叙述中国佛教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尤其是对前一个问题的看法,对于了解中国历史上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以及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两个问题的对立见解
关于印度佛教是神灭论还是神不灭论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佛教尤其是早期佛教是否定精神不灭、灵魂存在的。这可称为佛教灭论说。这种看法的具体理由是,早期佛教是在反对当时印度流行的灵魂不灭说、个人精神本体“神我”的常住独存说的斗争中形成的。早期佛教认为,人是由五蕴和合而成,并没有一个恒常自在、联结生死的实体存在,也没有超乎形体和精神之上的另一种东西——“我”,也就是说“人无我”,或“人空”。“人无我”是一种反对人的精神、灵魂不灭的独特表述。
和上述看法不同的另一种见解是,认为佛教肯定了变相灵魂的存在。早期佛教十二因缘说的“识”,是托胎时的心识、精神的活动,也就是轮回报应的主体。“行缘识”,“行”,潜在的意志活动;“行缘识”是表示由潜在的意志活动产生具有分别作用的识。“识缘名色”,“名”指心、精神;“色”,指色质、肉体;“名色”就是指胎中的精神和形体;“识缘名色”是表示由识进而形成有生命的个体。后来有的部派佛教,如说一切有部为了进一步解释轮回报应的主体问题,提出“中有”(“中阴”、“中蕴”)的理念。“有”,生存;“中有”,指前世死亡的瞬间(“死有”)与次世受生的刹那(“生有”)中间过渡时期所受的身,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灵魂。但是,大众部、说出世部等则不承认“中有”的存在。后来大乘佛教又主张“中有”为有无不定的两可说。与“中有”的有无问题相联系,部派佛教犊子部、正量部和经量部还承认“补特伽罗”实有。“补特伽罗”,梵语pudgala的音译,意译为“数取趣”,意思是数度往返五趣(五道)的轮回者,也就是轮回转生的主体,自我存在。后来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进一步认为有情众生的根本识“阿赖耶识”(alaya-vijnana)是轮回转生中的执持识,是众生转迷开悟,从凡夫直至成佛的生命主宰,也就是因果报应的主体。这种主体被认为是不灭的灵魂,从而肯定佛教的神不灭论。神不灭论是佛教有神论的理论基础。
关于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的问题,也有两种看法。一种坚持佛教是无神论,另一种看法认为佛教是有神论。
认为佛教是无神论的理由是佛教并不信仰绝对的神。释迦牟尼本人就反对当时婆罗门教的梵天创造宇宙万物和主宰一切的说法,否定世界上万物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的存在。早期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造物主和救世主,不是万能的绝对的神,而是一位觉者、尊师、教主。释迦牟尼也从不希望弟子及信徒对他盲目崇拜,他遗言嘱咐弟子要“依法不依人”,强调佛教信仰要以“法”即教义为归依。
认为佛教是有神论的根据是,早期佛教容纳了印度神话诸神,这些神虽被定位为生灭众生的一部分,并不居于绝对的地位,但毕竟是高居于人类之上的天神。又,释迦牟尼虽遗言依法不依人,然释迦牟尼作为佛、法、僧三宝之一,也是归依对象之一,而受信徒的礼拜。部派佛教时期,佛教信徒追慕释牟尼的人格和功德,更形成“永恒释尊”与“久远佛”的观念,有的部派提出了“超人间佛陀”或“超自然佛陀”的说法,把释迦牟尼看成是神圣的人格神。这就导致了信奉对象(本尊)究竟是法还是佛的重大争论。后来,大乘佛教又进一步强调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和他力得救,并由早期佛教时期只限于释迦牟尼一个佛,进而提出了十方三世有无量数的诸佛,并把佛奉为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神格化的救世主,从而使佛教成为典型的有神论宗教。
以上简要论述了关于印度佛教主神灭还是神不灭,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的两种对立见解及其论据,对这个两个问题的不同见解,中国佛教学者极为关注,并结合中国相关固有观念从理论上作出了回应。
二、中国佛教的一般回应
佛教传中国之初,在中国人看来,它的因果报应和修持成佛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承认有神,是逻辑地肯定人死精神不灭和佛为神灵的。袁宏《后汉纪》云:
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注释:《后汉记》卷10,5页。]
神明受报,修道为佛,从汉代以来就被中国人认为是佛教的要义。早期佛教讲的因果报应的主体,是指十二因缘中的“识”,中国人以为是“神”,这个“神”是指精神、灵魂,与“识”的心识活动原义是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把它们混淆为同一概念了。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期,中国人认为神不灭论是佛教理论的核心思想。
与上述看法相联系,中国人也把佛视为神,如《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注释:《楚王英传》,《后汉书》卷42,第3册,14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浮屠”,即佛。东汉初年,上层社会把佛与黄、老同样作为崇奉的对象,洁斋祭祠,祈求福祥。后来汉桓帝也“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以“听于神”[注释:《教桓帝纪》,《后汉书》卷7,第1册,3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把佛当作天神祭祀。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认为佛教是神不灭论和有神论的看法,也曾受到过批评。后秦著名佛经翻译家、般若学者鸠摩罗什就指出了“阿罗汉住寿命”、“菩萨可住寿一劫有余”等住寿之说,是与佛理相抵牾的妄传。直至近代,章太炎还发表《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人论》等数篇论文,宣称佛教为无神论。杨度也说:“悟灵魂说为外道,而非佛法。”[注释:《新佛教论答梅光羲》,《杨度集》,718页。]梁潄溟也声称“佛法为明确之无神论”[注释:梁潄溟:《印度哲学概论》,1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围绕佛教是否主张神不灭、佛教是否主张崇拜神灵,中国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
三、形成分歧的深刻原因
从佛教哲学发展史来看,形成上述的分歧和争论,是有着佛教的内在理论发展逻辑和历史演变的深刻原因的。早期佛教在哲学理论上主要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断、常二见,提出缘起论,宣扬无常、无我和因果报应说。所谓断、常二见,“见”即见解、观点;“断见”是认为人和事物的内在主宰者“我”死灭后就断了,“我”并不受因果报应的支配;“常见”是认为“我”即人和事物的内在主宰者是常住不断、永恒不变的,就人来说也就是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早期佛教反对这两种看法。但是,在形式逻辑范围内,非断即常,非常即断,否定断见,就会导致灵魂不灭论。主张“无我”,生死轮回的主体就失去着落。肯定“无常”,对永恒的涅盘境界说,就易生疑惑。害理论上的矛盾、困难,势必导致后继者在观点上的分歧,也势必导致对佛教报应主体的不同评述。而后来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在报应主体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无疑更加深了人们在佛教的神灭和神不灭问题上的观点的对立。我们认为,从佛教的理论结构来说,神不灭论是其因果报应说的逻辑要求,中国佛教学者的神不灭论学说正是对佛教因果报应主体说的重大发展。
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
人的形体死亡以后,人的精神是随之消灭还是继续存在,即“神灭”还是“神不灭”的问题,是先秦以来中国哲学不断探讨、争论的重要论题。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佛教学者着重结合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成佛论、佛性论、法身论等思想,阐发了神不灭论。
东汉时中国佛教的神不灭论学说就开始引起了人们,尤其是儒家学者的怀疑。东晋后期,慧远为了答复人们的质疑而作《形尽神不尽》专文。南朝宋初,出现了激烈反对神不灭论的意见,儒、佛两家互相诘难,彼此开展论战。到了齐梁时代,神灭神不灭的论争更是达到了高潮,书写了中国佛教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篇章。梁代以后,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走向低潮,相应地,这一争论在此后的佛教思想史上也退居于次要地位。
一、论争的开展
神灵不灭,因果报应,是汉代佛教的主要学说。记述中国早期佛教思想状况的重要著作牟子《理惑论》,最早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神灵不灭、因果报应的非难和牟子的回答。文载:“问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注释: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7页。]又,“问曰: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牟子答曰:“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注释: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7页。]问者站在儒家立场上非难佛教生死轮回之说,牟子答以人死是身体朽烂,魂神是不死的。这也是现存中国佛教著作中最早的形尽神存的神不灭说。
二、论争的激化
东晋后期,随着神不灭论思想的广泛流行,更兴起了神形关系的辩论之风。孙盛(字安国)致书罗含(字君章),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注释:《与罗君章书》,《弘明集》卷5,四部丛刊影印本。],认为精神(知)如同形质一样,都可粉散而化为异物,反对神明“更生”的说法。罗含作《答孙安国书》[注释:《弘明集》卷5。]回复。他在《更生论》[注释:《弘明集》卷5。]中,强调“今生之生,为即昔生”。认为万物是不断“更生”的,天地变化无穷,万物必然会不断“更生”;只有天地有终,万物才不更生。又有庾阐阐作《神不更受形论》,已佚。他作吊贾谊辞有曰:“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托神用,故能全生。”[注释:《庾阐传》,《晋书》卷92,第8册,23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据此看来,他反对神能更生受形,主张神灭论。僧人竺僧敷为了反对“异学之徒”的“心神有形”说而作《神无形论》,以形的有尽来证明神的无形。文说有形者就有数,有数就有尽。神是无尽的,所以也是无形的。[注释:详见《竺僧敷传》,《高僧传》卷5,《大正藏》第50卷,355页中。]还有郑鲜之(字道之)著《神不灭论》,认为形与神是平行的,两者是不同的。形神的不同,是指形是有始有终的,神是无始无终的。该文还提出了新的论证,说:“夫火因薪则有火,无薪则无火。薪虽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为用耳。若待薪然后有火,则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阳,阳为火极,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资,亦犹此矣。”[注释:《弘明集》卷5。]这是以火理即火之为火的理才是火的根本、无火之前就有火理的观点,来论证和发挥神不灭论。
慧远所作《沙门不敬王者论》的第五篇论文《形尽神不尽》,是东晋后期阐发神不灭论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神不灭论著作。这篇论文是当时神灭与神不灭辩论的产物。慧远针对“神之处形,犹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毁必灭。形离则神散而罔寄,木朽则火寂而靡托”[注释: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85页。]的问难,进行两方面的答辩:一是强调神与形的区别,认为神不是物质,也不是一般的情识,是“精极而为灵者”。因为“精极”,所以具有“上智”的人,也不能确定它的体状,穷尽它的幽致。因为是神灵,所以“有冥移之功”,“物化而不灭”,“数尽而不穷”[注释: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85页。]。二是用“冥移”和“传异形”的观念解释薪火之喻:“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注释:同上书,86页。]神有暗中转移的妙用,不随形而灭,传于异形而不灭。
南朝宋初,不同学者围绕神灭神不灭的问题,以书函论著,交相攻伐,争论迭起。时有“黑衣和尚”之称的沙门慧琳于宋元帝元嘉十年(公元433年)前后所撰《白黑论》(又称《均善论》、《均圣论》)一文,是当时引发神灭与神不灭论争的导火线。论文假设白学(儒)黑学(佛)双方,较论两者的优劣异同,认为儒、佛学说各有长处,“均善”;儒、佛创始人都是圣人,“均圣”。又认为佛教讲幽冥和来生,并“无征验”,“示来生者,蔽亏于道、释不得已”[注释:《天竺迦毗黎传》,《宋书》卷97,第8册,2391页。],实际上否定了神不灭论。此论一出,震撼了佛教界,为众僧所摈斥。但慧琳颇得宋文帝的宠幸,他的论文更为衡阳内史何承天所激赏,何氏把论文送给慧远的忠实门徒宗炳评论。宗炳作《难白黑论》、《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答何衡阳书》(一、二),反对慧琳的观点,与何承天往复辩难。宗炳作文的中心论旨是神不灭论。他强调人之所以能够成佛,就因为有不灭的神。形神不同,形质至粗,神明实妙,两者归宿也不一样,形有尽而神不灭。神不灭有两种涵义:一是生死轮回的神识不灭;二是成佛法身的神识常住,也就是佛性永在。人在轮回中若能逐渐断除情欲、烦恼,轮回的神识就能归于法身的神识,一旦唯有法身神识时,人即成佛。何承天作《答宗居士书》、《达性论》、《报应问》等,反对神不灭之说。他认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注释:《释均善难》(《答宗居士书》,《弘明集》卷3,四部丛刊影印本。]强调“生必有死,形毙神散”[注释:《达性论》,《弘明集》卷4。]是自然现象,死后神即散灭,不可能转移到另一形体上去。颜延之又作《释何衡阳达性论》、《重答何衡阳》,与何承天辩《达性论》。他说:“神灵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注释:《释何衡阳达性论》,《弘明集》卷4。]他认为人与草木不同,死后“精灵必在”,必当再“受形”,肯定了神不灭之说。何承天作《答颜光禄》予以批驳。同时有刘少府也作《答何衡阳书》,与何承天的《报应问》展开争论。[注释:《广弘明集》卷18。]此外,时有任城彭丞作《无三世论》,僧含法师特撰《神不灭论》与之抗衡。[注释:《释僧含传》,《高僧传》卷7,《大正藏》第50卷,370页中。]以上足见晋末宋初神的存灭之争,已蔚成学坛论辩之大观。
三、论争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