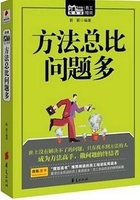1
我是个不善于旅行的人。
善于旅行的人装备精良,行囊里永远只揣着必需物品,对旅途无益的玩意儿,通通丢个干净!而我只是打包,把所有的东西打成一个又一个的包裹——爱、恨、情、愁、回忆、梦想、痛苦和绝望,通通背在身上,佝偻着,四处去流浪。
“I was standing,all alone against the world outside,you were searching,for a place to hide,lost and lonely,Now you`re given me the will to survive,When we`re hungry,Love will keep us alive……”
Pauloner的乐队忽然轻轻吟唱起了这首歌。我最喜欢的《love will keep us alive》。忽觉迎面扑来一阵夏日的风。那潮湿的带着青草气息的风,是江南特有的呼吸。山谷、虫鸣、下弦月,还有在月影下摇曳的、相偎的两个孩子的背影……
“喂!”MAY突然大力拍了下桌子,惊醒了如坠梦境的众人。
“你干什么?”我瞪大了眼睛。
“我问你们两个干什么!也不说话,也不喝酒,都发什么呆呀!真无聊!”MAY撅嘴。
“要怎样才算不无聊?”叮当淡淡开口。
“找点什么来玩玩嘛!喝酒、跳舞、玩骰子……什么都行啊——总比干坐着好!”
我看看叮当。
叮当看看我们,神秘兮兮地笑。“来了。”她说。
“什么来了?”MAY不明所以。
“玩的乐趣。”叮当保持高贵而莫测的笑容,有意无意地将眼波绕到我们背后,转了一转。
答案由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耳边揭晓:“三位美女,可以认识一下吗?”
我与MAY同时转头,看到了一个男人立在身后。
这男人理了个清爽的短发。穿格子衬衣和米色长裤。长相普通,但并不讨厌。属于街上一块钱十打那种,过目即忘。
MAY瞟了他一眼,低头兴味索然地抓了把爆米花塞进嘴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男人没钱没关系,相貌平庸或者丑陋,就绝对不可原谅!
叮当优雅地吸了口烟,声音如同青黛色的烟雾柔和而冷淡。“对不起,我们没兴趣。”
男人显然没有准备碰到这么一个硬钉子,错愕了一下,抓了抓头发。“呵呵……这个……我没有恶意……只不过是想……”
“想什么都跟我们没关系。”叮当面无表情,“请别打扰我们。”
“哦……好吧……”男人尴尬地把手插回裤袋里,看得出他紧紧地捏了下里层的布料,“那么……Bye-bye!”
我望着男人落荒而逃的背影,心怀不忍。
“你也太狠了。”我对叮当说。
“无所谓啦!”MAY伸了个懒腰,“这么傻不拉叽的家伙,无审美情趣!”
“而且还没钱。”叮当镇定自若。
“你怎么知道他没钱?”我很吃惊。
“要学会看人哪,小妹妹!”叮当笑,“人的口袋里到底瘪不瘪是绝对看得出来的!”
“怎么看?”
“第一,你看他的手表。Casio的,而且很旧,表带有些断痕。表明他只有这么一块手表,戴了很多年。第二,你看他的衬衣,明显很皱。估计就是洗衣机里随便洗了洗,也没烫就穿了——好的衬衣可都是要干洗的。第三,他的皮带。那种光泽明显不是上好的牛皮的光泽,皮带头上的图案也不知道长得像谁,来历不明。第四,他的皮鞋居然是圆头绑带子的!这么老的款式,我爸爸都不会穿!第五,在酒吧里跟美女搭讪,一般人说的第一句话都会是‘能不能请你喝一杯’,而他一开口就是“能不能认识一下”,表明他连三杯啤酒都不敢请。第六,……”
“天哪!”MAY惊叹,“现在拜你为师还来得及吗?”
叮当笑:“这种事要看天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自个儿慢慢琢磨吧!”
“琢磨是琢磨不出来了。”MAY肯定地摇头,双眼闪闪发亮,“不过,下回我再挑男人,一定要带上你做导师!”
“叮当的品位跟你不同。”我笑着打岔,“在她眼中,这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有钱的,一种是没钱的——在你眼中,这世界上也只有两种男人,但一种是你的男朋友,一种不是。”
MAY格格地笑了起来,作势就要打我,“女人从来就是为了爱而生的,懂么?”
我哼哼一声,讪讪地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大口——这话茬儿我接不了。我在MAY的理论下,立时成了一个死人。
叮当突然掐熄了烟蒂站起来。“去跳舞吧!”她说。
“好啊!”我立刻附议。
“早该想点有意思的节目了!”MAY一下跳了起来。
2
对于女子而言,你在酒吧里所跳的舞蹈,将会直接影响到男人对你的评判和欲望——是先认识再开房的欲望,还是先开房再认识甚或拍拍屁股走人的欲望。据说男人看到舞池里腰肢如水蛇般灵活扭动的女人,就会很容易产生后一种欲望。
音乐很强劲。
我提醒着自己——身为一个好女子,即便她真的缺少一个男人,但她需要的应是一个拉着她的手躺在她身旁睡觉的男人,而绝不是一个趴在她身上睡觉的男人。
“小姐?小姐?”嗅觉有偏差的人依旧存在。
“小姐!小姐!”那家伙开始拍我的肩膀。
还没转身,我已经先横着一个眼风扫了过去。却是瞥见了那张被叮当打败的没钱男人的脸。男人尴尬地摆了摆手:“嗨!”
我飞速瞟了MAY和叮当一眼。她们正在专心致志地摇头晃脑,连眼皮都没动一下。我又把目光拉回到他脸上。
“我朋友说他认识你!”他在我耳边大声地说。
我不可自抑地浮上来一抹轻蔑的微笑。不说话。双手环抱在胸前,故意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看来一个人的自尊程度果然与他荷包的肥瘦程度成正比——在这一点上,倒当真是男女平等。
他一时有些窘。红了脸,结结巴巴道:“不是……你不信么?我没骗你……真的……”
“Hey!炎炎!”一个声音远远飘过来。
我猛地扭头四下张望!找不到熟悉的面孔。尽管对于我这个近五百度的大近视来说,这个动作纯属多余。
就在我怀疑这声音来历的时候,一只大手突然雨伞一样张开来,盖在我头上,用力抚乱了我的头发。
只是刹那间,我像个疯子一样不受控制地惊跳起来!
我迅速回头!鼻尖撞上了一具坚硬的胸膛。淡淡的古龙水的香气混杂着烟草味道一下钻进我的鼻孔。没有汗味。干净的浅黄色T恤上,还留有阳光干燥的气息。这是一个健康而自律的男人。
“怎么啦,你这丫头!几年不见,就不认得人了么?”他大声地说。低沉而微微沙哑的声音里藏了一张明朗的笑脸。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血液中的颤栗泛滥到外面来。可是没有用!我的嘴唇那样的凉。额角的青筋隐隐凸显,腾腾地跳动着,尖锐而刺痛。
回忆的包裹碎裂了,沉睡的封印解开了!尖埃扑嗦嗦地掉下来。一张熟悉的脸庞仿佛穿越了千年的荒漠来到我面前。
“怎么,真的不认识我了么?”他笑嘻嘻地望着我。
我小心翼翼地望着他。
浓浓的眉。挺直的鼻梁。单眼皮。狭长的眼睛里透出狭黠而愉快的光。厚薄适中的嘴唇抿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嘴角向上,像笑容。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一个惹人眼球的亚麻色莫西干头。前面一簇还夸张地染成了金黄色。
“天哪!”我惊呼,“你怎么把自己的头弄成这个鬼样子!”
他大笑起来,又伸手过来蹂躏我的头发。“你这野丫头!小时候老在我屁股后面‘晓峰哥哥长,晓峰哥哥短’的,现在倒好!见了面连人也不叫一声,没规矩!”
我突然咬了嘴唇,低下头去,却是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晓峰贼亮的眼睛X光般把我从头到脚扫射了一遍,点了下头。
“嗯,不错!是个大姑娘了!”
我抬起头来,勉强笑道:“八年了,还不长大吗?”
哓峰歪着脑袋想了想,也不禁失笑:“是是是,算来倒真是有八年了!怎么样,这八年过得还好么?”
“还行吧!不再到处野了——你一走,我便成了个好孩子。”
“哈哈,这话说的!好像是我把你带坏了似的!”
“怎么不是!那回……”话到这里却突然哽住了喉咙。我兀自抿了抿嘴巴,一个硬块棱角分明地割着食管壁一路滑下去。
“喂喂喂!把我们当透明的了!”MAY挤了过来,一手搭在我肩头,一手拉着叮当。叮当的一双火眼金睛,显然已经在透视这个男人的身家。
我慌忙打断:“哦,对了,我来介绍——这是MAY和叮当,我的好朋友。这是晓峰……”一眼瞥见晓峰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咬了下嘴唇,轻声补上两个字,“哥哥……”
“总算你还有点良心!”晓峰一拍手,笑道。
“哥哥?”MAY吊起一只眼睛来打量我。
我被她逼得慌,舌头竟有些打结:“是我在A城从小一起长大的隔壁邻居……好朋友……比我大两岁……”
叮当扑嗤一下笑了出来:“我们又不是查户口的!那么急着撇清,就撇得清了么?”
我顿时涨红了脸,待要分辨,却是一句话也想不出来——我庆幸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灯光昏暗,遮盖住了我脸上灼灼的炭火。
晓峰不便多言,但也不想让几个女人以他为标的物展开一场研讨会,于是便打岔道:“有幸见到这么多位美女,值得庆贺啊!”
MAY一偏头,挑起一眉毛来端详他,却被叮当推了一把。
“行啦!人家可是炎炎的‘哥哥’,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她刻意加重哥哥的发音,我脸上的火烧得更旺了。偷偷瞄了眼晓峰,却只是看到他脸上呵呵的笑容。
3
几个人坐下来,我便发现了一张平淡的脸。那个不幸被我们羞辱了两次的男人神色镇定地端坐在那里,仿佛打不死的昆虫。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看吧,我说我朋友认识你吧?还以为我真想泡你呢,臭美!
晓峰介绍说昆虫的名字叫“奇伟”。我暗自偷笑。这个又奇又伟的名字,倒像是他本人的反义词。
晓峰的另一个朋友叫Michale。据说是在澳洲读书时结识的好友。长了一双玉狸眼,分外撩人,却似有些阴柔之气。MAY偷偷凑过来在我耳边说:“这男人长得倒是不赖,可惜有点‘屁’!”(上海人管同性恋叫“屁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