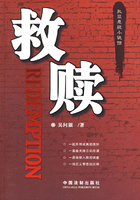1
我把头仰起来。
尽量地仰起来。
潮湿的海风穿过我黑色的长发,带来海水淡淡的咸腥气味。星星正在闪耀。很大颗。细碎的光流淌过面颊,抚摸我伸长的脖颈。身体很烫,睁开眼睛看到的净是点点的乱梦星光。
我忽然有些迷惑。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何年。
“后来呢?”有个声音在耳旁响起。
“后来呢?”她又问。
我迷迷蒙蒙地转头,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
“后来呢?她怎样了?你倒是快说呀!”她着急起来,拿胳膊肘一个劲儿地捅我。
我终于从一片乱梦之中惊醒,用力眨了眨眼,定睛看了看面前的这张脸孔。
“哦,简儿。”我说。
“废话!当然是我啦!在问你话呢,也不理人!”简儿瞪眼。
我笑笑,低头去喝啤酒,却发现手中的罐子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清空。我把它倒转过来,晃了晃,一下扔出去老远。
“她后来怎么样了?快说!”
我侧脸看她:“你问谁?”
“叮当!”
“哦,”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后来她回到家里,发现已经人去楼空,连地上的血迹都不见了——白宇就像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般,永远地消失了。”
“那她呢?”
“她么?”我笑笑,“她也走了。用那张卡里的钱重新租了一套房子住下——又遇到了很多男人。年轻的,年老的,漂亮的,丑陋的,有钱的,没钱的……各种各样的。再后来,她遇到了一个跟你……老公差不多的男人。她跟了他——也做过很多工作——直销、卖服装、卖化妆品,后来又自己开了家投资公司。再后来……”
“哦,我知道!”简儿连忙插嘴,“就是骗钱!——你都说过啦!”她格格地笑了起来。
“那她现在呢?在做什么?过得好吗?”
“她么……”我笑了起来,“已经做了人家‘少奶奶’了。”
“真的呀!”简儿叫。看她那一脸开心兴奋的样子,仿佛倒是她做了人家的少奶奶。
“是谁?是谁?她嫁给了谁?”
“你干吗这么兴奋?”
“哎呀!”简儿跳了起来,抓着我的手臂一阵摇晃,“说嘛!说嘛!快告诉我,她到底嫁给了谁?”
我笑:“你那么着急做什么!——故事长着呢!今天可讲不完!这么晚了,早点回去睡吧!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简儿一怔。看了看我,低下头轻声道:“我不想回去。”
“总是要回去的,或许他现在正在酒店里等着你呢。”
简儿重重哼了一声道:“你以为他还会在吗?”
我一时语结,只得干干地笑了笑。
“我跟你回去好么?”简儿突然说。
“呃?”
“你住哪儿?”
“XXXX。”
“好!”简儿一下跳起来,拍了拍裙角。脸上挂着认真的孩子气的笑容,“那快走吧!回去好好睡一觉——我累了!”
我苦笑。
我发现我非常不善于拒绝孩子的请求——尤其是当面前的这个孩子霸道且脆弱的时候。
回到酒店,简儿非常自觉而迅速地给自己洗了个澡,穿上了我的睡衣爬到床上。
“我先睡了,宝贝,”她打了个哈欠说,“我想你应该不止带了一套睡衣。”
我双手环抱在胸前打量这个自说自话的女人。她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激越的行动力,还有渴望——非常直接的赤裸的渴望——她所要的,总是那样浓烈而丰盛。宛如一头穿梭于丛林间的小豹子——然而小豹子有时也会虚弱。是年轻的生命不可避免的稚嫩。
小豹子突然睁开眼睛,发亮而机敏的眼珠子里被揉进了一些蒙蒙的灰。
“炎炎,亲我一下好吗?”她说。
我一惊:“说什么?”
“求你,亲我一下,否则我睡不着。”
“可是……”
她笑了起来:“你放心!我不是lesbian!这只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我喜欢有人在我入睡前亲吻我。感觉我是被爱包裹着入眠——那比什么都安全。”
“如果没有呢?”我说。
“那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她说。
“好吧,”我叹了口气微笑,“为了你能好好地睡一觉。”
我走到她床前蹲下来,轻轻亲吻了她的额头。
“晚安,小公主!”我对她说。
“晚安,宝贝……”她又打了个哈欠,朦朦胧胧地半瞌着眼睛。
“对了,你忘记告诉我,MAY后来怎么样了?”
我笑,轻轻捋了捋她的长发。“明天再说吧,亲爱的。现在你累了,需要休息。”
“嗯。”她点点头。
“炎炎?”她闭上眼睛模糊地说,“你来这里是因为晓峰吗?这片海有你跟他曾经的回忆——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对吗?”
我微微一怔,伸出去的手僵在她额头。
“哦,炎炎,”她说,“你很想念他……”
“……”
简儿这句话并非问话,她自己给了自己和我一个答案。然后咂吧了下小嘴,兀自翻了个身,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我坐到宽阔的窗台前。把头枕在膝盖上,侧脸看窗外的大海。海面黝暗。看不清汹涌的暗流。耳边简儿匀称的呼吸却仿佛潮汐有节奏地涌动。
远处的建筑站在暗影里,带着坚硬的棱角。天边竟有一丝微光。红红地反衬着黑夜的影子。我知道新一轮的交替又将从那里开始——总是如此——暗夜与晴空、希望与绝望——而人只是一个沙漏,把一些东西颠过来倒过去,从中空的洞里慢慢漏掉。
我掏出手机拨出了一串熟悉的号码。
振铃声响起。等待惶然而漫长。
一声、两声、三声,在寂静的深夜,仿佛叹息。
终于,在濒临绝望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问候:“嗨,炎炎。”电话那头的人说。
我鼻子一酸,忍不住落下泪来:“叮当!……你好吗?”
“啊,还行吧,”叮当的声音听起来软棉棉的,似是仍在睡梦中,“你怎么样,还好吗?”
“嗯……”我紧握着电话点了点头,“对不起,吵醒你们了吗?”
“哦,没有,”叮当轻轻地说,“我老公不在。”
“不在?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下班以后就没回家——不提他了,你怎么啦?这么晚了还没睡吗?”
“嗯……我……睡不着……”我的喉咙在打结,声音开始发颤。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我只是……很想念你们……”
“哦……”叮当幽幽地说,“你还是那么不快乐,炎炎。”
“叮当,我好想你!我好想MAY……可是你们都离我那么远,都不在我身边……”
叮当忽地叹了口气,“炎炎,你要学会从过去当中抽身。”
“我不是……”我哽咽,“叮当……我……”
“任何事情都需要代价,炎炎。”叮当说,“没有一种生活会没有痛苦——这只是我们的代价——为了我们要的,为了离开。”
我忽然打了个冷颤。抬头望望冷气的出风口,一根鲜艳的红色丝带在那里抖得异常凶悍。犹如巨蟒的红信。
我用力深吸了一口气,点了下头:“嗯!我知道……其实我只是……叮当,对不起!”
“我们之间,不需要对不起!”
“嗯!”我努力让自己微笑起来,“……你怎么样?跟你老公过得好吗?”
叮当笑了。“好不好并不重要——那只是另一种代价,炎炎。”
2
没有一种生活是没有痛苦的——叮当深知这一点。
所以,她总是很惯于忍受痛苦。
预备开在义乌的那家投资公司,在经过了数周的分娩阵痛期之后,终于顺利地降临这个世界。
叮当毫不犹豫地又打包起了她那三个大箱子便能装完的所有家当,风风火火地便要奔赴义乌。
她笑笑地说,要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去远方。
阿辉默默地看着她,眼底有灰色的影子。叮当,你……真的……
是。叮当说。
叮当,你……能不能……
不能。叮当头也不抬。
我和MAY都较为同情弱者。
你也太狠了。我说。
阿辉也真够可怜的。MAY说。你走了,他一个人怎么办?
叮当只是淡然。
任何事情都需要代价。她说。这只是我们的代价。
你真冷酷!MAY说。
叮当笑笑。我们只是一群行进在旅途上的人,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这一站赶往下一站——至于擦肩而过的路人会怎样,我们根本无谓去想。
太可怕了!我故意叹了口气。你的血是凉的。
叮当吐出了一个漂亮的烟圈。
这不是冷血。她说。这只是清醒——尚且无法对自己负责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谈论责任?
我和MAY突然都不说话了。
3
我再一次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
黄色大领口毛衣。黑色仿皮瘦腰外套。紫红色纱巾长长地垂在胸前。大而漂亮的眼睛。高而挺直的鼻梁。厚薄适中的嘴唇,再配以披肩长发和精致的妆容——我很高兴。虽然已过花季之年,我却仍暂且留住了傲人的美貌。这让积压在我身上的莫名其妙的紧迫感稍稍减轻了一些。
晓峰来了电话:“可以摆驾了吗,老婆?”
“还不行。”我笑,“最少再过两小时!”
晓峰也笑:“我是无所谓啊——等老婆大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怕MAY他们不答应!”
“就你会说!”我嗔道,“等着!我这就下来了。”
今天是叮当留在上海的最后一天。MAY亲自下厨,特地煲了一锅材料十足的鸡汤为她饯行。我和凑巧前来上海看望我的晓峰自然也在受邀请之列。
一进MAY的家门,叮当身旁的空位便格外扎眼
“你家那位呢?”我朝那空位努了努嘴。
叮当微笑:“我没让他来。”
“为什么?”我睁大了眼睛,“今天可是临别秋波呀!”
叮当点点头:“这就是原因。”
MAY和她的那位“老公”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瓶红酒。
“来啦?”她斜眼打量我,“知道自己迟到多久么?”
我抬腕看了看表,“十几分钟嘛。”
“是二十五分钟!你的破表该扔了!”
“好吧”我笑,“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很简单,”MAY说,“迟到的人,该罚洒。”
“怎么罚?”
“一人三杯。”
“用得着这么狠么?”我吃惊道。
“不狠一点,你长不了记性——迟到大王!”
“好吧,姐姐!”我赶忙陪笑脸,“是我不对,是我错!可我的酒量,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MAY笑笑地睨了晓峰一眼,“你不行,可以找人代呀!难道这么大一个美女,竟没有英雄来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