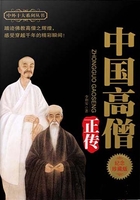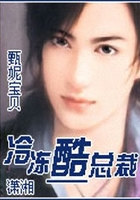前言
我曾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健起来,却没能提升思想与灵魂;我挣了足够多的钱,解决生存问题,但却无法填满内心的缺憾;我画画,在艺术的世界里遨游,但艺术不足以成为排遣郁闷的出口。机缘巧合,我选择了航海,历经无数常人无法体会的苦难,结果成为第一个驾着无动力帆船孤身完成环球航行的中国人!
人们总是喜欢用征服、战胜之类的词来形容航海活动,但是,只有当真正到了海里,才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渺小。在大自然海洋的力量面前,人类简直是不堪一击的。据说万物都是从海洋来的,那么这里也应当是我的归宿。只是我不甘愿在这一刻被大海吞没,只要理想的风帆还没有降下来,我就会坚信任何一个生的希望。
人生是不是抵达终点时的鲜花、掌声、荣誉和总结?如果那是人生,我还没有靠岸。
人生是不是行走过程中的狂风、巨浪、涛声和夕阳?如果这是人生,那我正在其中。
现在中国人正在做着一个“大国梦”,正在准备做一个“大国民”,那么海洋必然是这个梦中的一部分,也必然是这个身份的一个标签。
1.错失台北,痛失我爱
2008年12月11日晚10时半(注:夏威夷时间),窗外狂风怒吼,急雨敲窗。
宁静的书房里突然手机铃声大作,上面显示了翟墨海事卫星电话号码。“茱莉亚,我看到有个台风在我身后,请你问问你先生,它有多大,风速多快,什么时候会赶上我,还有台风具体的位置。”窗外风雨声更紧更急。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日照号”在黑压压的乌云底下,任凭狂风撕裂,骤雨劈打,汹涌巨浪将其抛向空中的险境,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控制了自己的声音,平静地说:“别慌,我马上与在印度洋迪雅戈岛上的我的先生联系,你半小时后再打过来吧。喂?喂?喂?!”电话断了。我赶紧联系我的船长先生。一会儿,E-mail中附上菲律宾海域地图传过来了。先生说不太妙,翟墨正在热带风暴中心即将经过的在线,让他赶快往南边躲一躲。不过那边的风浪比较大的……
四十五分钟后,手机又闪起来。是翟墨的号码。冲着电话我大叫,你快吓死人啦!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从图上看,估计台风要两天才赶上你,而且有由西往北偏的趋势,应该说,你还是安全的。叫完以后给了他一颗定心丸吃。
以上节选自茱莉亚的博客,讲述我离开关岛之后,遭遇台风的情形。非常感谢她如此精彩的描述,这篇博文我现在看起来还非常心悸。
但是更多的是心痛。正因为这场台风,我和阿美没能走到一起。
准备离开夏威夷的时候,阿美正好有飞行任务,不能送我离开。我和她约好了在台湾见面。但是途中“老伙计”又出了点小故障,我被迫向关岛进发。要阿美过来和我会合,她说有任务,不能直飞关岛。
没办法,我还得前往台湾。可就是在这番折腾中,台风“白海豚”跟在了我的后面。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对比“日照号”和“白海豚”的速度,这股猛烈的台风三天之内就能赶上我,到时候就会是一场悲剧。
正如茱莉亚电话中我呼喊的那样,台风一直尾随着我,让我恐惧不已,只能依靠唐纳德舰长用最先进的设备导航了。茱莉亚和唐纳德传来了非常有用的情报,我与“日照号”按照她的指示,在关岛停留一周后,没有去台湾,而是直插菲律宾。
船毁人亡的悲剧是避免了,但没想到后来困守菲律宾的日子,我却发起高烧,无法再去台湾。没有想到,这一次和阿美失之交臂,竟然成了永远的遗憾!
早在夏威夷时,我和阿美就约定了去台湾的时间,无数次憧憬过她在码头迎接我的情景。困守菲律宾的日子,我天天扳着指头数日期,想去又不能去,内心的焦躁一天天加重。终于,在我们约定的日子,我没能出现在她面前。接到她的电话时,我正停靠在菲律宾一个荒无人烟的岛旁,奄奄一息地躺在“日照号”上,与突如其来的高烧搏斗着。
电话那端传来阿美带着哭腔的声音,质问我为什么会失约。我口干舌燥,有气无力,不能解释,也不想解释,默默挂断了电话……
那一刻,我想起了安琪,想到她为我担心病倒进医院的事。此时此刻,我正怀疑自己染上了登革热,在这无医的荒岛上,能不能活下来还是未知数。生死未卜间,我不能把真相告诉阿美,不能再让心爱的女人为自己担心!不解释,就让她以为我是一个负心汉,恨我,忘掉我,重新寻找新的幸福吧。
“等归航的时候你来台湾,我带你去吃好吃的!”阿美的话至今犹在耳边。
靠着那堆过期的药物和顽强的意志力,我和高烧对抗了五天五夜,最后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但我和阿美,却从此永远地分开了。
困守在菲律宾的时候,对于我和阿美之间,也静静地想了很多。正如航海的人总不会永远停靠在港湾一样,航海人的恋情也总是在风雨中飘摇。飞行员是一个非常忙的职业,而航海人很少会永远固定他的锚。等着她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我们都是特别极端的人,两个人都在等待对方,这种等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和阿美之间,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飞行需要关注气象,航海也需要关注气象,和她在一起,我能体验到那种强烈的心灵共振。我深深明白,自己在不惑之年,再一次遭遇真爱。漂泊多年,我也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等自己回家的女人,我很珍惜这段感情。
可是,这种真爱,也使我们彼此牵肠挂肚,异常痛苦。她那边一起飞,我就揪心,直到她落地给我报平安,这颗心才放下。我这边一起航,她也是不眠不休地等待我报平安的电话。这种滋味太难受。一个是振翅高飞的鸟,一个是潜翔大海的鱼,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一起呢?
我和阿美就这样遗憾地分开了。告别安琪的时候,我心痛如刀绞,让船漫无目的地漂流;告别酋长女儿的时候,我充满遗憾,因为那离我的艺术梦想——“寻找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大溪地”——只有一步之遥;和阿美的分手却连告别也没有。也许她当时会哭,会整夜等我的电话,会唱那些伤心的情歌,可是我已经无法去台湾。
我想清楚了一个航海者的宿命,恐怕我注定孤独,只要我的心还漂流在海上。
再一次,痛失我爱!
打开那台载满歌曲的MP3,宿命般的,我听到了齐豫那清冷凄楚的声音,正唱着《飞鸟和鱼》:
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你一次失速流离,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
你勇敢,我宿命,你是一只可以四处栖息的鸟,我是一尾早已没了体温的鱼,蓝的天,蓝的海,难为了难为了我和你……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听着听着,我竟泪如雨下!
2.画了一个圆满的圈
也有令人振奋的事情,被台风“刮”到菲律宾苏里高后,我完成了自己的环球航行!
12月14日,好友安文彬传来消息:“按照跨越所有经度就算环球航海的界定,此时你的行程,事实上已完成了环球航海。山东省日照市负责人准备在12月15日下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日照号’环球航海成功归航新闻发布会。”
我在这边兴奋地挥起了拳头,太棒了!
电话挂掉之后又遇到了台风,我关闭了电话。原本准备15日下午16:00发布会那边与我有个电话联线。这时的意外情况我关闭着手机。直到台风干扰减弱,发布会才终于联系上我,日照市长赵效为、副市长解世增分别与我进行了卫星通话。我告诉他们,我这边虽然风浪很大,但目前是安全的,属于正常航行。
世界在这里,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圈。我轻轻抚摸着“日照号”这个老伙计,两年相处下来,我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我想起了和它相处的点点滴滴。
还记得大风大浪中,“日照号”倾斜到几乎水平,却始终坚持着没有翻覆。它用结实的躯体抵抗着惊涛骇浪的冲击,给我提供了一片海中的孤岛。
还记得无数个夜晚,我用缆绳把脚和舵绑在一起,就这样固定着“日照号”的方向,我昏昏沉沉睡去,又一次次被舵的转动惊醒。“日照号”像一个老朋友,动动我的腿,告诉我前方有船,赶紧转舵!
还记得好几次,狂风暴雨把风帆撕成碎片,舵的螺丝被一次次打断,老伙计一声不吭,载着我逃离险境……
还记得海上孤独的时候,我甚至与船在对话,只有它是陪在身边唯一的朋友,驱散我的寂寞和孤独。
看着“日照号”几个字,我还会想起那座滨海的美丽城市,想起杨书记,想起出发之前的种种艰难、愁苦与喜悦,心中五味杂陈。
终于,这一站站都走过了,一根根经线变成了写在大海上的历史,缀连在一起,成为我环球航行的标记。
小时候想要证明自己的念头,今天彻底实现了。我曾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健起来,却没能提升思想与灵魂;我挣了足够多的钱,解决生存问题,但却无法填满内心的缺憾;我画画,在艺术的世界里遨游,但艺术不足以成为排遣郁闷的出口。机缘巧合,我选择了航海,历经无数常人无法体会的苦难,结果成为第一个驾着无动力帆船孤身完成环球航行的中国人!
我深深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人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和如此痛苦的折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这一点,我从我自己,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
那一晚我把自己灌醉了,不,其实酒不醉人人自醉,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明亮,风也特别轻柔。
3.波澜里的思绪
出发的时候,我带了一百多本书,回来的时候已经看完了。
白天,把船交给风,我可以唱歌、听音乐、画画、看书,随着风漂流,这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了。难熬的是晚上。有月亮的晚上要好一点,没有参照物的月亮显得硕大无比,我感觉那清凉的月光一直流淌到我心里去了。
往事和旧友此刻会一股脑地冒上来,让我不禁有大吼大叫的冲动;而月亮也隐没在厚厚的云层里时,夜晚才是真正黑暗的,黑黢黢的海面不知道会有什么危机在等待我,没准黑幕里就藏着一个巨大的怪物,没准那些葬身大海的魂灵正漂浮在海面上——电影《加勒比海盗》里不就有这样的场景么?想得我心里直发毛。
一个人就是喜欢胡思乱想,前尘旧事都在心里翻滚,可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恐慌就会袭来,背后有人?远处是什么?没有人我会觉得孤独,而看到有隐约的亮光,我又会马上熄灯匍匐,不知是敌是友,万一是海盗呢?
我已经习惯用海事卫星电话逐一向朋友们报告我的GPS位置,以防不测。这种习惯的养成,来自我对死亡的恐惧——尽管每分钟8美元的话费有时更让我恐惧。
我会不会死在海里?我会死在哪片海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如果有几天看不到一条船,甚至连一条鱼都看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会用睡不离身的尖刀结果自己的生命——救援就别想了,那与其浮沉在海里被泡成一个面团,不如干脆一点,直接结果了自己。
但我还不那么甘心就这样被大海吞没,毕竟“日照号”一路走来,钢筋铁骨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而朋友们的一腔热情,也化作这条船上先进的电子仪器设备。我其实不是一个人在航行,尽管形单影只,但我背负着多少人的目光呢?我沿路拍摄的风景与文化,将让更多人领略到海洋的魅力;一个十几个朋友组成的“密切关注翟墨单人环球航海委员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惦记着我的行踪,等待着我的到来;少阡等人会将我的生活和经历变成文字,见诸报端,更多人会从那些铅墨上读到一段壮丽的旅程,也许这会让他们对大海不再陌生,对生活燃起更灿烂的希望?
茫茫海路,我学会去辨认每一种天象,每一种海洋生物,甚至每一朵浪花,每一道湍流。比如这印度洋上的贸易风。
贸易风也叫信风,指的是在地空从副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低气压带的风。在赤道两边的低层大气中,北半球吹东北风,南半球吹东南风,它们像一个守信的使者,年年以同样的风向,同样的时候出现,因此被人起名为信风。古代时,聪明的商人就知道利用这种风来吹送商船,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这种风又有了贸易风的名字。
印度洋上盛行东南贸易风,而“日照号”正要载着我向东行进!我不是商人,没有算计着顺风而行。这次航行,我没有选择沿岸航行的路线,而是决定横穿大洋。出来航行,如果只挑那些好走的路,那么考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诗人汪国真曾经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真正的风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我很以为然。
我经常听王滨的那首《那一刻》:
那一刻,我落下了眼泪,忽然间看见真实的自己。
那一刻,忍不住说后悔,忽然明白脆弱也是种力量。
那一刻,我承认我害怕,忽然想卸下男人的坚强。
那一刻,只有一个愿望,想大声地告诉你,我爱你……
王滨也是个喜欢帆船,喜欢大海的人。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发起了“纵横四海”法国—中国洲际帆船远航。在海上,曾经经历了电子仪器突然全部失控的状态,不得不利用船上的磁罗经进行导航;还有一次,帆船由于燃料不足,不得不停止使用燃油发电,晚上点起马灯照明,停用了耗电的自动舵,完全依靠船员轮流值班人工掌舵。和他一起航行的朋友说,在航行中,死亡的恐惧是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只能战胜恐惧本身。
人们总是喜欢用征服、战胜之类的词来形容航海活动,但是,只有当真正到了海里,才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渺小。在大自然海洋的力量面前,人类简直是不堪一击的。据说万物都是从海洋来的,那么这里也应当是我的归宿。只是我不甘愿在这一刻被大海吞没,只要理想的风帆还没有降下来,我就会坚信任何一个生的希望。
4.病困菲律宾
接到来自国内的消息,很让我兴奋了一阵。这时是2008年的年底,我已经从日照出发快两年时间了。现在祖国近在咫尺,我忽然想回家了,在海上的日子已经够了。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前面已经交代过,我当时正停靠在菲律宾的一座无名荒岛旁。
2008年12月中旬到2009年2月初,我一直停留在菲律宾。一年多以前来这里时,为了赶路,匆匆忙忙,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多停留几天,好好看看这个岛国。
1月14日,为了避风,我来到一座无名荒岛,人烟稀少,非常安静。我把船停在岸边,昏昏沉沉睡去。
可能打开天窗睡觉,着了凉,我发起高烧,几天都不退,我以为自己得了登革热。这小岛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人烟稀少,又没有医生,我只有靠喝椰子水度日。
我翻出船上储备的抗生素,却发现药品还是两年前的,早就过期了。管他呢,先吃了再说!
我一次塞了一把药丸到嘴里。浑身发冷,这副在海水中浸泡过的身躯,第一次瑟瑟发抖。
就这样过了一天,再次醒来时依然不见好转,又出现浑身乏力症状,看来这船是开不动了。
我忽然想起,菲律宾是航海家麦哲伦的葬身之地。这个不好的念头在我心上笼上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