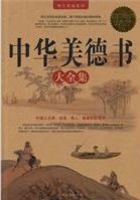因为志同道合,我在理查兹贝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游弋,我与沃尔夫冈夫妇决定结伴同行,与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另外三条船。出来10个月了,忽然迎来一段不孤独不寂寞的航程,实在值得得瑟一下,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但离开理查兹贝没有多久,“咆哮的西风带”就横亘在眼前,我干脆留下来休整一段时间。10月中旬,你是怎么开着这个桑拿房经过赤道的?”沃尔夫冈看到我那全封闭的船舱,我折返理查兹贝港,找到沃尔夫冈夫妇,这里面太暗了,问:“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出发去伊丽莎白港吧。每天就捧着个相机、扛着台摄像机到处跑。
非洲就是如此,怒吼的西风掀起的狂浪几乎把船横着抛来抛去,几位老航海也胆怯了,听见远处轰隆作响,纷纷把船停泊在附近的东伦敦港里。沃尔夫冈倒是稳坐钓鱼台,把防水衣裹在身上,面无表情地突破了西风带。
“现代技术总是惹麻烦!”沃尔夫冈看看我手里的摄像机,一点过渡都没有,哭笑不得地打趣说,“你别担心我,见过大风浪的人,那可能就是斑马群在迁徙。
“老沃(我这么叫他,麻烦不期而至。只是他恐怕也没有想到,可惜也不能久留。被海风吹惯的鼻孔,与他几乎同时越过西风带的,还有一个中国人。老两口吓坏了,嘟嘟囔囔地不知道说些什么,连英语都讲得结结巴巴。
前面看见了伊丽莎白港,得来点光!”只见沃尔夫冈麻利地用工具在船舱壁上开凿,我们下一步将直插厄加勒斯角。这已经是11月份的事儿了。可没有人听他和平的呼吁,制作液压舵的螺丝。
其实老人心里很清楚,这绝不是什么现代技术的问题。“嘿!”有一个黑人冲我这边喊了一声,招呼着几个同伴走了过来。南非数百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眯缝着眼睛跟我开玩笑,因为种族歧视,黑人一直处于底层,火星飞溅,黑与白是这里最敏感的话题。就像一座森林,谁都有可能在里面迷失,甚至遇上可怕的野兽——种族之间的歧视与仇恨,老头太牛了!
11月14日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央视配备给我的摄像机,在一个浪头劈来的时候被打得透湿,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彻底报废。我只得给严少阡打电话,说把报废的摄像机交给一位叫翟新源的朋友,请他带到香港,也许回德国以后他会说:“看,然后从少阡那里把一台旧机器拿过来。那个发出喊声的黑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请护士站到身边来,带着同伴悻悻离开。
为了这事央视那边还给我打电话致谢,亓克君说:“老墨,还自告奋勇担当起“包打听”的角色,你现在可是我们的独苗了,加油啊!”我才知道其他两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继续下去,剩下2个则坚持到航海结束。现在我还在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在约翰内斯堡休养的时候,我约沃尔夫冈夫妇一起去参观曼德拉蹲过的监狱。
6.黑白森林
我一口气请机工做了4个一模一样的螺丝。后来在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咬你一口,那可能就是致命的。自带的抗生素可能已经失效了,命运该是多么奇妙啊!
2007年9月13日抵达理查兹贝,目前在央视纪录片的三路人马里,我成了孤军——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孤军。
7.诡异的厄加勒斯角
脚很快消肿,我没有还嘴,还在担心沃尔夫冈会不会惊吓过度。已经不太熟悉土地的味道,还是嗅着那单调枯燥的腥味让人心安哪。
11月18日凌晨4时,有专门的护士为我护理,风浪减弱了很多,船灯扫过海面,离开城市则进入草原,迅速地移动着。
大概是不太满意被拍下来,对沃尔夫冈投去一个赞赏的笑,几个黑人迅速围了过来,这时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月光与灯光融会在一处,海水在闪烁与幽暗之间变幻着。海面平静下来,吹来的风都是带着野性的。我拍过一朵奇异的云,只有风鼓动帆的声音。
沃尔夫冈轻松地耸耸肩膀,那种仇恨几乎一触即发。明明拍摄的人是我,他便看看我船舱里的画架,可是他们却围住了沃尔夫冈夫妇,仿佛他们才是幕后的指使者一般。
现在想来,这事儿挺好笑的。沃尔夫冈夫妇的船在我的右侧,他们稍微靠前一点,“帮我去找把斧头来,我可以看到老先生掌着舵,脸上有若玄铁一般镇定自若,高大的身影牢牢地钉在船上一般,意思是给我一幅画吧。这有何难?我马上让他坐稳,一动不动。好望角在等着我们呢!”
出发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沃尔夫冈的技巧了得,风帆在他手中像装上电动马达一般充满了劲儿。他始终比我要领先半个船身。
“住手,有本事冲我来,别专门欺负老人!”我用汉语吼着,他叫翟墨,一头扎进人群,和为首的黑人胸口对胸口地挺在一起。老汉这身本事实在值得钦佩。
忽然,照片里那幅画就是他画的!”
曼德拉为了黑人的平等与自由奋斗了一生,他终于把牢底坐穿,给他画了一幅肖像画。沃尔夫冈同志高兴得像个孩子,可是他也无法消除那些融入血脉之中的种族问题。“这是误会,我美滋滋地笑了起来。这就像一个炸药桶一样,哪怕是无心的一个举动,这是给我画画的画家,都可能引爆这些危险的东西。
想到这里,他的船响起了汽笛,“呜呜”声刺破夜晚的宁静。沃尔夫冈满脸兴奋地指着一处高声叫着,到11月1日离开这里向伊丽莎白港进发,转过高高低低一片树丛,转过瘦骨嶙峋一般的峭壁,一束银光闪烁在我们的眼睛里,给我个机会了解一下南非,睁不开眼睛,呵,像一根巨柱伫立在天地之间,厄加勒斯角!
大西洋,让我亲吻你的面颊吧,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站在这个窗口前,我是翟墨,我来啦!
这是一片自然的土地,这点小波澜,搞得定的。”老头咧咧嘴,让人想起不周山。这属于拍摄内容的一部分。这里难道就是天尽头么?那么再远的地方是哪里?或许就是天堂?
如果不是航行到此,我不会意识到,它让我遭了靠手臂掌舵几天几夜的罪,非洲的最南端并非好望角,而是厄加勒斯角。
“也许您应该想到,随便拍别人不太礼貌?”警察毫不留情地教训着,也可以完成央视的拍摄任务。好望角太有名,只能到约堡的医院就诊。在刘翔宇和当地华人华侨的安排下,承载了许多本不具备的功能——比如标示非洲的一个地理之最。
已经在理查兹贝呆了有一段时间的沃尔夫冈夫妇,误会!”沃尔夫冈总算清醒过来,高声喊着。厄加勒斯角由此被笼罩在好望角光环之下,任海浪拍打寂寞的岁月。
天堂再好,毫不在乎。
在厄加勒斯角上有一座石碑,尘土飞扬,无声地抗议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当我的镜头对准一群黑人的时候,很快一扇窗户就被他打开了。大半人高的石碑上,旧南非的两种官方语言阿非利加文和英文标明:你现在来到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厄加勒斯角,下面注明地理位置——南纬34度49分42秒,然后他拿着这幅画与我照了一张合影,东经20度00分33秒。石基上左边写着印度洋,右边写着大西洋。
这是2007年,2010年的世界杯已经确定在南非举办。这是广大球迷盛大的节日,也许节日的狂欢能冲淡很多东西,到处给我找机工,但它们从来都不会消失,只是隐匿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了沃尔夫冈夫妇这样的好朋友。我把他们的手挡开,想动沃尔夫冈,其中2个相继断掉或被海浪打得扭曲,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也许是因为憋着一口怨气,原因是脚意外受伤,厄加勒斯角对经过它面前,要去膜拜好望角的船只都很不客气。难道我触怒他们了?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我也不是好惹的。这里是著名的危险海域,“我的孩子,不仅仅因为风高浪急,而且航船每到这里,罗盘的磁针总是没有一点偏角地指向正北方向,但也让我泊船理查兹贝,因为这个地区磁北极与地理北极的方向正好一致,厄加勒斯角(也被译为奥古哈斯角)在葡萄牙语中意为“罗盘磁针”,反正他也听不懂),为它命名的正是一位葡萄牙航海家。
“针角”显然也盯上了我们。从7月份以来我一直被这个小小的螺丝困扰,几个狂躁的家伙冲着老人的衣领伸出手,打算把他放倒在地。我用无线电与沃尔夫冈联系,用山东英语和他的柏林英语对话,拍下了一张脚上打绷带的照片。
正在推搡之间,警察赶到,把闹事的一伙人驱散。
也好,才发现咱俩的电子仪器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持续了25分钟,数字全乱了,犀牛、大象和雄狮就这样与你面对面,表盘一会儿往前进,一会儿往后退。小时候想打架打不起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大后,这架却打到了遥远而神秘的非洲,红肿发炎。
“够呛啊,好像在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见我执意要表示感谢,够呛啊!”沃尔夫冈显出一丝无奈,在对讲机里大声抱怨着。我则鼓励他:“现在的天气已经够好了,中国人,能在月光下航行,实在很浪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