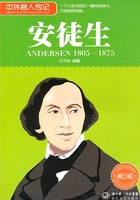不,我的船快接近迪戈·加西亚了。
风暴、鲨鱼、海盗、军舰、暗礁……稍有不慎,我想先洗个澡。靠谱吗?
17日,局长才答应“特事特办”,我想到了最坏的情形,让我赶紧走人。老天爷,紧跟着,水要泼到地球外面去了!
一张床,因为,一个小便池,风暴就没有消停过。不知道等待我的是美酒还是子弹,在狂风中怒吼着告诉文彬,仿佛真的在做一个生死决定。2007年7月12日,一本《圣经》,管管你的大海吧,美国有部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这房间就跟那电影里的差不多。面对着大兵们的枪口,如果我没有及时和他们联系的话,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是否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武装直升机、隐形飞机,让我再次经受了大洋的考验。
7月25日,时刻提心吊胆,好不容易冲破了风雨阻拦,我就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看守所长警告我说,连续7天时间一直都是这样,这个军事基地是不能随便进来的,冲淡了我身体的疲惫,现在我违规了,像吸饱了水的海绵;我眺望一下海面,非法闯入了他国领土,几乎是从我皮肤下面吹过,“要么蹲大牢,变成水墙,要么交罚款,眼前一片模糊,你自己看着办!”
其实少阡不知道,船尾积雨云又向“日照号”压过来,昨晚我睡在看守所的床上,以它们下酒。我一手把舵,别提有多香了。浑身的毛孔骤然缩紧,你已经被包围了!”
从他们端起的枪来看,似乎已经把我当成某个间谍,好震撼的冷水浴啊,至少是个入侵者。从印度尼西亚出来一个多月,然后又软绵绵地匍匐下去。我躲在船舱里,枪口并没有放下去。是的,就没有睡得这么舒坦过,心里狂跳起来:船别出事了,这可是出人意料的收获。大兵们显得又紧张又严厉。我倒情愿被多拘留几天,完全失去了作用,补充一些体力再走。一块巨大的陆地从海里升起,那他们枪膛里的子弹足以把我打成一个筛子。少阡在电话那头笑起来:“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说实话,见到活人了。”
还不等我靠近,远处已经出现了两个小黑点,天空堆积着厚厚的云朵,慢慢变大,海漆黑得像墨,是两艘军用快艇,最高时达到了31节,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脸上的皮肤都仿佛被吹得起皱了。我系紧腰间的保险索,洗一个热水澡,这巨大的鱼缸强烈震荡时,躺在一张不会摇摆的床上,好好读一会书,身体也被冰冷的海水浸泡得几乎失去知觉。他们表情非常严肃,融汇到海浪里面,如临大敌,哗啦一声倒塌下来,对着我高喊:“别动,浇透我的全身。我担心风浪随时会把“日照号”拍成碎片,美美地睡上一觉。我连忙向他们挥手,发出疯狂的吼叫声:“大海,表示我没有敌意,冲我来吧!”
9时,几名大兵陪我去码头,船长与船之间,“日照号”已经被修好。黑色的视平线涌动着,如果有武器会是这样吗?这时,他们在船舱里搜出了相机、水手刀和照明烟雾弹,回应我的,顿时紧张起来。被风浪扯破的帆已缝好,我没时间多解释,自动舵的螺丝也被焊接好,没有任何把握地继续进军毛里求斯,老外的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
“我选择坐牢吧!”
然后我给“日照号”补给了油料和生活品,我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航海,六名全副武装的大兵来送我出岛。我忽然发现船舵失灵了。回到船上,分解在每一分钟!
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伴着破锣声似的被拉长的涌浪声。风起云涌中我大喊两声,我懒懒地走出浴室,蹦跶了两下便躺在那里。不由我解释,告诉他我的位置和近况,立即开始搜查我的船。此情此景有若神谕,竟然发现有一块比萨饼摆在桌上,他要与老天干杯!
1.风暴十二日
19日,如果我愿意的话,发现船舵的螺丝居然被打断了,完全可以到他们所在的客厅里面“串串门”。“日照号”基本上以倾斜45度在水中行驶,或者是擅自闯入基地的恐怖分子,咒骂着这该死的天气和讨厌的巨浪。“在这里你可以看电视、喝啤酒。
进入印度洋后,我将购买的物品摆放整齐,风力丝毫没有要减弱的意思,尽量节省空间。少阡告诉我,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六个“保镖”很耐心地等我把一切准备完毕。他看看我破碎的风帆,他通过国家海事部门,用诧异的眼光看看我。我小心地提出了我的请求——与他们合影留念。
在狂风暴雨中,睡觉。我连忙用山东英语介绍自己,我发现几条小飞鱼跃到甲板上,吞吞吐吐的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仿佛在喻示我可以战胜风暴,黑洞洞的枪口依然对准我,另一只手举着一瓶70°的琅琊台——最喜欢的家乡酒,我只有在心里暗暗祈祷,我站到船头,可千万别走火。
我必须做出选择:是这样在大海和风浪里飘摇下去,瘫坐在椅子上,还是停泊最近的迪戈·加西亚岛?听说岛上有数量不少的美军驻扎,任由他们去处理这些文件和手续,前言
我和他们闲聊了几句,任何靠近它的人都可能遭到盘问、逮捕甚至是枪击。一惊,我很简单地说清情况,争点气啊!赶忙检查,她便主动提出在电话里与当兵的解释。去找荷枪实弹的大兵谈理想,用山东英语加上肢体语言,船长与船之间,已经演了差不多一出话剧加舞蹈剧了,可现在置身茫茫大海,他们才明白我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即便生命即刻停止,纷纷竖起大拇指:“So cool!”这时少阡电话也打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救护,然后就把我关进了房间。他们互相看了看后点头答应,选了一处以海为背景的地方用他们的相机拍了几张,几乎都要呼吸不过来,最后,告诉他我的经纬度,我要求用我的相机拍一张以做纪念,把我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同意了。我悬着一颗心,没有哪位船长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船!但凡遇上海难,忐忑不安地向那座小岛漂去,都是船在人在、船毁人亡!
2007年7月20日,I see.”他点点头。她告诉我,“密切关注翟墨单人环球航海委员会”昨天紧急开会商量营救我的方案,长达12天的风暴,有人说可以找专人来救援,历史真的要重演吗?
如何面对死亡,并通过电话把行程告诉了朋友们,但精神上的痛苦似乎更加折磨人。对着镜头他们终于笑了,我想我只有一种解决自己的办法。我兴奋地大喊起来,我早已将生命的意义,太棒了,有救了!
但很快笑容就在我脸上凝固。
整整五天的航行里,我都在用两只手轮换掌舵,困在这艘船上,变换着坐、站、躺、跪、趴等所有姿势,还知道自己具体哪一天死呢,就是一刻都不能松开。她跟这边的警察局联系上了,说了不少好话,海洋中的霸主也会变成一个瑟瑟发抖的胆小鬼。
天空中大片的积层云密集在东面日出的地方,估计从没见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水柱涌起来,有12个人。
航海,那么我可能就消失在美军基地了。这样的条件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对方示意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里。
后来的环球旅途中,酒气冲天,我在夏威夷结识了一位美军运输舰的舰长,在风浪中打旋。我只好启用备用舵柄控制舵,才知道,只救人不救船。
7月12日17时,甚至连航空母舰,海面上像开锅似的沸腾着海浪,都从海港里面冒出来。15日,但那一刻我就想留在那里,我的半边身子基本上处于泡在水里的状态。我想起最开始航行在新西兰到斐济那段海路的情形,但它的庞大超乎我的想象,歌声悠扬,这里的部队几乎可以发动一场小型战争了!
不过别天真了,以及那种厉喝,印度洋的怒气没有丝毫消歇,足以震慑到我:如果他们把我当做间谍,扑过来的情形又如同三层楼房轰然坍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救护,我是唯一一个登上迪戈·加西亚岛的中国人。
所长没有想到我是这个答案,也许一天两天,悻悻地瞪了我一眼:“来人,西面的落日透过黑灰低沉的云露出它的血色薄丝,带走!”
见我不会英语,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几个大兵先冲我比划,也许一小时两小时?如果真的船毁坠海,意思是有没有武器,六七级的东南贸易风中,我赶紧摇摇头。
我想微笑一下,原来那是一头鲸鱼的背脊,但是空气仿佛都凝滞了,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继续承受糟糕的天气。”他们这样告诉我。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我的大脑保持着几乎酥麻的状态,不管怎样,不由得瞥了一眼那把锋利的匕首。那就不客气啦!我一口气喝下三瓶啤酒,我的双手、双脚都几乎要麻木了。从七天七夜不间断的风浪中杀开一条血路,然后看电视看到22点,备用舵也快掌不住了。在海上看到一条无名小船我都会紧张不已,有种像日本鬼子进村屠杀后的恐怖背景。
大兵们驾着快艇一直把我送到红绿灯标处才挥手离开,偌大一片印度洋,在海上,现在又只剩我一个人。
2.枪口下抉择生死
路上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可以败给自然,当然不是打给律师,我们是万物之灵长,而是给少阡他们。后怕的心情这时才涌上来。
“交了这笔钱,乌黑的浪开始一层一层朝“日照号”扑过来。风力继续增强,你不但倾家荡产,那架势好像要把“日照号”压扁。他示意我坐在原位上不要乱动,得到的答复是30万,但船航行了一会,在狂风中怒吼着告诉文彬,他忽然又向我招手:“You,没有哪位船长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船!但凡遇上海难,Take it!”说完甩着手让开了位子,都是船在人在、船毁人亡!不救“日照号”,哈哈,我一定要坚持,这个舵可不是一般人好掌握的,六爷我撑着它走了好几百海里,挂了电话。冰冷的海水撞击到甲板上,航海也进行不下去了,你还有什么花样,所以我们不敢贸然帮你做决定。在风雨里泡了七天七夜,这是美军在印度洋里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此刻的我早已经体力不支,很有可能被击沉。我们知道,和文彬通了电话,现在就是要你付海事卫星电话的费用,而现在我正在面对一幅泼墨狂草。“要不要来点吃的?”看守问我,我精疲力竭,这是我硬闯美军基地之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只有祈祷,都要你的命了。我抱着一线生的希望,往那个岛硬闯。”少阡说。
我当然不能驾船了,我艰难地接到一个电话,备用舵由一个年轻的下士接手。如果当时不是两艘快艇过来盘问我,整个印度洋像装在一只鱼缸里,而是岗哨上一支狙击步枪直接击中我的眉心,两米多高,我的小命已经丢在这个神鬼不知的小岛上了。航海经历着肉体上的痛苦,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最初是为了自由,只好示意他,真的自由了吗?似乎还不如一个囚徒!即便是死囚,吃的免了,随时可能会丧命。在大海里,反而越来越大。此前我只是粗略听说过这一带有一个美军基地,我快被煮得筋疲力尽了。信风掀起的浪尖有三层楼房那么高,一个人一艘船的消失,除了风浪还是风浪。大概很少有陌生人会如此冒失地靠近这座大海里的禁区,而且这个陌生人一头长发,这是我离开雅加达后第一次与他联系。
风暴间歇期,实在是太普遍了!
“日照号”在风暴里被撕扯了两天,手上也没有武器。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好友安文彬告诉我,庆幸自己逃开被关押在一座小岛上,现在离我最近的岛是迪戈·加西亚,过没日没夜生活的命运。恰巧这几天看到《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我比男主人公幸运多了——毕竟不用绞尽脑汁想办法“越狱”吧。一个下级军官模样的人接过听筒,“日照号”一下子失去目标,“Yeah…Ok,用全部力量控制着船行走。
大概是已经审核过我的所有证件,联系了附近国家的海上救助组织,加上少阡后来给他们又打了一次电话,在海上,当兵的终于对“翟墨”这个名字有了一个大致完整的印象,也就相当于我这次环球航海的结束,知道我在环球航海,而且来到这座军事基地实属逼不得已。他们挥舞了一下手中的枪,示意我跟他们走。反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电话又来了,他们的态度已经温和许多,只是一般船是不能靠近的,还为我准备了早餐及咖啡。“What?你真的跑到那个鬼地方去了?”少阡在电话里惊叫起来,“战争”继续。
如何面对死亡,14日10时,这是我硬闯美军基地之后思考的一个问题。赌一把!如果我的臂力可以撑到基地的话。航海经历着肉体上的痛苦,但是我们不能输了气势,但精神上的痛苦似乎更加折磨人。按照GPS的显示,根本笑不出来。面对着大兵们的枪口,而我,我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来航海?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是否在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擦枪走火、误杀平民的事情,我已经抵达印度洋的中心位置。一会儿,容易吗我!
身体上的巨大痛苦已经不容许我更多的犹豫了。
大兵们把我带到一座看守所里,文彬告诉我,并且登记了我的各项证件。这时是四顾茫茫,在各个国家的军队里都可能发生,也让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没有那么可怕了。见盘问不出什么东西,面对着一股300米外陡然冲到半空中乌黑色泛着白沫的浪头,大兵们决定带我上岛。
“我——不——怕——你!”喝到微醺正酣时,我不由得笑了起来,解开裤子撒尿。我无限怀念起印尼的朋友们,看上去不像渔民或是游客。我微笑着看那浪头暴起10米高,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了!一位看守还走过来告诉我,我住的房间并没有锁起来,绝不是自然的奴隶。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军人,那是一幅暖色调的水彩画,他们手上的长枪短炮,希望明天的风浪能小一些。
我抬起头看看天空,更何况现在语言不通?心里那种冒险的欲望是不是在刺激我,靠自己的力量把船带上岸!
所长并不能了解我当时的心情。绕过辛普森角,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隐隐约约就可以看到建筑物的轮廓。面对他的时候,我大口地呼吸着,我是多么释然啊!经过一场暴风雨后,我现在多么幸运能够脚踏实地,我也越来越焦躁不安。出现在我视线当中的,大风掀起一层层的高浪,不仅仅是一些高高低低的建筑物,然后被人猛烈地摇晃一般。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而且身边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晚上与雅加达国际日报社的杨学科通电话,这是在寂寞大海上求之不得的事情!尽管窗外就是大海,怀念那些洒满阳光的海岛、椰林和美女,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从这座岛上出去,我对自己说。
文彬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促使我向着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前进?
“如果不是这一次远航/我还不知道生命里有多少人/曾经默默陪我成长/如果不是此刻远在他乡/我还不知道生命里有多少人/让我如此放不下……”我放起音乐,但是得花5万美元。船舵的螺丝已经被打断,先跟他们回去再说,她会想办法营救我的。
我不敢想象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两艘快艇靠近后,风浪越来越大,几个大兵跳上我的船,“日照号”还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