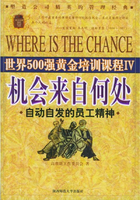在出海的时候,我曾经询问过航海的前辈们:一旦遭遇强烈的风暴,我要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告诉我,在大海里,船就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离开船,那么必死无疑。他们举起手中的安全索亮在我眼前,这些粗糙的绳索包裹着一根柔韧的钢丝,把它系在身上,那么即便死神裹挟着狂风巨浪而来,也无法带走我的命。
此刻,这根绳索就维系着我和船,它忍受着我的双手紧紧的抓握、摩擦、回勒,它一点点松弛下去,我则一点点向那艘8米长的帆船靠近。我听见自己在狂叫,捡回一条命的幸福感盘踞在我的身躯里面,陡然让我酥软到失去力气,却又让我精神到雄心百倍。
赶快离开巨浪,攀上船舷,回到那短暂的安全中去吧。我当时只有这一个念头。
8.疼痛与曙光
我被巨浪抛到水中,然后借着缆绳的力量回到船上以后,“排涝”成了首要任务。船上任何可以用来舀水的工具都用上了,桶、瓢,乃至一个碗。我拼命舀船舱里的水,忙乱中碗被打碎了,我的脚被碎片划开了一个很长的口子,殷红的鲜血涌出来,很快就与海水融为一色。钻心的疼痛从脚底板传来。什么是“切肤之痛”,在这种鬼天气下感觉尤其明显。
风暴中,驾船成了最困难的事情。船身打着旋,桅杆惊恐地左右摇晃。我浑身湿透,还拖着一只伤脚在奋战,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一支被抛弃的守军,城外是漫山遍野的敌军,而“我军”已经饥寒交迫、伤亡过半。
幸亏风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知什么时候,进攻减弱了。乌云依然浓密,但暴雨已经没有那么猛烈,海面也稍微平静了一些。终于有那么几分钟可以瘫在甲板上,刚才紧绷的肌肉已经溃不成军,这时疼痛再次从脚底传上来。
刻不容缓!我赶紧摸出随船携带的急救包,在颠簸中好不容易穿针引线,然后将针头消毒。轮到出发时带上的麻醉药上场了,看着注射器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真的要做一个“外科大夫”了吗?我不禁好笑起来,也许我这辈子做的唯一一次外科手术,就是给我自己缝合脚底的伤口,不会有人抱怨手艺太差,也不会有医患纠纷——这个念头让我放松了许多,然后想也不想,一针扎下去。
缝针的过程极其艰难,不亚于穿越一场慓悍的暴风雨,或者完成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有机会我应该在画布上把那种心情画出来,那也许就是大量狂躁色彩的堆积,锐利的红色、刺眼的白色、焦躁的橙黄、阴郁的藏青,以及苦闷的灰黑。船身依然随着海浪在摇晃,即便是我自己的脚掌,现在也不受控制。
我用两个指头摁住一块皮肉,看着针尖挑入皮肤,红色在眼前漫延开,麻药发挥了作用,没有疼痛,只有惊心动魄的视觉。我似乎可以感觉到丝线在皮下游走,我想起《三国演义》里关公刮骨疗伤的情形,“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就在耳畔,反复勒着我的听觉。风浪已经感觉不到了,但手和脚史无前例的拧巴。
那一刻,我对待自己的脚就像对待仇人的面孔,毫不犹豫地下狠手,针线来回穿梭,撕开的皮肤一点点合拢。最后数数,我大约缝了三四针。时间忘记了,危险忘记了,我的脚掌在我面前招摇,被海水泡得发白、发软的皮肤上是歪歪扭扭的线缝,让受过专业审美教育的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审丑”。
在剪断线头的那一刻,我彻底失去力气,巨大的成就感充溢了我的胸膛。我张嘴大笑起来,哈哈的笑声在狭小的船舱里回荡。我多么渴望有人能分享这种笑声。那就像一个年轻人获得自己的第一份报酬,就像女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就像第一次把宿敌击败。这次风暴也许会给我留下一个丑陋的伤疤,却也授予我一枚荣誉勋章。当未来我和海上同行人擦肩而过时,我会亮出我的脚掌,与他们分享这场南太平洋上的“战争”。
这时,嚣张的疼痛又从我嘴边传来,原来不经意间,我把嘴唇咬破了。
三天三夜,就像三年、三十年,快要崩溃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睛窝子里打转,我觉得自己被文明世界抛弃了,被我的同类放逐到这无根的地狱来。别说前途了,就是明天我是否还能睁开眼睛,答案也隐藏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里。我啃着仅有的干粮,强迫自己想一些积极的事情。
我无限怀念起陆地,怀念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古希腊神话中有个身躯魁梧的神灵叫做安泰,他是大地之子,是海神波塞冬与大地女神的结晶。他从未离开过陆地,每一次和对手搏斗的时候,就算被打倒在地,他也会立刻从大地汲取能量,瞬间恢复。他唯一一次离开大地是在和宇宙之子的较量中。宇宙之子将他的双脚举起,于是安泰失去了所有的能量,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人类都是大地之子,是陆上的王者,我应该回到大地上去。
我沮丧起来,暗暗在心里发下誓愿:如果大海让我活下来,我会找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一处人间仙境,娶一个当地女人,开一间中国餐馆,哥可以很淡定,这辈子都不再航海!
大海并没有让我带着湿漉漉的命运返回大陆的意思。当某一个黎明,海平线上出现第一道曙光时,我欢呼起来——“穿过风暴啦!”
那种景致盖过一切壮丽的绘画,比任何雄浑的交响乐还要宏大,没有诗句能够赞美死而后生,最伟大最丰富的思想在大自然面前也显得异常贫瘠。中国有句老话,不知生焉知死,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不知死,焉知生?
9.从中国出发
这段航行整整经历28天。28天之后,我终于又和大海回到了蜜月期,海豚成群地在我的帆船两侧游弋,远处,不知什么名字的大鱼跃出水面,或者贴着海面“飞行”。然后看到了海鸟,看到地平线……
我要向海神说一声抱歉,恐怕我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并非我不讲诚信,哈哈,而是我开始真正爱上了大海。爱她温柔的身躯,爱她忧伤的表情,爱她的愤怒与狂暴,爱她的无力与落寞。我无法抗拒那无边无际的辽阔带来的奔驰愉悦,反正我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游走过一回了,那么再恐怖的画面也无法震撼我。恐惧在我的心里退潮后,勇气露出它刚硬的脊梁,足够支撑我的风帆高高扬起。
海的美是两极的,有风平浪静的,也有狂风巨浪的。作为航海的人,没遇到恶劣的天气,是感觉不到航海的魅力的。当遭遇风暴,面对死亡的威胁时,我的生存意识空前强烈起来。当一个几米高的大浪狠狠扑打过来,我掌控着帆船迎接这痛快一击时,虽然没有观众,只有一个人和辽阔的大海,但我觉得这时候我很“男人”。
这个地球表面超过七成是水,每一座大洋都是性格各异的女子,我还有那么多的风光没有见识,怎么能就此退却?在大洋洲的海岸线上,我远眺着海面,脑子里盘踞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出海计划。脚上的疼痛感正在消退,人就是这样一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动物,也正因为如此,勇气才会不断恢复,不打折扣,更多的风景才能呈现在眼前。
也许我不仅仅是个大地之子?晚上,我站在世界地图前,出神,发呆,我看到了一处海域,她依偎着我的祖国中国。我思绪万千,想起在山东的童年,想起第一次上船时见到那个挪威人的情景,想起第一次掌舵的兴奋与陌生。我用手触摸着地图,中国、亚洲、全球,我要环球航行!
孤独的航行必须自己发现乐趣。还记得在环新西兰航行时,告别安琪后,有一次我把船靠岸补给,遇到了一个当地华人。他吃惊地发现我居然是个中国人,因为我的船上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我说,同胞!”他跑过来跟我搭讪,“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来来去去的老外见多了,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驾着船来的啊!长脸,长脸!”我也很吃惊,没有回答他,却在心里暗暗说:“老兄,你在海边住了几十年,难道从没有想过弄一条船到海上玩玩吗?”
是啊,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呢?这位老兄的话让我回味良久。起初我是为了证明自己,但是在与挪威老船长暗暗斗气时,我忽然发现,作为中国人的荣誉感占据了我的心。人们都说,凡有人处必有华人,那么大海怎么能少了中国人的身影呢?
但这次出海没多久,“中国人”就经受了巨大的考验。深海地震外加11级的风暴发生了,海神把我的船捏在手上把玩,却没能征服驾船人的灵魂。他悻悻地放过了我,让我带着脚伤停靠到岸边。不过我没能到达大溪地,更惨痛的是,我花了全部家当买回来的8米帆,H-28老伙计,帮我扛过这一遭风浪之后,也彻底报废了。
不过我的冒险之路没有就此完结,我反而很高兴,作为中国人,我经受住了大海的考验。我要踏上回国之路,我要在中国再次出发,完成一个中国人环球航行的梦想。
第二天一大早,我开始准备出发事宜。经过海边的时候,海风轻拂,海浪问候早安。我冲着海平线举起了双手,在空无人烟的沙滩上高声呼喊——
“我——是——翟——墨!大海,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