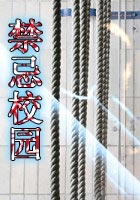解救最美的灵魂
当我落笔写下旧时光中的这段人生,会油然生出感慨:不管日后如何,当年的萧军,实在是一个伟男子。
几十年后,他们的生死之恋已散作遥远的传说,暮年的他会坐在傍晚的余晖里,抽丝剥茧地回忆这场悲欢离合,深情又不动声色地说:“我挽救和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女作家。”
的确,如果没有萧军,世上便没有萧红,没有《生死场》,亦没有《呼兰河传》。
如果没有三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只有一个被扣留在东兴顺旅馆的东北女人张乃莹。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呼兰小城跳大神的鼓声,充满肃穆神秘的气息。彼时她虽年少,落在她耳边却尽是凄怆之音。这不肯散去的哀凄像夜晚的寒风,一路潜游过来,成为她生命的基调,悲凉,和宿命的凄艳。
因此我遥望她短暂的一生,不得不对萧军心生钦敬,他在黑地里点燃了火把,照亮了她的梦想,使她悲凉的人生似一朵火烧云,绚丽地飘过了彼时的天空。
佛说,无明缘行、行缘识,十二因缘,流转生灭。是前世多少次的回眸多少回的擦肩,才换来这一生的乱世情缘。
他比张乃莹年长四岁。1907年7月3日,他出生在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凌海市大碾乡,满族人氏,原名刘鸿霖,又名刘蔚天,成年后取笔名酡颜三郎、田军、刘均等,后以萧军名世。
这位桀骜不驯的满族青年,论身世比张乃莹还要凄苦。他有一个蛮横暴躁的父亲。当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母亲不堪父亲的毒打凌辱,吞鸦片自杀,自此他在失去母爱的贫困乡村,踉踉跄跄地长大。辽西地界,野蛮尚武,他小小年纪便练习武术,梦想行走江湖行侠仗义。十八岁,他在吉林当了骑兵,后考入张学良所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法律与军事。1929年,他以笔名酡颜三郎在《盛京时报》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懦……》,开始走上创作之路。
认识张乃莹之前,他在乡下已结婚成家。然而,在生死都显潦草的年代,人如浮萍聚散,遑论婚姻离合?1932年初,他在时局动荡中来到哈尔滨,秘密宣传抗日,成为革命文艺战线中的一员。这年春天,身处危境的三郎将妻子送回家乡,随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前路茫茫,也不知何日方能回家团聚,让她另行改嫁他人。
彼时,他像一个切断了退路的勇士,带着唯一陪伴在身边的一枝手枪,投奔了《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协助他编写儿童特刊,并用“三郎”的笔名发表革命作品。
似乎,他来到这个世界,除了做一名革命勇士,还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去营救一个才华出众的女人,并使她成为萧红,给这苦难人世增添一道光芒。
斯年彼时,他也落魄。在哈尔滨,他其实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人。因此,1932年夏天在道外区一家小饭馆,当裴馨园与报社同仁说起张乃莹的遭遇时,他表现得并不积极,在《烛心》中他回忆说:“我听到这些,只是漠然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而已。”就连他敲开旅馆的门,走进她困居的小房间,寥寥数语完成裴馨园交办的任务时,对张乃莹而言,他依然只是一个难以亲近的陌生人。
但他是好不容易才漂流到身边的一根浮木,茫茫苦海,她快要窒息了,直觉也许告诉了她,他是上苍派来救她的,不管有多难,这个刚烈侠义名叫三郎的人,会带着她离开。
于是当他起身准备离开,她丢开矜持,情急中恳求着说:“我们谈一谈……好吗?”
他于是留下来,继而,发现了她的画、她的字、她的诗,于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在他心上眼底盛开,他为自己的发现狂喜难禁,他对自己发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挽救这个苦难中最美丽的灵魂。
尽管彼时她是个孕妇,身形臃肿毫无美感可言,他却难能可贵地爱上了她的灵魂和才情。他在《烛心》中写:“那时我却只觉到这世界上只有你是美丽!——这样的话也写给过我曾爱过的一位少女——不知什么缘故,我只是要俯向你的怀中去哭!哭!哭个尽够!”
他们在苦难中遇合了,相爱了。
尽管饥饿,尽管旅馆老板隔三差五就来逼债,但困境中的张乃莹却被恋爱的幸福填满了。见到三郎的那一夜,她失眠了。饿,已经不重要,想起他的微笑,“便比吃什么全饱了。”她变得多情和从未有过的温柔,她开始写诗,写一首又一首的《春曲》:
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是那么美丽,水一般地,花一般地,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但又怕别人摧残,那我何妨爱他。
——(萧红《春曲》之二)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其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萧红《春曲》之四)
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他说:爱惯就好了。
啊!可珍贵的初恋之心。
——(萧红《春曲》之六)
恋爱中的心,是冬天的炉火么?可以抵挡凄风苦雨,也可以越过冰川,飞临三月阳春。
七月,一场持续二十多天的大暴雨袭击了哈尔滨,八月八日夜,松花江全线溃堤决口,洪水冲进市区,道外十几条街瞬间成了河流。从睡梦中惊醒的市民,尖叫着向南岗的高地逃生。
东兴顺旅馆的一楼已完全浸泡在洪水中,而在二楼,就困居着即将临产的张乃莹。她坐在窗台上,伸出手去,便摸到了窗沿下的洪水。她赤着脚,在房内来回走动。此刻,她像置身无处可逃的孤岛,四面都是大水汪洋,倾耳都是奔忙呼救声。这个悲凉的夜晚,似末日来临。
她坚信三郎会来救她。此时在裴馨园家中,三郎正与同事们商议营救方案。他心急如焚,水大势急,已容不得半点拖延。他请求说,自己会凫水,没有船不要紧,他凫水去救她。
东兴顺旅馆一片狼藉,老板忙着转移家产,房客纷纷找船逃难,看守张乃莹的茶房再也顾不得那欠下的六百元房费,也慌不择路地坐船逃命去了。眼看一只又一只船载着房客离开,张乃莹却守着洪水漫涨的窗台,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三郎,等着他像个骑士般赶来救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洪水一寸一寸漫涨,她站在二楼的窗前,仿佛时光过去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她不知道,此时的三郎正在洪水中,拼尽全力向着她的方向游来。
那一刻的情景,不需要虚构,不需要道具,多像一部现实版的爱情史诗巨片。偌大一个生死交关的灾难场面,浩劫中的街市,张皇失措的人群,纷纷扰扰的苦难人世,在他眼前都化作一片虚浮的布景,他眼前只有通向旅馆的白茫茫水街,脑海只有张乃莹孤寂无助的面容,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他要游到她的身边带着她离开。
好不容易游到了旅馆,二楼十八号房间却空无一人!他发疯般的呼喊着她的名字,四处找寻她的身影,却一无所获。
他在失望焦急中赶到裴馨园家,却欣喜地发现张乃莹正在那里等他!原来她等了好久不见三郎,旅馆已不能久待,恰巧一只柴船从窗前经过,她便随船离开了东兴顺旅馆,又按照三郎给她留下的裴家地址,一路找到了这里。
张乃莹命运的逆转,裴馨园是她第一要感谢的人。是他怀着正义同情之心,对张乃莹的求救信给予重视,并最终促成了她与萧军的一段恋情,现在,又接纳了这一对穷困潦倒的爱侣在家中居住。
然而,生活与理想相比,总要粗糙许多烦琐许多。张乃莹已接近临产,一个大腹便便的年青妇人,与一个关系尚不明朗的男人同住裴家,裴馨园能理解,可是裴太太和裴岳母却难以接受,冷漠和白眼,使这对情侣不安,于是他们便像游魂一般,晚上住在裴家,一大早便出门在街头闲逛。后来萧红在《弃儿》中回忆说:“就像两条刚被主人收留的野狗一样,只是吃饭和睡觉才回到主人家里,其余尽是在街头跑着,蹲着。”
可是,分娩的日子到了。张乃莹腹痛如绞,脸如白纸,耳边却是裴岳母厌恶的白眼和啰嗦。她流着汗,也流着泪,将肚子顶在炕上,想用力将腹中的小东西挤出来。屋外,正下着瓢泼大雨,三郎一头冲进雨帘,他要去借钱,他要将乃莹送去医院!
他终于雇到了一辆马车,在天已黑透时,将乃莹送到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敲开了医院大门,却要预交十五元住院费,无奈,一贫如洗的三郎只得将张乃莹又拉回了裴家。
没有钱,住不了院,张乃莹随时便有生命危险。这世道,是富人的温床,是穷人的地狱。可就算天塌下来,他也甘愿为他爱着的女人顶起来。
第二天,他不等医院开具住院手续,便径直将乃莹送进医院的三等产妇室,叮嘱她任谁撵也不走,随后外出继续筹钱。
他用穷人的生存智慧,总算让张乃莹住进了医院,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婴。
整整六天,她没有看孩子一眼,没有给孩子喂一口奶!许多人只觉得她狠心,却不懂她彼时的痛和无奈。尽管她后来所有文字中,对汪恩甲没有半句指责,但改变不了他给她带来的磨难和打击。尽管孩子无辜,她却无法向艰难的生活,要得更多。因此,她克制自己的情感,以女性少有的冷静和坚毅,将这新生儿送了人。
《弃儿》,是她对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请抱去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她把头用被蒙起,她再不能抑止,这是什么眼泪呢?在被里横流。”
她一直忘不了这个女婴。多年后在香港,她在病床前还叮嘱端木蕻良,让他将来去哈尔滨时,一定要去寻找那个孩子。
产后的张乃莹心情抑郁,身体虚弱,加上总是心酸流泪,紧接着便大病一场。三郎已山穷水尽身无分文,医院拒绝为张乃莹用药治疗。三郎站在她的病床边。别的产妇都在逗弄自己的新生宝贝,只有他心爱的女人,落寞孱弱地瑟缩在单薄的被子里,用哀伤惭愧又羞涩的目光看着他,两只大眼睛里蓄满泪水,似乎只要有阵风,泪水就会滴落下来,流成一条细细的小河。三郎知道,她的身心,正受着痛楚的煎熬。
病房内的护工告诉他,昨天他离开后,张乃莹便一个人靠窗坐着,坐了好久好久,今天早晨,病就重了。
“亲爱的,我是不是要死了?”她无力地问。大夫一直没给她用药。
他被眼前这一幕刺伤了。他心疼,痛苦,继而愤怒。他闯进医院值班室。两个值班医生正在下棋,他一扬手掀翻了棋盘,怒不可遏地说:“如果今天你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从此死去……我会杀了你,杀了你们的院长,你们院长全家,杀了你们医院所有的人……我等着你马上去医!”
他回到病房,已疲惫至极,不多一会便昏睡过去了。等他醒来,张乃莹正安静温柔地看着他微笑。在他睡去的这段时间里,医生慑于他的威力,已给张乃莹治过病。此刻她对三郎轻声说:“亲爱的,你胜利了。”
他的泪水,瞬间涌了出来。这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男人,哭了。
欧罗巴旅馆和商市街
我时常会想,如果没有萧军,彼时的萧红会怎么办?裴馨园出于人道的帮助,终究解决不了太多问题。她是一个奇异的生命体,一生虽短,磨难却如影随形。受骗、扣留、贫穷、分娩、疾病,一个孤独的弱女子,在动荡黑暗的东北“满洲国”,似乎除了堕入风尘便是坐以待毙。
只有刚毅孔武的萧军,才能在她滑落深渊前拉住她,分担她深重的苦难。
他们都是落魄无依的流浪儿,在生活底层,饱尝了艰辛。他们彼此唯一的财富,是知识文化,和对未来不曾懈怠过的美好憧憬。他们遇见,是两朵雨云的邂逅,在电闪雷鸣的天空,倾心交会。
三郎,满足了她最初对爱情的所有想象。年少时,她曾对继母的妹妹梁静芝说,嫁人不能只看钱,要找就找有文化的穷人。这也成了她自己的标准。三郎虽穷困潦倒,却有文化有思想,充满侠义情怀和刚毅品质,在她面目全非青春蒙尘时,认清了她的美好,从而狂热又深沉地爱她,不惜一切做她的支撑。
这是多么珍贵的情感。不论这爱今后是否会褪色,不论他们能相携着走多远爱多久,也不论往后有多少对与错,刻骨铭心的今朝,永远是一部动人的传奇。
这对苦难中的情侣,生活已至举步维艰。为了生存,他必须用穷人和武人的生存法则,冲开一道道铜墙铁壁。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出院后,裴家的气氛显然已不适于他们居住。灾后的哈尔滨,萧条冷寂,因旅馆客房的生意大不如前,三郎才得以带着虚弱的乃莹,住进了白俄人开的欧罗巴旅馆。
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地不属于我似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
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
“你哭了吗?”
——(萧红《欧罗巴旅馆》)
欧罗巴旅馆的小室,是如此白净,白床单,白墙壁,白桌布,她软软地靠在床上,像是住进了白色的幔帐中。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走进来,得知他们连五角钱一天的铺盖租金也交不起,便一股脑扯去了软枕、床单和桌布,仅仅几秒,眼前便是破草褥、破木桌和破藤椅,连喝水的杯子都得用脸盆来代替,那白净的小室瞬间成了幻觉。
原先包月三十元的房租,因水灾已涨到了每日两元,他们所有的家当却只有五元钱。彼时,因为乃莹的缘故,三郎与裴家闹得很不愉快,一气之下离开了《国际协报》,每月二十元稿酬的工作,也因此失去了。两个赤贫如洗的情侣,除了爱情,别无所有。
旅馆的管事勒令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得搬走,情急之中三郎从床下取出长剑,那管事才勉强作罢,当夜却招来了数名警察,差点将他们关进警察所。
三郎每日早出晚归,四处借钱,找食物,找工作。她蜷缩在旅馆的小房间里,饿着肚子等他。有时他空着手回来,有时带回一点馒头,时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好在三郎有讲武堂练武的功底,便贴了武术招生广告,偶尔会引来几个人咨询,一见他们寒酸至此,只当是江湖骗子,往往看一眼便匆匆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