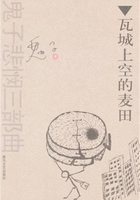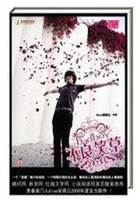年幼的荣华,天生敏锐善感,内心细腻却充满叛逆。除了祖父张维祯,这个家族里的几乎每一个人,甚至连她的亲生父母,都因重男轻女对她都有着冷淡的疏远。在她四岁时,祖母每次出门上街,都会敷衍她说要给她带回一只小皮球,却一次也没有兑现过,于是每一次,她撑起来的满满希望,最后都变成失望和落寞。这样的情形直到她六岁,终于在一个清朗的夏日,她戴上小草帽,独自出门,去买那个在祖母口中重复过无数次、却从未进过家门的小皮球。她跌跌撞撞一直向前走,直走到迷路找不到家时她也坚决不哭,所幸遇到一位善良的马车夫,辗转良久,才将她送回了家。
“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而父亲,对她的所谓“爱”,更是连母亲也不如。母亲姜玉兰是个薄命女子,荣华九岁那年,姜玉兰患病离世。临终前,她拉着女儿的手说:“荣华子,你哭了吗?别哭,好孩子,别怕,妈不会死的。”她泪水流了满脸,母亲对她最温柔的时刻,却在永别时分。
母亲去世仅隔三个月,张廷举就续弦迎娶了新人。
在萧红的回忆中,父亲始终是个对立的角色。她与父亲的隔膜,像严冬江河上的冰冻,冷硬地僵持在字里行间。在一张1947年萧红家人的合影中,照片中的张廷举一袭长衫,戴一副圆似车轮的眼镜,已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他两手相握垂于胸前,嘴角下拉,年轻时的固执严厉,在岁月的掩盖下仍清晰可见。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父亲开始暴烈地打她。每逢此时,她总是默默地躲到祖父身边,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寻到疼爱与慰藉。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飘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到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善良温厚的祖父,疼爱着这个时常落寞的小女孩,从荣华来到人世起,他就抱着她,背着她,拉着她,寸步不离地呵护着她。“祖父到鸡架那里去放鸡,我也跟在那里,祖父到鸭架那里去放鸭,我也跟在后边。”等她稍大一点,祖父又教她念《千家诗》,小女孩读得极兴奋,嗓门大得惊人,老人慈爱的吓唬她,“房盖都被你抬走了。”
荣华童年的乐园是家里的后园子,祖父常带着她,去后园拔草浇水。园子里,种着黄瓜、白菜、玉米、玫瑰和蓊郁挺拔的树。在萧红的文字中,园子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快乐宁静:“黄瓜愿意开个谎花就开个谎花,愿意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要长到天上去也没人管……”这片宁静的自然乐土,不仅是荣华的乐园,也常引得蝴蝶和昆虫来搭讪做客,似乎连天上的云,也显得格外白,格外纯净。
园子里的玫瑰,从五月能开到六月。祖父蹲在地头拔草,荣华悄悄将他的草帽插了几十朵玫瑰花,一边插一边笑,耳听得祖父自言自语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怕也闻得到。”直把小荣华笑得直哆嗦。
母亲去世那年,九岁的荣华在家门口的“龙王庙小学”入学读书,取学名张秀环,因与家中长辈同字,外祖父替她改名张乃莹。
她与众不同的悟性和才能日渐显露。她总是学校里出类拔萃的那一个,思维灵敏又深具才情,最为可贵的,是秉承了一份东北人的坚毅,以及关注民族命运的品格与志气。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她在县立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读高小二年级,那年她14岁,却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向当地最有权势的“八大家”募捐,又在话剧义演中饰演角色。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反侵略的社会活动,这热情此后伴随了她的一生。
小学毕业,张乃莹继续学业的愿望遭到父亲的蛮横反对,她困在家中,整整休学了一年。她以出家当修女相要挟,逼父亲让步,父女二人的关系也因此剑拔弩张。父亲在她眼中,“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情感的动物。”
是慈爱的祖父,替她争回了读书的权益。祖父始终站在孙女这一边,不求回报,甚至不问对错,心甘情愿做她的支持者。
彼时,她已16岁,这呼兰河的女儿,终于考取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而走出了呼兰。而今,这所学校已改名“萧红中学”。
她不再是童年那个落寞又淘气的小女孩,她愈发沉静,浓密的黑发,衬得脸庞白皙异常,一双明澈的大眼睛,像幽幽的一潭水,映照着她的聪敏、坚毅、孤独,与不驯。
哈女中是她人生重要的驿站,她在这里,较为系统地接触到了新文化。国文老师王荫芬是鲁迅的拥趸者,受其影响,张乃莹爱上了鲁迅作品;而美术老师高仰山,毕业于刘海粟时任校长的上海美专,在他的指导下,张乃莹的绘画才能日益显现。在哈女中,她爱读书,爱绘画,梦想将来当个女画家。与此同时,她又以悄吟为笔名,在校报上发表散文诗,那是她最早的文学作品。她的文艺潜能像呼兰河的水,像初夏的艳阳,不动声色地闪着光。
1930年,张乃莹中学毕业,她想去更远的地方读书,可是这一次,父亲不仅彻底斩断了她的梦,还逼迫她嫁人完婚。
而最疼爱她的祖父,也在后园的玫瑰花开了满树时,永远地离去了。
出走的日子
父亲逼迫她嫁的那个人,就是汪恩甲。
汪恩甲的出现,似乎是命运的刻意安排,他为讨还一笔情债,将她逼至危谷,最终引来萧军的英雄救美,才有了东北作家群的“二萧”传说,才有了文学史上这段生死悲情的倾城之恋。
因此从宿命论角度而言,他造了孽因,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成全。
张廷举虽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却是顽固的封建家长作派。早在张乃莹读高小时,他便在哈尔滨顾乡屯结了一门亲,将张乃莹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随时做好了嫁女的准备。眼看女儿渐渐长大,受新式教育影响日盛,张廷举怕夜长梦多生出变故,于是一再阻止她继续学业,催逼她早日完婚。终于耐着性子等到她读完中学,嫁女,便成了这个封建家长刻不容缓的大事。
彼时,汪恩甲,这个出生封建帮统之家、张乃莹的未婚夫,已从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执教于滨江县三育小学。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也算得相貌堂堂,最初,他给张乃莹的印象并不坏。他常来学校看她,她也常去汪家走动,甚至汪父去世,她还以准儿媳的身份专门去吊过孝。
然而,这相貌堂堂的青年,居然抽起了鸦片。以张乃莹的觉悟和性格,这样的陋习,她断然不可接受,于是屡劝不止失望再三,便渐渐生了厌恶之心。她看得见自己的未来,若不挣脱,她只有沉沦下去,谨小慎微活在这个封建旧家族的阴影中,做一个只会生儿育女的卑微女人。
恰此时,她的远房表哥、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与她在频繁相处中,产生了微妙的情感。她明白,只有到更远的地方继续求学,才能摆脱命运的设计,偏偏,“贪婪而失去人性”的父亲,却逼她中断学业,与汪恩甲完婚。
她和父亲之间,爆发了新一轮抗争。最疼她的祖父,已经离世,此时,再没有人可以站在她这一边,给她默默的支持。吵闹得激烈时,继母总是大开屋门,似乎要向邻居证明,张家的前房,出了这么一个叛逆不孝的女儿。
于是,她索性将这叛逆坚持到底。她假装同意完婚,借口去哈尔滨置办嫁衣,逃到了北平。她为求学而来,也奔着爱情而来。彼时与她志同道合的陆振舜,已在北平做她的接应。在陆振舜的帮助下,张乃莹成了师大女附中的高一女生。
他们背负伦理的谴责,期待冲开一个决口,去自由呼吸。遗憾的是,彼时陆振舜已有妻室。这向往理想和自由爱情的行为,成了一场殉道。残酷的现实,又将他们逼回到生活的原点。
陆振舜选择了妥协。张汪两家得知他们的下落,找到陆家要人,陆家在勒令陆振舜送回张乃莹无果后,怒火中烧,随即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天寒地冻,衣不蔽体,身无分文,忍饥挨饿,理想和自由,瞬间成了可笑的游戏。于是,放了寒假再也无处可去,他们只能踏上归程,各自回家。这短暂的出走,以理想开始,收梢时,却像一场闹剧。
呼兰县的张家,比她出走前更显冷酷而陌生。在她的年代,一个未出阁的年青女子,胆敢与男人私奔,虽不至于绑石沉潭,也是一朵恶之花,足以让家族蒙羞。因此,父亲怒她败坏门风,视她为离家叛祖的异类;四面邻里的嘲讽和白眼,如芒刺冷箭,让她无处躲藏。
她孤立无援,像一只受伤的刺猬,面对冷漠无情的围攻,蜷起小小的身躯,不屈不挠地抵挡对抗。于是,当她的亲舅听从继母的申诉,特意赶到呼兰来教训她,她立马拿起一把菜刀,红着眼睛与舅舅对峙。彼时,她想告诉世界,她宁可大逆不道,也绝不轻易妥协,为了自由生活,连死亡,她也不惧。
呼兰的家已无法立足,1931年春,继母带着她和弟妹,来到了阿城县福昌号屯,在叔伯家暂时栖身。福昌号屯是张家的老宅,却并不是她的安身之所。在佃户与叔伯爆发的一次纠纷中,她出于对佃农的同情,试图说服叔伯减轻地租,这让火上浇油的伯父暴跳如雷,将她痛打一顿后关进一间空屋子,又派人拍电报给张廷举,让他火速赶来将这败家的女儿勒死了事。
她叛逆,却深具正义情怀;她向往自由和爱情,却总是被情所伤。真实和特立独行,是她的关键词。她是一个本质纯真的女子,不习惯也不屑于曲意逢迎,没有机心,不懂得隐藏,却换来一生的惆怅与孤独。
阿城的秋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十月的村庄,已是草木凋零,霜冷风寒。在几位姑婶的帮助下,张乃莹偷偷坐上一辆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阿城,离开了那个曾经温暖而今冰冷薄情的家,开始一段艰难漂泊的旅程。
那一年,她刚满二十岁。走时,穿一件旧蓝士林布旗袍,憔悴,落寞,唯独眼神中倔强的坚定,依旧沉静凛然,不妥协,也不退缩。那是她留给呼兰河最后的背影,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颗自由的种子,已在她心底生了根。就像儿时的后花园,她可以是任意一朵花,一茎草,一片云,无拘无束地吹着风、淋着雨、沐着朝阳,没有屈辱和压迫。她多么向往那样的时光。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萧红《呼兰河传》)
而今,呼兰河小城里边,埋着她亲爱的祖父,也埋着她风一般的年少时光。她不再留恋,了无牵挂,因此她要带着一颗悲壮的心,去追寻自由和爱情。
这一次离家出走,是一条不归路。父亲怒恨交加,将她视作家族的耻辱,开除了她的族籍,并禁止家人与她联络,连她写给胞弟的信,都被扣留严查。四年后,由张廷举亲手编撰的族谱中,找不到关于张乃莹的只语片语,她仿佛压根就不是这个家庭的血脉。
然而,有没有家对她来说,早已没有任何意义。她整整一个多月都在哈尔滨街头流浪。寒冬已迫近,飘雪的哈尔滨,更像一口冰凉的枯井,每日每夜,她瑟缩着走在积雪的街头,像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寻找着光明和温暖。
那夜寒风逼着我非常严厉,眼泪差不多和哭着一般流下,用手套抹着,揩着……脚的下面感到有针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我家乡那边的马房,挂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
(萧红《过夜》)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她后来写这句话时,不知是否想起过流浪的日子。悲凉,是她此番的写照。但她宁愿如此,也不愿妥协。在哈尔滨街头,她曾不期然遇见已断绝关系的张廷举,父女二人冷脸相对,漠然擦肩;一个初冬的早晨,她又与堂弟张秀璇偶然相逢,在亲人眼中,她已落魄得让人心疼。
“莹姐,”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去,回家去吧!”等他说:“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去一次呢?”我不知为什么被他这话激动了。
也许要熄灭的灯火在我心中复燃起来,热力和光明鼓荡着我说:
“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
“那么你要钱用么?”
“不要的。”
“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啊!”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满着祈祷和愿望。我们又握过手,分别方向走去。
太阳在我的脸面上闪闪耀耀,仍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过街头,我无目的地走。寒风,刺着喉头,时时要发作小小的咳嗽。
(萧红《初冬》)
十一月中旬的哈尔滨,寒风刺骨,冷如冰窟,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衣衫单薄,饥肠辘辘,居无定所。她蜷缩着身子,以拥抱的姿势为自己取暖,她多么期待一个怀抱。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汪恩甲,出现在她面前。
于是,这个不该出现却又及时出现的男人,将她带到位于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以同居的形式,结束了她孤独的流浪生活。
后来,她成了孕妇,使她成为孕妇的男人,却在欠下旅馆一笔债务后,将她留作人质,逃之夭夭。
再后来,她给报馆写信——于是,她今生的传奇缘分就此开启。天注定,她一生挚爱的三郎,会在这一刻,不早也不迟,在正正好的时分,穿过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走进东兴顺旅馆长长的甬道,敲响了十八号房门。
她一直在那里等他,经历的一切磨难也许都是为了与他相见。为着这一刻,她等了整整二十年。
只喜欢看你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其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