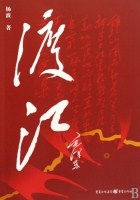他娶了不爱的女人
其实在我心底,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就数她最值得钦佩。
她是青炉中的一支香,燃了半截便灭了,烟散尽,余下的半截默然立在炉中,百年千年的立着,看不出遗憾与悲喜。只是在低回旋转的风中,偶尔会袭来淡淡沉香,告诉你她一直都在那里。
她留下的相片不多,一张单人小照,她娇憨可爱地睁大双眼,像一枚仲春枝头的青果,纯净的样子惹人怜爱;另一张,她与结婚六年的男人并肩而立,她想挤一个微笑,却是满脸的拘谨和僵硬,让怜她的人止不住心酸。这张照片拍完不久,她的男人徐志摩,在报上发了通告,宣布与她离婚。
从嫁进徐家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他们之间悬殊的姿势。即便做了他的结发妻子,也只是与他站在了云梯一样的石阶上,他始终站得比她高,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她,让她的仰望变得谦卑而拘谨。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第一个女人。与江冬秀一样,她们都是旧式婚姻的女主角。但迎娶江冬秀时,胡适已留学归来;而彼时与张幼仪成婚的徐志摩,还只是一名中学生。
1915年,也许是早了点。如果再晚几年,他可能会拒绝这桩媒妁之言的婚约。那一年,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刚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尚在萌芽,年满18岁的徐志摩也刚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他还来不及去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因此,这个羽翼未丰的徐家少爷,懵懂中接受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姻缘。
民国初年的徐家,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是有名的富户。父亲徐申如是硖石商会会长,不仅在本地开着钱庄、酱园、丝厂、绸缎店,在沪杭两地也拥有大量产业。徐志摩虽是徐申如的二太太所出,却是徐家的独子单传,因而从出生起,徐家少爷的生活,虽比不得脂粉堆里的贾宝玉,也是蜜罐香箩,宠爱缠身。
他本名章垿,字槱森。据说在他周岁时,一位法号志恢的僧人为他摩顶,信誓旦旦说了句“此子必成大器”,日后他果然聪慧异常,1918年临去美国留学时,父亲为他改名“志摩”,以铭记僧人志恢的吉言,激励他学有所成。
不论这名字来历如何,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确实聪慧灵敏,这或许是他天生的秉赋。幼年的志摩,既是“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也和“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鱼就和鱼儿说话”的贾宝玉一样,细腻敏感,浪漫多情,有着一颗绵密诗心。
我小的时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我的小心就欣欣怡悦,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
——(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
他的敏感诗心或许有着家族遗传,彼时经商的徐家虽不是诗礼簪缨,但此后却人才辈出,且出的都是文化界名人:金庸是志摩的姑表弟,沈钧儒是他的表叔,而台湾的琼瑶女士,则是志摩的表外甥女。细究起来,他们的祖上,都与海宁徐家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1910年,徐志摩以全校最优的成绩从硖石开智学堂毕业,在表叔沈均儒的介绍下,考入杭州府中,与郁达夫成了同班同学。他开始爱上文学、科学和天文学,并频繁在校刊发表文章。这段时期,他一直是杭州府中最优秀的学生。
1915年夏,志摩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上海浸信会学院。这一年他十八岁,他葱郁的青春如新竹破空,已是庾郎年少,俊逸拔萃。就在这一年,他生命中忽然多出了一个陌生女子,十五岁的张幼仪,嫁到了徐家。
若说这是一桩不幸姻缘,那么这不幸的始作俑者,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
彼时,上海宝山县的张家是远近闻名的望族。张幼仪的祖父为前清举人,曾在四川内江、屏山等地任知县。父亲张润之多年行医经商,育有八子四女,生于1900年的张幼仪,是张家的二小姐。在张幼仪的记忆中,张家人丁众多,不仅各有各的厨房佣人,甚至还有一个专替张家做鞋的佣人役。
也许得益于儒雅家风的熏陶,张家的子女成年后个个贤达,一半以上都成了知名人士。大少爷张嘉保,是沪上著名实业家,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少爷张君劢,曾留学日本,担任过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是颇为活跃的政治家、哲学家;四少爷张嘉璈,著名金融家,日后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八少爷张嘉铸,曾任中国蔬菜公司经理;而30年代享有盛名的新月书店,老板张禹九,也是张家的少爷。
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秘书的张嘉璈到杭州府中视察,在检阅学生课业时,读到一篇令他赞叹不已的文章,文笔极似他钦佩的梁启超先生。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才华横溢的徐志摩。
他当下便觉眼前一亮。这难得一见的好文,在他历次视察中绝无仅有。张嘉璈觉得,写文章的少年是生辉的珠玉,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光华耀野。他暗中调查这年轻士子的来历,当得知他是当地一个有钱好人家的少爷,便觉得无需再做更多查访,他心底埋了个念头,要给自己的妹妹、尚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张幼仪,做媒提亲。
张嘉璈迫不及待给徐申如写了封信,希望两家联姻以结百年之好。宝山张家已是上海显贵,徐申如当然求之不得,当即回信:“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满口应承了这门亲事。
显而易见,父亲的应允,是奔着“张嘉璈之妹”而去的,显赫门第,是他看中的筹码;而作为婚姻当事人的徐家少爷,面对父亲溢于言表的喜悦,却只有淡漠和无奈。
一枚小照呈在他的眼前。他瞥了一眼相片上的女子,用不屑的语气吐出几个字:“乡下土包子!”
第一次相识,就是通过两家交换的相片。他们都还懵懂,喜欢或反感,他们都不用掩饰。彼时张幼仪并不知道,徐家少爷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居然厌烦若此。多年后她依然清晰记得初见徐志摩相片的那一刻,尽管她叙述得平淡,却仍然让人感觉,那是一个传奇时刻。
我头一次听到我丈夫的名字,是在13岁那年。爸爸妈妈在我放假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把我叫到客厅,交给我一只小银盒子。
我想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他们说,看看他的相片。我打开盒子,看见一张年轻人的照片,他的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还戴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
爸爸想知道我对相片里那个人的看法。
我一言不发盖上盒子。自从大姐算过命后,家里人一直期待这刻的来临,我就依着家人的期望说:“我没意见。”
根据当时的中国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她这么早便订亲,确实与姐姐算过命有关。算命的结果是,幼仪的姐姐若二十五岁之前出嫁,必会夫亡家破。因而二女儿幼仪的婚嫁,只宜提前进行。
其实年轻的幼仪并不土气,只是有几分娇憨的青涩。志摩喜欢的是“有学养的女人”,是娇俏灵动的,可以点燃他浪漫的诗心和激情。张幼仪足够端庄贤淑,往后的事实证明,她是一个温婉可敬的女子。但这些优点,对在优裕生活中长大的徐家少爷来说,再好,也只是蒙尘的珍珠,他看不到光泽,也无心去探究她柔美的品质。
尽管他不乐意,但彼时的徐志摩,仍然尊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淡然接受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
张家的陪嫁之丰,多到令人艳羡。不仅嫁妆采买自欧洲,仅家具一项,就连一节火车厢都装不下,最终由幼仪的六哥专门用一艘驳船从上海运到了硖石。六哥回来的那一天,她望眼欲穿地盼着,因为直到此刻,张家人只从相片上见过这位传说中的佳婿。
至于我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六哥目光炯炯地说:“他才气纵横,前途无量。”
六哥说,徐志摩的志向和气魄都不同凡响。
当然,我很高兴听到这消息。我以为自己嫁了个和我哥哥一样思想前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1915年10月29日,上海宝山县张家的二小姐张幼仪,嫁到了浙江海宁,在硖石镇商会礼堂,与徐志摩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那一天,她眉目含情,娇羞动人,身穿一袭盘龙绣凤的粉红色礼裙,头戴中式彩冠,礼裙下,却是一双天足,她为此有几分不安。
幼年时,母亲给她缠脚,第四天便痛得不行,在她的尖声哭喊下,二哥君劢实在不忍,央求母亲解开了她脚上密密层层的布条,对母亲说:“将来如果没人娶她,我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她庆幸自己嫁的男人是新式青年,在他眼中,也许小脚并不比她的天足美丽,但她心底仍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她不敢想,这个秘密若是公开,她还能不能成为他的新娘。
当初算命婆看过她和志摩的生辰八字,认定他们属相不合,无法长久。在张家的一再权衡下,在将幼仪的生年报给徐家时,便虚减隐瞒了两岁。改过的属相与志摩自然十分匹配,徐家赞叹这姻缘简直是天作之合,唯有她自己知道,这是一个不能诉说的秘密。
十五岁,她还是个单纯的少女。她天真地以为,既然这个男人娶了她,那么她一生的时光,都将与他相守在一起。她只须做一个端淑贤惠的女人,一心一意与他过甜蜜温暖的日子,这一世,便安稳知足,再无所求。
志摩伸手掀开她的盖头时,她又害怕又激动,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虽然我想表现得像个新式女子,可是我办不到,只是瞪着他又长又尖的下巴。我本来希望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会对我一笑,可是他的眼神始终很严肃。
……当时的我又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我们之间的沉默从那一夜开始。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他们开头便这样潦草,似乎为日后的离散埋下了伏笔。他要的是心动,要的是爱情,要的是女子的柔媚和浪漫。他的小妇人却只有旧式女子的三从四德,和低眉敛声的恭顺。
幼仪虽不敏锐善感,但丈夫的冷淡依然伤了她的心。她是名门之女,嫁入徐家之前,她过着锦衣玉食、呵护有加的日子,现在做了徐家的儿媳,她放下了养尊处优的习惯,侍奉公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她自问没有失礼之处,却焐不暖这个男人冰冷的表情。
她对幸福生活最初的期望,像阳光下屋瓦上的积雪,一点点消散变得遥不可及。晚年她回忆徐志摩对她的不屑,想起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有一次,徐志摩在院子里看书,忽然背痒,便叫佣人过来替他挠一挠,她恰巧在他身边,理所当然走过去给他帮忙。彼时,他没有说一个字,却投给她一个轻蔑厌烦的眼神,那个眼神像一道长满利刺的栅栏,生硬地将她隔开,果断严厉地制止了她。
在徐志摩眼底,张家二小姐显赫的家世以及其他种种,都无法成为骄傲的资本。他一点都不爱她。他的目光几乎从不与她交接,偶尔落在她身上,也只轻飘飘地掠过。对他来说,这个他不爱的女子,只是徐家的儿媳,却绝不是他的爱人。
张幼仪无奈而伤感,在他面前,她日益拘谨而不知所措,一点一点散失了自信。她知道这个男人的心,她是抓不住的。
尽管痛苦,尽管失落,她却谨记着出嫁时母亲说给她的一番话。母亲说:嫁入徐家,你便是徐家的女人。记住,第一,绝不可以任性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与自己的男人发生了什么,你都要以始终如一的态度对待公婆。
于是,她守着偌大的徐家大宅,过寂寞冷清的日子。早晚向公婆请安,知礼明孝,恪守儿媳的本分。新媳妇不宜抛头露面,她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双接一双地给婆婆做鞋,一针一线地绣鸳鸯绣蝴蝶。她在那些精致的图案和艳丽的色彩中,消耗着芬芳的渴望,和一寸寸虚空的时光。
彼时的徐志摩,却愈发地玉树临风,俊逸出众。她有一种悲哀的预感,这样的男人,她快守不住了。
不搭调的小脚与西服
1915年深秋,婚后的徐志摩离开硖石,到上海继续求学。
当初选择在上海浸信会学院就读,徐申如考虑的是离家近,婚后的生活学习可两相兼顾。但上海浸信会学院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初到上海的徐志摩,既不喜欢这座城市的浮华,更不喜欢教会学院刻板的仪式和课程,因而他在上海只读了一年书,便于1916年秋,转入了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班。翌年秋天,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他也随之进入北大,主攻法学,兼修政治学、日文、法文和中外文学。
彼时的北平,正值军阀混战,民怨沸腾。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与段琪瑞上演府院之争,之后张勋入京,拥宣统复辟,只维持了十二天的复辟闹剧偃旗息鼓后,段祺瑞又挑起了南北战争。
而此时的文化学术界,新思潮正静水潜涌,新文化正在破土萌芽,一批留洋归国的文化精英们,引领着新的文化潮流,对西学的推崇渐成风尚。
在北平学习期间,徐志摩一度借居在军事家蒋百里府中。蒋百里是志摩的海宁硖石同乡,他在1913年任保定军校校长期间,因无法兑现对学生的承诺,在召集学生会议后举枪自杀,最后不仅奇迹般生还,并与看护他的日本护士堕入情网,结为夫妇。
这一段传奇经历让徐志摩极为倾慕。这样的爱情才是他憧憬的,他心里有一匹野马,有许多浩荡的春风,他期待一场浪漫的宿醉,他对自己媒妁之言的婚姻,日益厌倦。
尽管如此,他和张幼仪的长子阿欢,还是在1918年4月,来到了人间。
这一年初夏,在蒋百里的引荐和张君劢的介绍下,徐志摩正式拜师,成为梁启超先生的入室弟子。在胡适眼中,“徐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尽管日后在与陆小曼的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曾怒斥这一对新人,但这并不妨碍志摩成为他最得意的门生。
1918年8月,徐志摩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启程赴美留学。出国的愿望,他向往了许久,但他始终觉得欠双亲一个交待。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此刻,随着阿欢的出生,似乎全都迎刃而解。
“子息的问题既然解决了,徐志摩就得到父母允许负笈海外了。”这句话,多年后从张幼仪口中说出,仍透着淡淡的无奈和哀伤。她的婚姻,仿佛一开始便只是他的负担和任务。
8月14日,南京号远航轮驶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二十多天后,徐志摩成了美国克拉克大学的一名华人留学生。徐家以商行世,按照日后志摩的说法,“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因此在克拉克大学,他选择攻读银行学和社会学。
1919年6月,他以一等荣誉奖从克拉克大学毕业,旋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硕士。一年后,以毕业论文《论中国的妇女地位》,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无法揣测他在写这篇论文时,是否将张幼仪作为他笔下的旧式女子来参照。尽管他的论文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但这个看似清醒的智者,却在践行中国最传统的封建式婚姻,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