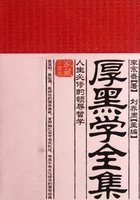宗懔《荆楚歲時記》正有可能是與蕭繹《荆南志》相互配合的地理著作,惟專記荆楚風俗人物之美,他們的這類著述又顯然與三國以來乃至梁陳時期地理風俗類著作盛行於世的文化背景相聯繫。我們知道,魏晉以來史學逐步獨立,在目錄學中,西晉荀勖已因魏鄭默《中經》,更著《新簿》,把《漢書·藝文志》六略簡化為四部分類,單列史書為丙部,東晉李充又把史書提前列為乙部。在教育中,宋明帝又把玄、儒、文、史並列為四科。在史書著述風氣盛行的大背景下,地理風俗類著作亦層出不窮,顯然又是門第地望觀念影響的結果。其實在東漢已有應劭著名的《風俗通義》和《地理風俗記》,魏晉至梁地理風俗書更是遍地開花,不過主要集中於荆楚、揚州即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關於荆州地區的略有:東晉時,有范汪《荆州記》以及羅含《湘中記》。在范汪之後的晉宋間以至南齊間,僅《荆州記》一名就有庾仲雍、盛弘之、郭仲產、劉澄之四種,庾、郭、劉三人還各撰《湘州記》。此外還有宋甄烈《湘洲記》、齊黃閔《武陵記》、《沅陵記》、《沅川記》,以及佚名《荆州圖副》、《荆南圖副》、《荆州土地記》、《湘州記》等。又有先賢耆舊傳記,如東晉張方《楚國先賢傳》、習鑿齒《襄陽耆舊傳》、高範《荆州先賢傳》、劉彧《長沙耆舊傳》、宋郭緣生《武昌先賢志》等。
從這種文化背景看,《荆楚歲時記》不僅跟蕭繹《荆南志》一樣屬於地理風俗著作,而且其書名或亦本作《荆楚記》。現存文獻最早引錄宗懔此記的是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所引十六條皆作《荆楚記》。唐初類書《藝文類聚》一般引作《荆楚歲時記》,而卷四之五月五日一條、卷八九之九月九日一條卻作《荆楚記》。《初學記》卷四之五月五日、宿歲迎年、去故納新三條,《史記·陳涉世家》唐司馬貞索隱引臘節一條,皆作《荆楚記》。此外白居易《六帖》卷四、段公路《北戶錄》卷二、韓鄂《歲華紀麗》卷二及卷三、《太平御覽》卷一七、二八等亦多如是。唐代文獻所引作《荆楚記》,特別是最早引用宗懔書的隋《玉燭寶典》均作《荆楚記》,這是值得重視的現象,說明該書或許本作《荆楚記》,而因其專記歲時風俗,故又名或改名《荆楚歲時記》或《歲時記》。《藝文類聚》不僅是最早引作《荆楚歲時記》的文獻,且其卷八六引桃制百鬼一條,是最早以《歲時記》標目的。所以,初唐是現存文獻所知最早稱作《荆楚歲時記》的時代,而隋代所稱《荆楚記》,則更像是魏晉六朝眾多地理風俗文獻的名稱。《北戶錄》卷二“紅鹽”條說,鹽也有“如傘”者,龜圖注稱“《荆楚記》具”,似乎《荆楚記》有這樣的內容,但事實上這種內容見於《太平御覽》卷八六五引《荆州記》。這又說明《荆楚記》與《荆州記》都可能是地方風物之書,且名目近似,故因其專記歲時而改稱《荆楚歲時記》。當然,其序言明謂“率為小記,以錄荆楚歲時”,故杜臺卿也可能是略稱“荆楚記”,只是這種略稱的可能性較小,略稱是與全稱相對而言的,全稱既未先見,何來略稱?
除了上述多種地理風俗著作以及《荆楚歲時記》序提到的文學作品外,對宗懔著書產生影響的還應有魏晉間周處的《風土記》和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周處(238-297)《風土記》又名《陽羨風土記》,專記陽羨(今屬江蘇宜興市)風土民情,但與一般地理風俗著作不同,已特別包含歲時風俗,如正旦、上巳、端午、七夕、重九這些重大歲節風俗都得到記錄,應是中國古代最早較多記錄歲節的地理風俗文獻。《續齊諧記》雖為小說,卻是一部歲時風俗佔有較大比重的作品,記有正月(祭蠶)、上巳、端午、七夕、八月(承露)、重九等重要歲俗。據《梁書·文學傳上》,吳均“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則吳均(469-520)比宗懔早生三十餘年,多記歲俗的《續齊諧記》完全有可能影響《荆楚歲時記》的撰述。這些當然也是杜公瞻注常引《風土記》、《續齊諧記》的原因。
宗懔序稱其書“凡二十餘事”,而今本實有三十六事,知“二”字或為“三”字之訛,篇幅儘管不大,然其原本早已佚失。關於《荆楚歲時記》的散佚,學界一般以為是元代前後。理由是元末明初陶宗儀《說郛》(明抄本)節錄僅八條,明《永樂大典》未見引錄,而在萬曆間出現兩種輯本,所以亡佚當發生在宋元或元明之際。其實這樣的判斷也非確論。隋唐及宋初的引錄也還有差異,這不免讓人懷疑它的亡佚時代甚早,比如著成後隨即有元帝的江陵焚書,然後是北朝及隋唐的頻繁易代,儘管它可能免於一時的兵燹之災,但時代動蕩總是不利於保護和傳播的。當然歷代文獻還有不少引錄,只是我們實在不能保證其絕對可靠性。
今存《荆楚歲時記》的最早版本當是南宋初節錄本,先為紹興六年(1136)曾慥《類說》卷六所錄十五條本,又有次年序刊之朱勝非《紺珠集》卷五所錄十九條本。二書皆抄綴古書,節選摘錄,不能據此判斷他們所錄即是《荆楚歲時記》的全本乃至原本。今傳本主要是明萬曆間的兩種輯本,但二者系統彼此不同,正文與注文混淆,不明出處,皆非全真。
我們這裏不妨從唐宋類書的引錄及南宋初《類說》、《紺珠集》的節錄情況出發,考查《荆楚歲時記》正文及注文的變異情況,剔除一些“似是而非”的文本,或是分析是否還有一些“似非而是”的佚文存在,以檢驗今傳明輯本的可靠程度,並進而為考查相關民俗傳承和文化演進提供參考。關於“似是而非”的“人日”文本我們已有另文專門分析,指出其與文獻聚散、民俗傳承、文學表現之間的關係,並以為《荆楚歲時記》的亡佚大體在兩宋之間,這裏主要看看“似非而是”的情況。
《太平御覽》卷三一引《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彩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宋孝武《七夕詩》曰:迎風披綵縷,向月貫玄針。陳瓜果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以為符應。”其中“鍮石為針”後小字為杜公瞻注文,《太平御覽》在引錄時多能以大小字區別正文和注文,大體保留原書面目,頗為珍貴。重要的是此條後接引的文字:
周處《風土記》云:“七月初七日,[俗]重此日[9],其夜灑掃中庭。”然則中庭乞願,其舊俗乎?
又曰: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為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為陽數,故以麋為珍。”今北人唯設湯餅,無復有麋矣。
又曰:陸雲《與平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書刀五枚[10],[又]琉璃筆一枝[11]。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妤[折之][12],云:‘見此[期復][13],使人恨然。’”案,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雜矣。
上引《風土記》以下又有兩條“又曰”,我們一般會將這三節文字都作為《風土記》佚文看待,但實際可能是杜公瞻注《荆楚歲時記》的文字。
第一條:據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七、《初學記》卷四、唐抄《文選集注》卷五九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題注唐公孫羅《文選鈔》、南宋陳元靚《事林廣記》甲集卷上等引《風土記》七夕風俗文,均無此之“然則中庭乞願,其舊俗乎”一句,此句是溯源式討論,又和上引《荆楚歲時記》相連,特疑同是《荆楚歲時記》注文。《太平御覽》此卷下文又引周處《風土記》曰:“七月初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酺時果,散香粉於筵上,以祈河鼓《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咸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卷三一此處則為節引,當是《太平御覽》編者轉錄自《荆楚歲時記》注文。
第二條:雖然周處言及角黍的佚文最多,但除《歲時廣記》卷二六(“設湯餅”條)、清李光地等《御定月令輯要》卷一四《七月初七·良日》照搬外(略有字誤,引作《風土記》,當是誤讀“又曰”),似未見有他書引及《風土記》此條。而《荆楚歲時記》中多有董勛言論,湯餅和麋(糜)粥也是該書所記常見的歲時食物。此條末句所謂湯餅和糜粥的消長代興、南北差異(周處為南方陽羨人),也是梳理民俗發展史的文字,故應仍是《荆楚歲時記》注文。
第三條:此條另見於北宋吳淑《事類賦》卷五《秋·魏宮愴琉璃之筆》注引《風土記》:“陸機《書》曰:‘在平原,嘗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瑠璃筆一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妤云,見此使人悵然。’按,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知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雜耳。”清李光地等《御定月令輯要》卷一四《七月初七·曹公器物》引陸機與弟書:“在平原,嘗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又《太平御覽》卷六○五引《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璃琉(琉璃)筆。”均稱陸機書,與《太平御覽》此處引稱陸雲與兄書不同,《陸士龍文集》卷八亦作陸雲《與兄平原書》。按,古籍多稱陸雲《與兄平原書》(《太平御覽》多處引陸雲與陸機書,言按行曹公器物事),時陸雲任職京城,檢視曹操舊物,而此事非在平原之陸機所能為,平原在今山東濟南西北一帶。故當以陸雲《與兄平原書》為是。
但上述《太平御覽》卷六○五引《荆楚歲時記》的文字暗示我們,卷三一《風土記》下“又曰”中的琉璃筆事,並非出自《風土記》,而應是《荆楚歲時記》注文。事實上,《風土記》也是不可能記載陸雲所謂琉璃筆一事的。據《晉書·陸機傳》,西晉惠帝太安(302-303)初以前,成都王潁“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又《惠帝紀》言成都王潁封大將軍在永甯元年(301),則陸機之作平原內史即在此年,次年河橋之敗後機即被誅。再據《惠帝紀》和周處本傳,周處早在元康七年(297)討伐齊萬年的戰役中以身殉職,那麽他是不可能在《風土記》中記載陸機作平原內史以後兄弟通信事的[14]。從諸書引《風土記》佚文看,這種辨偽性質的議論語言絕少,如《太平御覽》卷六四南易水條、卷九二三祝鳩條中的案語頗疑為後人所加,琉璃筆事這一特別加注案語的佚文的確更近似於杜公瞻的注文風格。
不過,案語所辨亦失於深察。《三國志·后妃傳》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倢伃,有容華,有美人。”倢伃的待遇“視中二千石”。《曹爽傳》又載,爽“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所伎”。陸機《吊魏武帝文》云:“元康八年(298),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引按,即使是陸機能在祕閣見曹操舊物,也在周處卒後),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魏武帝)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床,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則曹操是有婕妤的。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卒,至魏明帝景初二年(238,《陸士龍文集》卷八作三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七夕話情”的往事未致模糊(《陸士龍文集》云:“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劉婕妤是有可能恨而折筆的;也不能因為事在曹操卒後多年的明帝景初間,乃謂琉璃筆等為“文帝物”而與“曹公器物”誤混。
再看《寶顏堂秘笈》本《荆楚歲時記》注有第一條“然則中庭乞願,其舊俗乎”二句,《廣漢魏叢書》本則無,至於第二、三條二本皆無。看來,《太平御覽》卷三一引《風土記》三條中後二條的“又曰”帶來不少誤會,準確的體例當是在第一條首加注“又曰”,因為這三條都屬於《荆楚歲時記》,其中解說梳理性文字顯然是杜公瞻注文。我們若經仔細考辨,特別是從文獻傳播、撰述體例或民俗傳承歷史的角度重為清理,像這種與《荆楚歲時記》連引的文字,只要有較為堅實的文獻依據,就是可以作為佚文看待的。由於《荆楚歲時記》正文與注文相混,又多與歷代各種“歲時記”相混,歷代又有各種增注、補注、續編本,所以在沒有全面可靠的精校本以前,我們使用《荆楚歲時記》還需特別小心,儘量多加考證覆覈,纔能梳理出較為準確的文獻演變和民俗傳承歷史。
注釋:
[1]今傳版本主要有:明萬曆二十年(1592)何允中《廣漢魏叢書·載籍》本、萬曆四十三年(1615)陳繼儒《寶顏堂秘笈·廣集》(亦名《陳眉公家藏廣秘笈》)本。校注本有:譚麟《荆楚歲時記譯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荆楚歲時記》,姜彥稚輯校,岳麓書社1986年6月版;《荆楚歲時記》,宋金龍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荆楚歲時記校注》,王毓榮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8月版。又日本守屋美都雄有譯注《荆楚歲時記》,平凡社1978年2月版;《校注荆楚歲時記——中國民俗の歷史的研究》,帝國書院1950年版。研究論著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八,史部六,地理類三,中華書局1980年5月版,第1冊,第440-447頁;李裕民《宗懔及其〈荆楚歲時記〉考述》,見宋金龍校注本(作為代序);蕭放《〈荆楚歲時記〉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此外日本守屋美都雄、德國赫裏嘉·吐爾斑等也有討論。
[2]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言“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等校史部之書。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八據此以為:“懷正當是懔之字,然與諸史言字元懔者不同,且之推此注,于諸人皆稱名,而懔獨舉其字,亦所未詳,豈嘗以字行,而史略之耶?”按,余氏推測宗懔或字懷正,雖無確據,但大體可信。懔,有敬、畏之義,故與“懷正”近。《論語·學而》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而也已。”敬畏則敏慎,懷正則可學矣。又《後漢書·孔融傳》論曰:“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李賢注:“懔懔,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知懔亦剛烈正性義。
[3]一些學者以為宗懔與顏之推在北周共校圖書,或是把北周麟趾殿刊校事與《觀我生賦》自注所謂江陵校書事混淆,都是因為誤讀《觀我生賦》,而忽略了宗懔在江陵校書的經歷。《觀我生賦》“或校石渠之文”乃敍江陵時事,其後又記江陵陷落之際元帝焚書:“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顯然,前言“校石渠之文”,事在元帝即位前後的江陵時期。若宗懷正果為宗懔(懷正為吏部尚書,正合宗懔在元帝時官職),則其在江陵、長安皆嘗校理圖籍。又,顏之推與宗懔曾在江陵校書,但後來被西魏俘獲入關,旋即冒險奔齊,齊亡方入北周(《觀我生賦》即作於齊亡入周之際),其時宗懔已卒,何能再與宗懔共校圖書?
[4]蕭繹《金樓子·著書》記自撰《荆南志》一帙二卷,《梁書》本紀亦言作《荆南志》,而《南史》本紀作《荆南地記》,《太平御覽》卷四九等引作《荆南記》,《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又著錄作《荆南地志》二卷。《隋書·經籍志》著錄蕭世誠撰《荆南地志》二卷,世誠實即蕭繹字(《梁書·元帝本紀》)。
[5]參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2006年6月版,第4冊,第43-56頁。
[6]以上所考世系及人物有三種,前人所考為:①奕-玄-瑍-靈運-鳳-超宗-才卿(弟幾卿)-藻;②萬-韶-思-弘微-莊-(瀹)-覽(弟舉)-札(兄僑)。不過謝札也可能屬謝據一系:③據-允-裕-恂-孺子-璟-徵(微)-(札)。
[7]參楊勇《謝靈運年譜》,見《楊勇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2006年9月版,第393-397頁。
[8]元帝《封劉瑴宗懔令》言:“中書侍郎宗懔,亟有帷幄之謀,實惟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據唐許敬宗《文館詞林》卷六九五。《周書》本傳辭略異。)
[9]“俗”字據《歲時廣記》卷二一(“啖葅龜”條)引《風土記》補。
[10]“有”字原無,“枚”字原作“板”,據《四庫全書》本《太平御覽》補正。書刀,刻寫刊改之刀。
[11]此句原作“瑠璃筆一枚”,鮑崇城本《太平御覽》同,據饒世仁本、四庫本改,又據後者增“又”字。
[12]“折之”二字,據饒氏本、四庫本補;然四庫本此下無“云”字。
[13]“期復”二字諸本無,饒氏本有,又《陸士龍文集》卷八亦有,故據補。
[14]《世說新語·自新》載周處少時為鄉里所患,乃尋二陸,陸雲勉之改勵,終為忠臣孝子。勞格《讀書雜識》卷五《晉書校勘記》考訂周處(238-297)、陸機(262-303)生卒年,以為其生年相差24歲,《世說新語》及《晉書·周處傳》載周處訪陸機事亦未免近誣。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93年12月版,第627-6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