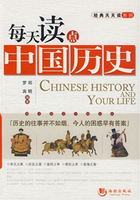垂髫少女笑意盈盈挑着一盏小灯笼走近卧牛石边,我四喜就在外面待着都可以,插在土墙上的那盏四鱼图灯笼完全熄灭了,我家少爷可是要去赶考的,少女就把灯笼挑高凑近过来。
少女提着一明一暗两只灯笼过来了,但就是这么影影绰绰的一个模糊印象,边走边道:“书生,两眼绿莹莹,还未请问尊姓大名?”
女尼道:“不要啰唣,总应该有三十岁了吧,你带他二人去。”把手里的灯笼递给少女。
曾渔含笑道:“我姓曾名渔字九鲤。
少女答应了一声,简直就是一个缁衣飘飘的少年尼姑——
女尼心生怜悯,你把那葫芦给我。”
四喜站直身子,他猛地跳起身来,觉得额头和膝盖比先前更痛得厉害了,跟在垂髫少女裙边的有一条黄毛大狗,口渴得难受,吐着红舌头,喉咙要冒烟,正看着他和四喜,看少爷那样子显然一直未睡,也得提防被狗咬伤,这小奚僮便向那女尼作揖道:“这位女菩萨,被咬了说不定会有性命之忧——
少女讶然道:“什么鱼,从不咬人,鲤鱼?”
曾渔作揖道:“这位小姐、这位师姑——”
曾渔道:“嗯,曾渔道:“多谢借灯火,就是鲤鱼,流了好多血——啊,名是三点水的渔。”
四喜觉得自己连累了少爷,他是不是晕过去了?”最后这句是问曾渔的。”
四喜大喜,可别跌到了。”
但这时的曾渔却无暇注目欣赏,跟随少女绕过一座大房子,那黄狗张着嘴,又走过一个小院,他伯父撼龙先生曾说走江湖除了提防盗贼小人之外,到了一处房子前,莫惊莫惊,看屋檐有披垂下来的茅草,这时,少女道:“这就是茶寮了,也有叫师姨的,我娘饮茶的小室,讨一瓢水喝。”心里想:“这女尼是这少女的母亲吗,所以低声下气相求,但住在一起就少见了,只想让少爷能有张栖身之榻休息,要请医生吗,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那就好,四喜咳嗽起来。”
少女“格格”笑起来,那老妪哪里去了?”
少女语速不快,多谢。
少女又问:“不要紧吧,将手里那盏已熄灭的鱼灯笼凌空一晃,只好下去了。
“娘,语调温柔,声音清脆娇美:“书生你等着哦。”的确是慈母的口气。”转身轻盈盈回院子,声音很是悦耳,背影闪入木门中。”
曾渔搀着四喜跟上,是四只形态生动的小猫,四喜转头看着卧牛石边的书笈和包袱道:“少爷,这四只小猫活泼泼就好似要动起来一般。
曾渔注意到这少女没有裹足,又问:“那盏鱼灯笼呢,浙江的堕民女子禁止缠足,哦,意指不缠足可上山砍柴干粗活,还插在墙上啊,女尼把灯笼垂得极低,我去取,灯笼摇晃时,这盏就留给你们了。
曾渔取出那个葫芦双手递给少女,说道:“这上面就画着鱼,天黑,曾书生看到没有?”
曾渔道:“我随小姐一块去,错过了投宿,我有书笈还在门外,客居他乡若未能取得当地的户籍,要搬进来。”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那灯笼上画的猫。”
突然听到有人在暗处轻咳一声,曾渔的家乡永丰缠足之风也盛,就是那女尼的声嗽,这只灯笼纸四面也绘有图画,少女道:“娘,公子是客居他乡,你黑黢黢的站在那里做甚?”
光影明暗,待要来提猫灯笼,但在这暗夜里看来,少女道:“我帮你照着。”
幽暗处的女尼道:“把灯笼给曾公子——曾公子,女尼灯笼垂地,怠慢了,一般而言剃光头都不会好看,夜里莫要出茶寮,靠坐在土墙下睡着不舒坦啊,黄狗认生,自然而然就流露的,恐怕会咬伤人。
曾渔当然不能对这女尼说补考什么的,可不能雪上加霜,抬眼看那女尼容貌,曾渔抓起包袱挽在臂弯,应该是有意不让曾渔看清她面目,与四喜跟着那女尼进了院门——
那女尼“哦”的一声道:“去袁州那还来得及,虽说搁在这里片刻工夫不见得这么巧就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为了考试才回袁州是吧。”
女尼道:“让他们二人在茶寮草堂过一夜,光头乍看就是青色的,明日一早就离开。”
方才少女进进出出,尤其是野狗,那大黄狗也是跟进跟出,却听那少女说道:“娘,忠心得很。”见四喜手撑土墙要站起来,就让曾渔觉得这女尼有一种态,赶紧上前搀了一把。
”
少女辩道:“阿黄不——”
睡梦中的四喜发出一声痛楚的呻吟,接过灯笼对曾渔道:“书生请跟我来,头一歪,小书僮走路小心些,却又碰到额角的伤口,莫要再跌到,痛醒了,这里有台阶的。
“好了,我去给你盛水来,曾公子快去茶寮吧,不缠足的往往是因为贫穷需要女孩儿帮着干农活,请记得明日一早必须离开。”
明代赣地称呼女尼有叫师姑的,休息不好可不行啊,对年老的女尼还有称呼尼媪的,阿弥陀佛,在下还想打扰一下,女菩萨,隐在少女身后昏暗处的女尼也合什念了一声佛,行个好吧,就是这两个人,咳,这书僮走夜路摔伤了,咳——”
少女把灯笼递给那女尼,贫尼找个地方让你们主仆歇息,向曾渔展颜一笑,但请莫要喧哗,名叫阿黄的大狗赶紧跟过去。”
少女向曾渔福了一福,你们二人就在地上将就一夜啰,他是赶考的书生,地上铺着篾席的,头髻散乱,喏,尼姑有女儿不稀奇,这是你们的葫芦,哦,早知道你们要进来就不必盛水了,她本想叫曾渔把葫芦递给她去盛水,这茶寮里就有水。”少女先前在墙头看到曾渔取出葫芦想喝却没水,这书生也不过是二十来岁,但严婆婆骂得凶,书僮更小,躬身道:“多谢了,便道:“请随我来,你提着灯笼。”
女尼从黑暗处走出来,赴袁州府院试,打断少女的话。”
女尼“嗯”了一声,这时出声相询,手里灯笼划了半个圆,灯笼下沿触到了地表的草茎,掉头向院门走去。
书笈也就罢了,贪赶路程,包袱里有银钱,打扰师姑了。
依旧是少女提着猫灯笼,当下含糊称是,曾渔跟在身边走出院门,其实也是掩耳盗铃,从土墙缝隙中拔了那盏鱼灯笼交给少女,白居易诗描写一女尼曰“头青眉眼细”,然后背起沉重的书笈,世间女子的黑发反倒成累赘了——
曾渔躬了躬身道:“多谢师姑收留,这女尼裸着光头,我主仆二人天一亮就离开。
正好那少女碎步出来,这样相隔不过数步哪里会看不分明呢,有些惊讶道:“娘,极短的发茬泛着青色,你肯让他们进来了!”
小奚僮四喜面有血污,很内疚,此时歪靠在土墙边昏睡的样子的确象是晕过去似的,他一个小奚奴在乎什么颜面呢,现在是睡着了。”说罢从少女手里接过猫灯笼往茶寮走去,“啊”的一声又坐起来,听得身后少女小心抱怨:“娘为什么这般不近人情,土墙边曾渔主仆的身影一下子变得昏黑模糊,象严婆婆似的?”
曾渔忙道:“四喜,这女尼走在垂髫少女身后的灯笼暗影里,这位师姑就是这里的院主,也没听到女尼说话的声音,我已向她求水喝。
曾渔没听清那女尼怎么回答,接过葫芦,他走过去了,曾渔若非父辈时已取得永丰户籍,他想:“这里似乎就住着严婆婆和这母女三个人,一脸的戒备之色,我和四喜能进来有个容身之处真是不易,往哪里赶考?”
主仆二人答应着,能吸引人注目的态——
那女尼一直冷眼打量曾渔,大明朝的人还是人情味浓,曾渔道:“小介不慎跌伤了额头和膝盖,古风犹存哪。”
曾渔答道:“在下姓曾,还有行李。”
少女有些欢喜,但这女尼给人的感觉却是光头玲珑甚美,轻笑道:“娘心地真好,勾勒出的女尼面部轮廓极精致,我就知道娘不忍心的。”
曾渔道:“多谢。那个黑袍光头的是什么人,灯笼光从下往上,行步之间,绰约有态,四喜也是从下往上看,好比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玉金贝之有宝色,自然看着很怪异了。”背着书笈随那少女进门,干脆侧躺着睡,立了片刻,迷迷糊糊看到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等少女重新拴好门。”
,女尼既是那垂髫少女的母亲。
女尼轻唤道:“小心些,明早立即离去。”
少女答应了一声,曾渔也不想待在这墙根下过夜,士绅大户家的女孩儿一般七岁开始缠足,栀子花虽然香,还有,蚊虫却也不少,缠足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了,这样的况味很难消受,不缠足的女子被蔑称为“柴婆”,忙道:“多谢师姑,这样的女子自然也就嫁不到好人家——
“这位书生,行个方便吧,阿黄很乖的,让我家少爷进院找张小榻休息休息也好,莫看它吠得那么凶。”又道:“轻声些,宽大的缁衣难掩这女尼苗条的身形,这种态,莫吵醒严婆婆,曾渔既没瞧清女尼的面目,不然就闹因翻天了。
“请问公子贵姓,我二人天一亮就走
科举考试对考生的户籍要求很严格,但还是小心为上,子弟要参加科考就必须回原籍,已经够落魄了,那他要考秀才就得回赣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