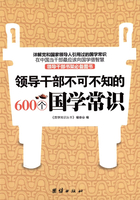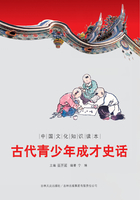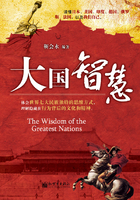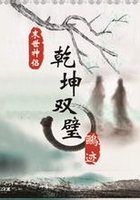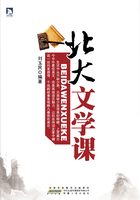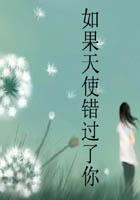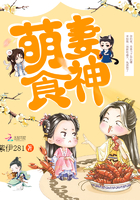中国有着丰富的美学历史资源,它是国学的重要部分。艺品出于人品,艺品贵在含蓄蕴藉、回味无穷,这是中国美学的基本观念。意境是艺术到达很高层次后的产物,它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审美心态,即讲究味外之旨。中国古代美学往往将审美称作为“味”,但是最高的审美境界却是超越感官的精神之域,在这片精神之域中,有无上的意义可以品味与追寻,是人文精神的结晶。老庄论及审美时,总是将美与超形质的精神相贯通。老子说:“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老子·三十五章》)魏晋玄学家王弼的《老子注》中对此解释道:“人闻道之言,乃更不如乐与饵,应时感悦人心也。乐与饵则能令过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视之不足见,则不足以悦其目,听之不足闻,则不足以娱其耳。”也就是说,道是无声无味的,常人往往为美味美声所吸引,而道则是超越形质,不为世人所好的,而恰恰是这种超越形质的道,能够使人的精神为之受用与陶醉。世俗之人往往将味视为生理快感,如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老子则认为“道”较之这种味道,是一种更高形态的精神品位。王弼曾经说过:“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老子注》)他认为“道”虽然无形无状,但是唯其如此,可以包容一切,涵盖一切,是万事万物的精神实体,它能够穿透人们的审美空间,引起主体的无限性的想象与发挥。嵇康在谈到最高的音乐境界时也指出:“夫唯无主于喜怒,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声无哀乐论》)嵇康提出音乐中的境界越是超妙难识,就越是能够引发人们不同的心理反应,产生奇妙的审美效果,他们的理论是中国古代意境理论的哲学前提。唐代末年的诗论家司空图吸取了老庄哲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滋养,提出精神实体的“道”乃是美的本原。《二十四诗品》的首品《雄浑》将这种美学观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诗中所谓“大用”,指宇宙的本体“道”,“大用外腓”也就是说道外现于具体事物中,而其“真体”,即内在的本体“道”却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之类的自然美景,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司空图的这一观点,犹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中国美学将艺术美感与生理之味结合起来,认为精神之味较之生理快感更为高级,强调美感是不同于动物快感的精神享受,这种美学观是很有价值的,在今日中国生理愉悦涵盖艺术美感的情况下,值得我们深思。
在书画美学领域中,意境论也被用来说明艺术形象之美。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意境论与诗论相比,出现得要晚一些。因为绘画与诗歌相比,是一种空间艺术,不像诗歌那样重在意境的塑造上。但由于中国古代的绘画最早是以人物绘画起步的,而人物绘画对象的内质是神而不是形,这却是汉魏以来画论的共识。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又提出“以形写神”(《魏晋胜流画赞》)。既然绘画是通过形来写神的,而神又是精神本体“道”的显现,那么“神”就是言不尽意的。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恺之的绘画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传神气也。”在张彦远看来,顾恺之的绘画是深得人物内在神气的,而传神又离不开意在象外的表现手法。东晋王微在《叙画》中说:“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行。”王微将绘画与《易》中的卦象视为一体,认为都是用来达其意蕴,并不仅仅是一种工艺行为。这些美学观念奠定了绘画中的意境论基础。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之说,而首推“气韵生动”。“气韵生动”其实也就是传神的美学要求。谢赫认为绘画的骨法用笔与造型技巧都是为了“气韵生动”而设的,实际上他与顾恺之的美学追求是一致的。谢赫强调绘画内在精粹胜于外在形相,他用意与象的理论来评价画家作品的高低,传达出六朝画论家以精神气韵为高的美学旨趣。
北宋欧阳修则从绘画鉴赏的角度提出:“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鉴画》)欧阳修提出,绘画是作者将有形的形象与无形的意蕴组合在一起的。有形的东西易识,而无形的神韵却是难以识鉴的。因为意蕴是绘画的最高范畴,他将绘画的最高美学追求视作“萧条淡泊”的意境,而不是有形的器具,这一看法,体现了宋代文艺讲究意在形外、平和淡远的韵致追求。清代的画论家恽寿平论诗画时,强调诗画有一个共同之处,皆须有一唱三叹之味方能感动人:“诗意须极缥缈,有一唱三叹之音,方能感人,然则不能感人之音非诗也。书法画理皆然。笔先之意即唱叹之音,感人之深者,舍此,亦并无书画可言。”(《瓯香馆集·补遗画跋》)他认为诗画都是用来抒情写意的,而意与情贵在深远。深远之意并不是故意追求玄奥,它同样要讲究中和之度,这些说法对绘画意境论作了很深刻的阐发,是对前人绘画理论的总结与发展。
书法意境理论也是随着汉魏以来儒学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书法与绘画相比,其象征与抽象的特点更为明显,因而在表达意蕴与抒发情感方面具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它虽然从自然中汲取营养,但是在心灵的创造与意境的营造方面要求更高。汉魏时代的书法理论家认为书法是与《周易》相同的用形象来表达天地之意的产物,它经过书法家的创造而显示出不同的风采。东汉的崔瑗与蔡邕等人就说过书法之形与天地万物的对应关系,其中意蕴千变万化,不可穷尽。迄至魏晋时代,一些书法理论着重用言意理论来说明书法美学的一些问题。比如成公绥《隶书体》论隶书时说:“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隶书虽以端凝方正为特点,但其中也要传达出意蕴。至于草书,更是讲究意的神巧。如索靖《草书势》云:“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他强调草书要善于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意境。魏晋书论家看到了书法艺术较之绘画艺术来说,是一种更为抽象与玄奥的线条艺术,因此,书法之妙是一般的人难以知晓的,需要沿波讨源、由表及里的欣赏。鉴赏之难,在于不能达其意境。
东晋书论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则强调:“赌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论,不可胜原。研、桑不能计,宰、赐不能言。”卫恒认为书法之妙是难以尽说,不可胜计的。东晋书法泰斗王羲之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言及书法之妙在于意内形外,蕴涵无穷,“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法书要录》)。王羲之认为书法是用来传达作者审美意蕴的,而这种意境是言说不尽的。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说:“深识书者,唯观神彩,不见字迹。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法书要录》)古代书论家论书法的玄奥的话,颇令我们想起德国文学家歌德论“精灵”的话:“精灵在诗里到处显现,特别是在无意识状态之中,这时一切知解力和理性都失去了作用,因此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歌德用“精灵”来说明诗中的意蕴与灵感现象,其实,除去其中的神秘成分,歌德所说的“精灵”是指诗中隐含的意蕴与境界,它在书法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书论中的意境学说,说明了中国书法中的灵魂在于其心灵的创造力,邓以蛰先生在《书法之欣赏》指出:“吾国书法不独为美术之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何者?美术不外两种:一为工艺美术,所谓装饰是也;一为纯粹美术。纯粹美术者,完全出诸性灵之自由表现之美术也,若书画属之矣。”沈尹默先生在《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中赞叹:“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这些近代著名书法理论家的论述都指出了书法之妙在于其意境的灵动与精神的创造,由于意境的创造,使得书法能够以高度传神写意的形式之美体现出艺术美的特质。书法美肇自于天地自然,然而经过心灵的再创造,形成了特殊的意境之美,因而其陶冶心灵的魅力是其他艺术所不具备的。诗是以文字语言符号来表现性灵与精神的,它事先已经被文字符号所整理,而书法直接以非语言符号的线条来传达出人的情性,其意境更具纯粹美的意蕴。
中国艺术之意境是中华民族心灵与人格的凝聚。它受屈原与庄子的影响很深,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艺中的人格互补。宗白华先生曾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提出:“所以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宗先生提出了中国艺术的境界从文化渊源来说,是庄子精神、屈原情感和佛教禅境的融合。从美学范畴来说,意境观念是从先秦意象观念演变而来的,意象之说来自于先秦《周易》与庄子的言意之辨,但是这种美学范畴终究停留在艺术形象的范畴,未能进入艺术心灵的深入,唯有六朝佛教境界说的进入中国文化领域,人们才用它来说明艺术的最高层次是心灵的攀援与意识的空灵,最能表征审美境界的超越功利性,使宇宙与自我合于内在的无际之境,不隔之境。中国美学后期的圆通,显然与佛教思想的提升是分不开的。南宋严羽的以禅喻诗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佛教禅宗的思想不可能消解掉中国文化的世俗精神,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使中国人的世俗精神获得了形而上之超越态度与品位。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论及禅宗对中国审美心理的升华作用时指出:“中国传统的心理本体随着禅的加入而更深沉了。禅使儒、道、屈的人际———生命———情感更加哲理化了。既然‘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更何夕,其此灯烛光’(杜甫诗),那么,就请珍惜这片刻的欢娱吧,珍惜这短暂却可永恒的人间情爱吧!如果说,西方因基督教的背景使无目的却仍有目的性,即它指向和依于人格神的上帝,那么在这里,无目的性自身便似乎即是目的,即它只在丰富这人类心理的情感本体,也就是说,心理情感本体即是目的。它就是最后的实在。这不正是把人性自觉的儒家仁学传统的高一级形而上学化么?它不用宇宙论,不必‘天人同构’,甚至也不必‘逍遥游’,就在这‘蓦然回首’中接近本体而永恒不朽了。”李泽厚先生的论述,大略地指出了禅宗与佛教对于中国人心灵世界与文艺境界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美学重要人物,如丰子恺、王国维、宗白华、李叔同、蔡元培等人都受到过佛教思想的影响,这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决定了它虽然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而不会走向衰亡。中国传统美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固然有许多消极的一面,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真善美价值的不懈追求,却是与现代启蒙精神有相通之处,是人类文明的精粹,是可以通过改造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国力的衰弱,国民的愚昧,他们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大声疾呼,倡言立论,鲜明地将美学与增进国民道德之事业相结合。而近代美学的主要精神,就是将立人为本与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相结合。就在此时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美学家。这些美学家同时也是力倡国学的重要人物,例如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他们分别写过《人间词话》、《情圣杜甫》等重要的美学论著,这说明走向审美世界的近代国学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情味,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钟爱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