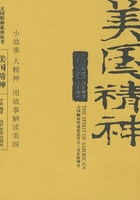名诗人和艺术批评家宾阳(Lourence Binyon)称:“中国以其新建立的团结与统一,作伟大的奋斗,以反抗无情的侵略,在一切珍视自由的国家里获得了倾心的同情与赞叹。我们很久已经尊重中国过去在和平的艺术中的成就,现在对于她的可惊怖的奋斗与受难的英勇,谨重表示其敬意。并祈祷中国克服困难,安全脱险。”
原剑桥大学中文教授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说:“我相信差不多全世界都盼望中国胜利,并且一切和我谈过这件事的都和我一样相信中国会得到实际的胜利。中国已获得全世界的钦服,中国自抗战以来之坚强和团结不但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就是那些了解中国,爱好中国的人们也非其预料所及的。”
修中诚不仅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赞扬中国领袖和人民的精神,相信中国必将胜利,而且抨击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指责英国的小人政治家,以英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拥有君子精神鼓舞“为正义而作伟大的战斗”的中国军民。
汉学家的真挚话语表明,“这一个伟大的抗战,不但使轻视中国、不了解中国的人,要对中国重新估价,就是‘那些了解中国爱好中国的人们’,也要重新估定其了解与爱好,他们今天的同情是已经有质的不同,不仅是同情一个产生过‘雨过天青’磁瓶的国家,产生过杜甫、白居易的国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站起来抵抗野蛮侵略的国家”(王礼锡:《在国际援华阵线上·英国汉学家对于中国的同情之声》,见《王礼锡诗文集》,498~503页。)。两度久住中国,有很多中国朋友的鲍威尔教授希望转达英国教育界对于奋斗中的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与赞扬以及反对欧洲军事独裁的坚定决心,而英国教育界对中国的普遍同情,不仅是自发形成,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爱好中国的教授们以感情与正义的鼓荡。(参见王礼锡:《在国际援华阵线上·教授们对援华运动的领导》,见《王礼锡诗文集》,488~490页。)
荷兰的远东研究发端甚早,享有盛名的国际汉学权威刊物《通报》,即由莱顿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与法国汉学家考狄协力创办,因而莱顿被视为巴黎以外的另一欧洲汉学研究中心。到20世纪,荷兰与丹麦、挪威等国组织了东方学联合会。20世纪20年代继任汉学教授的戴闻达(JanJuliusLockwijk Duyvendak)又组织了汉学研究会。戴原为驻华外交官,久住中国。1918年归国,先后任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会员、教授,参与主编《通报》。1926年初访问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吴宓见面,谈中国新文化等问题,并在北京研究国学之中外名流多人参加的燕京华文学校茶会上与苏熙洵一起发表演说。(参见《吴宓日记》,第3册,125、175页。)又于杂志The New Mandarin载文评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卡脱(Thomas Francis Carter)所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In-ventionof Printingin Chinaandits Spread Westward)。(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见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29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戴闻达撰,张荫麟译:《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载《学衡》,第58期(1926年10月)。)1929年太虚访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施乃德的晚餐会上与之相会,同座的还有傅路德、薛维林、芳春熙等人。(参见《太虚法师年谱》,155页。)
1922年,挪威大学哲学教授希尔达从北京到汉口向太虚请晤。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聘请丹麦的吴克德(K.Wulff)博士为通信员。(参见《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十二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1932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Prusek)来华收集中国史资料,曾与鲁迅通信联系,并将鲁迅的《呐喊》译成捷克文,鲁迅还为其撰写了序言。(参见《鲁迅全集》,第14卷,313页。)
瑞典的高本汉是伯希和以外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欧洲汉学家,他与杨树达的通信往来持续数年,互赠论著,交流心得。(参见《积微翁回忆录》,75、90、91、11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其为通信研究员。(参见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除与中国的语言学家关系久密而且广泛外,高氏兼治考古、文学等科,因而与其他专业的学者也有所联系。1947年陈梦家游历欧洲,收集中国青铜器资料,在高本汉的陪同下拜见了酷好中国文物的瑞典国王。(参见赵萝蕤:《忆梦家》,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后者20世纪20年代还是王子时曾来华访问,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多次到中国的新疆等地探险考察,1926年,他又组织中亚远征队欲赴中国西北考察,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反对,北京各学术团体如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皆认为此举系学术侵略,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发表反对宣言。经过多次交涉,与斯文·赫定达成协议,双方合组西北考察团理事会,由周肇祥任主席,斯文·赫定、徐炳昶任考察团长,中方参加者有黄文弼、袁复礼、丁道衡、龚元忠等,到新疆、甘肃、蒙古进行考古。(参见《中西人合组西北考查团》,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6号。)刘复则代表北京大学为常务理事,并担任照看考察团利益的委员会主席,“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所发现的汉简,由刘复、马衡和斯文·赫定三人共同研究。(参见《中华民国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载《国学季刊》,第4卷第4号(1934年)。)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也积极要求派人参与考察,收集有关资料。(参见《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2期(1927年11月27日)。)此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35年。
斯文·赫定为了改善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以便于考察活动,积极为中国作家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先后考虑提名者有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又到清华大学等处做关于所著《藏南》一书的学术报告,与中国学者广泛交往。此公英语纯熟,演讲生动有趣,浦江清甚至以“得一见其面,并亲聆其讲演”为“实可庆幸”之事。(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然而,真正使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界改善关系的是历时八年的西北考察,他不仅与考察团的成员同甘共苦,与理事会的成员时相过从,还结识并与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广泛建立起友好关系,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袁同礼等。1929年3、4月间,由顾颉刚、徐炳昶等人陪同,游览了苏州。他本人对此感慨道:“在1927年春以前,我们与中国学者的个人联系并不多,也看不出任何与他们建立友谊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致的目标,共同的甘苦,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那支考察队,我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在我离开北京的最后四年中,一直与我那些出色的中国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周、王安洪、王安江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76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第三节 从沙俄到苏俄
俄国汉学界与中国渊源甚远,早期来华者多为探险家,以后从事研究者渐多,但仍十分重视探险考古及民族调查。沙俄时代的学术,多由官办,政府设立的亚洲研究会,由俄国学术院、彼得堡大学东亚学科、考古诸协会、地学协会以及俄国政府的宫内、外交、陆军、财政、教育等部各出一名代表组成,会所设于外交部。(参见《露京の亚细亚研究会》,载《史学杂志》,第14编第5号(1903年5月)。)
十月革命后,苏俄因政治军事上与他国对立,一度处于和外界隔绝状态。对内则实行战时共产制,旧学者的财产多被没收,政治权力也被剥夺,一些学者被迫流亡异国。但局势相对稳定后,即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扩大对外联系与交流。列宁等俄共领袖从战略全局出发,重视东方研究,1921年,由列宁提议,在莫斯科成立全俄东方学术研究协会,隶属民族人民委员部,1924年改称全苏东方学术协会,归苏俄中央执委会领导。先后担任全苏东方学术协会会长的帕甫洛维奇(Poflowich)、巴尔托德和副会长、科学院常任书记鄂登堡(S.F.Ol’denburg)与俄共领导关系甚好,颇具影响力,又是内行,懂得按学术规律办事。(参见《ソウエト东洋学について》,载《东亚》,第4卷第9、10号(1931年9、10月);[日]冈田英弘译:《ニコラス·ボツペ自叙传抄》,载《东方学》,第69辑(1985年1月)。)在他们的主持下,苏俄的汉学研究乃至对外交流,尚能正常进行,并有所发展。
1925年,苏俄成立国外文化沟通社,成员包括苏俄主要的科学和文化团体以及沟通国外科学及文化团体关系的政府机关,下设交际、书籍交换、出版、询问、写真等五个部。该社与欧美多数文化及科学团体建立了关系,并通过华俄通讯社致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表示“渴望与中华之文化及科学团体成立同样之关系”,“急欲与中华交换关于文化及科学之书籍及杂志,且极愿以诸君所感兴味之书寄奉,与在中华印行之相等之中文书或英文书相交换”(《研究所国学门通讯》,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763号(1925年9月21日)。)。与此同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接到了类似的信息,王国维复函苏俄科学院,吴宓则答复俄国学术会的公函,并将研究院章程寄往苏俄。(参见《吴宓日记》,第3册,45、58、63页。)
中国方面同样希望与苏俄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沙俄时代的汉学研究虽然相当发达,但因语言等关系,详情为国际汉学界了解甚少。介绍最多的是伯希和与美国学者劳佛。五四运动后,中国普遍关注俄国革命以来的状况,而学术界尤其希望与各国学者建立交流关系,对于苏俄也不例外。1924年,北京大学派陈启修留俄考察,次年又派李仲揆参加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活动。陈启修对苏俄的社会科学及教育政策评价甚高,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史观的哲学》等书为不朽之作,预期将来新兴社会科学的势力必将风靡全世界,写信回北大建议从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哲学等5系的书费中提出500元至1000元,用以购买俄文的社会科学书籍。(参见《陈惺农教授自苏俄来函》,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409号(1924年3月3日)。)两人归国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特开茶话会,请他们演讲苏俄关于东方学术的情形。因二人专业均非中国研究,所了解的情况有限,但也由此获悉第三国际、外交部、东方大学等东方图书馆藏书以及东方协会出版的《新东方》杂志,俄国学术与西欧不同处在于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充足等情况。
苏俄政府为纪念俄国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付出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拨款200万卢布,筹备5个月之久,预计世界各国学者200人到会,加上国内各地的科学家,共约千人。其目的在于让世界知道俄国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建设的时期正在开始,“并且要向世界上表示,苏俄虽是主张劳工专制,然而他们也尊重学术和学者”。不过,欧洲各国学者中有人对此抱怀疑甚至抵制态度,或拒绝赴会,或提前离开,中国学者则较为积极。李仲揆主动与之接洽学术合作与交流事宜,与俄方约定,以伊尔库茨克(Irkutsk)为中俄学术界开会的中心点,苏俄将派人经西伯利亚、蒙古到北京,俄国科学院书记鄂登堡1920年曾率队到中国新疆考察,也计划1926年再次来华,并与中国学术机构交换出版物。(参见《本学门同人欢迎李、陈二教授茶会纪事》、《俄国学者的生活及其他》,均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12期(1925年12月30日);《李仲揆教授在本学门茶话会演说》,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当时苏俄汉学界分为新旧两派,所谓旧派,亦称古典派,主要指继承革命前欧洲汉学传统的学者。他们以俄国旧京彼得堡为中心,重点研究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古代历史文学宗教思想等,同时也关注现代及民间社会。20世纪30年代以前,旧派学者在全苏东方学研究协会中起主导作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主要在旧派学者中进行。而关系最密切的领域,为西夏研究、蒙藏中亚研究、古汉语研究、考古以及佛教研究。
西夏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法、俄、美等国学者相继加入,进展显著。而中国学者治此绝学者,早期只有罗振玉的两个儿子福成、福苌,而且福苌早逝。彼得堡大学教授伊凤阁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后,于1924年上学期通告指导研究题目为“西夏国文字与西夏文化”,包括“1.西夏国之历史文案和古迹。2.西夏国之地位与东方文化之关系。3.西夏国之历史、国语、文字”。欢迎学生报名。后因苏俄外交代表团事务繁忙,延期到6月才以一星期余暇每天来校讲演一小时。(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1389、1411、1472号(1924年1月18日、3月5日、5月17日)。)他还担任国学门歌谣研究会的特别指导,参与讨论以音标注方言歌谣等事。(参见《歌谣研究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406号(1924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