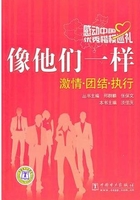水调歌头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唐人李白和宋人苏轼,一个被人称为“诗仙”,一个被人称为“坡仙”。既然都是仙,就有超越平凡庸俗之处,就会凭虚御风,飘逸,高洁,如同高高挂在斗牛之间的一轮清辉,所以,他们都是月的精魂,在每一个喧嚣落尽的夜晚,涤去浮尘,守护着我们心灵深处最后一片宁静和自由。但盈虚者如彼,万川之间又各有风情,那么,李白的月亮和苏轼的月亮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有两首关于月的诗篇,一是李白的《月下独酌》,一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透过那婆娑的斑斓光影,我们能看到两个不同的境界,两种不同的精神历程。
把酒问月,是一个徒劳的追问,但自《春江花月夜》后,就一直缠绕着诗人们,李白和苏轼也不能例外。一个没有答案的追问,实际上只是在暗示着没有起始的月是一个永恒的存在。而一个自明的永恒一再被追问,只能说明诗人内心的不甘和惆怅。“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面对着这片宁静而深邃的月色,每一个发问者都会感受到“永恒沉默”所带来的震撼。月就是圣洁而深沉的彼岸世界,那里有人类对永恒的憧憬。这种无望的憧憬萌发了诗人追问的冲动。
但一个彼岸世界,是如何与现实人生建立联系的呢?李白《把酒问月》诗云:“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月和人类有着遥远的距离,在古人眼里,那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到达的彼岸世界;但月却对人间有着密切的关注,那是一种怜悯和同情的关注,它因为爱莫能助而远远离开,甚至顾影自怜。对于人类来说,月亮是一个孤独的主体。但李白竟然能够坦然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表明月与李白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暗示了李白并非“凡人”。在世俗的世界里,李白感到了一种异类的孤独,“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这种无端而起的孤独,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孤独,它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的领悟和抵触。因此,李白不生活在现实世界,他不是一个凡人,他是另外一个独立而孤傲的主体,骄傲并满怀同情地俯视着芸芸众生。因此,月和人类的疏离关系不能困住李白。月和李白的关系,就是人和影子的关系。月就是李白,他们因共享孤独而成为一体,并从世俗社会中超拔出来,在幽冷空寂的云的深处高蹈。在苏轼的词中,“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也迷蒙着一种浓郁的怅惘,也暗示了月和人类世界那遥不可及的距离,月亮是一个超越此在人生的世界,比起那轮唐朝的月亮来说,它甚至更加冷寂。但苏轼也不是凡人,他在盈和虚之间的左右逢源,他对阴晴圆缺和悲欢离合的坦然和顺从,表明苏轼可以凭着自己通透人生的智慧,超越无常的人生,从而能“遗世独立”,“羽化登仙”。月亮对于苏轼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那凛冽于凡人的月亮,是飘然可及的“天上宫阙”和“琼楼玉宇”。换句话说,月亮对于苏轼是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自在的主体,那是一个理想和超脱的世界,是一个敞开的世界。对于有着无数烦恼和悲凉结局的人生来说,只要你能放弃对此在的执著,那轮明月就是一个遮风避雨的栖息地。
月亮之于李白,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避难所。李白对月亮的向往,是一种主动的意志追求。“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这是一个人唱出的热闹的戏。错综杂沓的光影,既营造出一种迎来送往的幻象,也真实地指示着那旋转舞动着的不过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灵魂。一个人醒着,却刻意为自己演绎着幻觉,那是宁可沉醉,
不愿醒来。在这热闹的孤独中,李白要坚持不懈地演出,没有观众,没有谢幕。这种坚持本身说明,李白明白自己的孤独处境,但却陶醉于这一处境。冷冷的月色就是李白孤芳自赏的光辉。“永结无情游”是一个悖论,“无情”就是拒绝关怀,就是对孤独的坚持,这句诗的意思首先就是对孤独的无条件的认同。正是“无情”,把李白送上邈远的夜空。
对于苏轼而言,月亮既然是一个栖息之所,那么,久居琼楼玉宇就不得不承担着退避的歉疚,所以他能感到“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温润的儒家情怀,把苏轼的根深深扎在现实的土壤中,即使遭到挫折,即使通达人生祸福无常,也不能完全从心灵深处抹去对现实的留恋和希望。苏轼一辈子都在入世和弃世之间辗转反复。他在黄州时曾作《临江仙》云:“长恨此身非我有,有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的坎坷经历和他对人生的洞彻,都使人相信这可能是真的,但第二天,“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急命往揖,则子瞻鼻憨如雷,犹未兴也。”(叶梦得《避署录话》卷二)苏轼不能改变人生的无常,又不能从无常的人生中解脱出来,那么,月亮只能是在自己走投无路时的一个临时避难所,而一旦立足于这清冷的光辉中,那无限的孤寂使他心中又充满了凛凛的寒意。
孤芳自赏是一种内在激情的燃烧,孤独的承受中有一种特别坚韧的人格力量。“皎若飞镜临丹阕,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把酒问月》)就在那无人知晓的云间海上,孤独的花为自己绽放出晶莹的光芒。李白正是凭着坚强的人格,鄙视现实,升华精神,超脱自我。孤芳自赏又是一种冷漠,因为不再期望任何人的理解,更不愿意将自己和世俗的世界混同为一,所以在冷漠中保持一个距离,在无限的空虚中漂泊游荡。杜甫《赠李白》很恰当地描述了李白这种精神面貌:“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自己的精神世界不容他人窥视,就不得不冷漠,在冷漠中展现了一种韧性,让孤独成为一根支柱,守卫着自己的世界。李白的冷漠和拒斥,使我们凡俗之人感到了难堪,这就是“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理由。“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的另一层意思是说:月,不是游伴;对月的认同,不是为了解脱自己的孤寂。没有相互的安慰,只有加倍的同一,月之孤独、明丽,倍增我的孤独、明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李白《峨眉山月歌》)当李白一往深情地追踪着那轮明月的时候,他迷恋的正是月的高洁、孤独、冷漠,或许还有一种深沉的忧郁。他是月,只能在云间海上出没,他不得不孤独。苏轼因为现实的孤独而不能认同现实,要乘风归去,踏上月宫。但“起舞弄清影”需要有超人的毅力和人格力量,我们知道那是可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且,我们又如何能以一种孤独来消除另一种孤独呢?所以遥远的月不过是苏轼悲凉的后院,而不是永恒的家园。对于苏轼来说,应该有现世的解脱之道。当苏轼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比拟人间的悲欢离合时,他首先说明人之存在的不完满是一种无可改变的事实,更为要紧的是,苏轼还希望确证这种不完满具有天然合理性。而后一点,对苏轼的生存态度至关重要。悲欢离合既然是生命中注定要承担的一种本质,那么,忍受也就成为一种美德,而悲欢离合中的思念简直就是幸福,为什么要逃避呢?当苏轼悟出这个道理时,他就有了现实生存的理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所表现的就是一种纠缠和留恋,是一种道德体验。苏轼的月亮离现实人生是如此的贴近,甚至可以说,它只不过是人生世界的一个投影,你可以从中看到孤独,也可以看到希望。所以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你有承担的勇气,就能从孤寂的现实中获得道义的安慰,获得人生的安宁和幸福。
李白的对月和苏轼的对月,皆由自孤独。“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花间”这一非世俗的场所,就表明了李白对不在世的自觉,表明了李白对人世自觉的离弃。所以李白的孤独是对彼岸生命的自觉承担,它不可能在人间找到解决之道。苏轼自然也能理解这种绝世才子的孤独,他的把酒问天也包含着对人类生命的超然反省。但苏轼更关注的是人生境遇中的“悲欢离合”,关注的此在生命的“不应有恨”,所以他的把酒问月是不离现实的在世之问,他的孤独需要在人间寻找现世的解决之道:那就是在确认孤独的合理性过程中实现“自欺”,并在“自欺”中展现道义的力量。都是孤独,都是对月,却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叶嘉莹女士将这两位分别称为“仙而人者”和“人而仙者”,她说李白的仙表现了“绝世天才入世的悲哀”,而苏轼则是“凭藉着几分飘忽的‘仙’气而得到解脱”(《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也许有人觉得苏轼更亲近,也许有人觉得李白更自由,但不论是李白还是苏轼,不论是抗拒还是执著,不论是唐诗还是宋词,那些飘逸游荡的月的精魂,不但体现了对此在生命的爱惜和一往深情,也赋予人类生命本身更为深厚悠远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