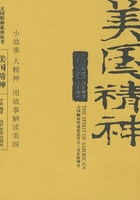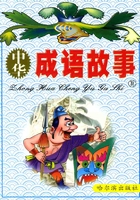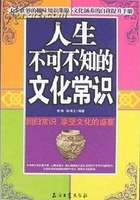因此,理学家对自然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变动不居、灵动活泼、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上。其中春天的景象是最适宜也最常见的选择,理学家特别青睐于、敏感于三春物色的生意盎然张鸣《即物即理即境即心——略论两宋理学家诗歌对物与理的观照把握》,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三辑)。。春天洋溢着浓郁的生意和化机,是天理造化最典型的表征。在理学家诗中“春”本身也就成了“理”的象征,从邵雍《和张子望洛城观花》“造化从来不负人,万般红紫见天真。满城车马空撩乱,未必逢春便得春”邵雍《和张子望洛城观花》,《全宋诗》卷三六六。到胡寅《三月晦和唐人韵诗云……》“一气冲融转大钧,四时舒卷见全身。若云春向晨钟断,须信诗人未识春”胡寅《三月晦和唐人韵诗云……》,《全宋诗》卷一八七四。,再到朱熹《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风光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以贯之,观春要在悟理,春意即象天理。春色春意与天理道心建立起了稳定的象征关系。梅花是三春芳菲之一,而且是春芳独先之象,在展现天意生机上有得天独厚之势。理学这份玄机理趣,可以说梅花是极好的观照对象与意义载体。南宋后期有首著名的僧尼《悟道》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虽然表达的是禅机触发、拈花微笑的禅悟之境,但其寻春究理、即春即理的思路与理学如出一辙。以东风第一枝、花色第一香表禅理玄妙之境,梅花可以说扮演了极其贴切、生动的角色。
理学大家中第一个把梅花与理学本体意义联系起来的是二程。《程氏遗书》:“早梅冬至已前发,方一阳未生,然则发生者何也,其荣其枯,此万物一个阴阳升降大节也。然逐枝自有一个荣枯,分限不齐,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个消长,只是个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穷。”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39页。天地万事万物都处在阴阳交替、变化消长之中,天理就体现在这变化不居的世界万象之中,也是万事万物、千变万化的根本所在。不同的事物所得气机不一,便有了不同的盛衰消长节律,但都是天理发生流转化育的结果。梅花是植物中生机最早的一种,以穷阴之极而发生,由此正可观万物之消息、得天理之流机。在二程这里,梅花只是个比方,是以梅花譬说天理。但先贤一言,殆成圣旨,这一即物究理的态度和格见乾坤消息的认识对理学后来者是一莫大的启发。
在梅花观赏中进一步体现这种精神的是南宋后期的魏了翁。魏了翁有一说法代表了理学家赏梅的基本立场,这就是“傍梅读《易》”魏了翁《十二月九日雪融夜起达旦》,《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在儒学史上,《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包含着儒家世界观的深厚内容。“傍梅读《易》”体现了即梅究“易”,透过梅花物性悟会天理流机,理解儒学本体的思想目的与审美态度。魏了翁《肩吾摘取“傍梅读易”之句以名吾亭,且为诗以发之,用韵答赋》:“三时收功还朔易,百川敛盈归海密。谁将苍龙挂秋汉,宇宙中间卷无迹。人情易感变中化,达者常观消处息。向来未识梅花时,绕溪问讯巡檐索。绝怜玉雪倚横参,又爱青黄弄烟日。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候虫奋地桃李妍,野火烧原葭菼茁。方从阳壮争门出,直待阴穷排闼入。随时作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人官天地命万物,二实五殊根则一。囿形阖辟浑不知,却把真诚作空寂。”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通篇贯注了格物致知、即物究理、即梅究“易”的认识方法。以前赏梅只知香影横斜之美、巡檐索笑之乐,现在发现梅花于穷阴之极却透露着阴阳变化、物极必反之大消息,体现着生生不息的太极根本、天理流机。“梅边认得真消息,往古来今一屈伸。”魏了翁《海潮院领客观梅》,《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天地开阖盈虚,气机阴阳变化,但总归天理仁心,根本实在。如此推究天理本体之义蕴,在咏梅中可谓前无古人,正如罗大经所说,其“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者未之及”《鹤林玉露》甲编卷六。。
梅花所体现的又非笼统的生机变化,而是乾行阳动、欣欣向荣的力量。魏了翁的诗中也不乏这方面的阐发:“惟梅命于阳,清艳照朴蔌。正冬白堆墙,初夏黄绕屋。纯乾禀自高,奚止香百斛。”《汪漕使即梅圃作浮月亭追和古诗余亦补和》,《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天寒万木脱,岁宴群动弭。西郊有孤芳,独唤春事起。幽光耿参月,清艳明野水。欲开未开时,似语不语意。或疑春较迟,的尚霜蕊。谁知春风心,浑在阿堵里。”魏了翁《西郊访梅……》,《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这里的着眼点与周、邵、程、朱等理学先贤观花赏春一样,特别抉发的是欣欣向荣之生机气象。
这种生意在理学的阐说中有着世界观和人生观有机统一的思想意蕴。《周易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两宋理学家就此也多有发挥,并引申出生意即仁,仁即其性的心性论和人生观。程颢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程氏遗书》卷一一,《二程集》第120页。“生”是天地之初始,也是万物之本源。在这里“生”与“性”、“仁”、“天地之大德”即天理是同一的东西。儒家君子贵在洞彻万物之本源,参合宇宙之初心,而具天地之大德。由此出发,观梅也就不是一般的物色之赏心悦目,而要从中体会生意、觉识仁心。这是君子人格、圣贤气象的体现。
上述几方面的理识,在南宋后期理学家的品梅咏梅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发挥。如:“对梅欲着语,当在梅之外。君看龙蛇蛰,中有江河沛。其元阳复雷,其真岁寒桧。于梅观此妙,眼力怜湛辈。无能根本求,仅为色香嗜。一元无识者,孤真可知矣……犹疑转语下,未为梅之至。愿闻第一义,更作向上计……”杜知仁《和范孙闲行溪西得梅数花韵》,《全宋诗》卷二七七一。“一日微阳积一分,看看积得一阳成。夜来迸出梅花里,天地初心只是生。”方夔《梅花五绝》其二,《富山遗稿》卷一○。“岁寒叶落尽,微见天地心。阳和一点力,生意满故林。”蒲寿宬《梅阳郡斋铁庵梅花五首》其五,《心泉学诗稿》卷二。“天地变化,其机不停。玄阴既极,万物用贞。由剥而复,微阳始生。苍山冱寒,幽花独馨。玉质朗耀,铁枝峥嵘。皓雪让洁,素月并清。得气之先,斯仁之萌。自华而实,斯仁之成。”陈深《梅山铭》,《宁极斋稿》。“天地生意,无间容息,当其已闭塞之后,未棣通之前,于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谓仁,则夫倡天地之仁者,盖自梅始。”文天祥《萧氏梅亭记》,《文山集》卷一二。“端如仁者心,洒落万物先。浑无一点累,表里俱彻然。”陈淳《丙辰十月见梅同感其韵再赋》,《北溪大全集》卷一。“雅如哲君子,觉在群蒙先。”陈淳《丁未十月见梅一点》,《北溪大全集》卷一。“吾知乃翁好梅意,不独区区为名第。霜飙天地惨无色,谁得东皇第一义。惟梅气禀独超卓,首送春风入书幄。对之心地悟理学,此是天民尹先觉。”陈鉴之《寄题长溪杨耻斋梅楼,楼乃其先世读书之所》,《全宋诗》卷三○二八。梅花是天地初心、仁德之始,仁人志士、士夫君子则因芳色体天理见道心,就生意寓仁德证觉悟。这正是周、程诸子“观造化之妙”在梅花审美认识上的体现和推演,无论是价值意旨,还是形象认识上都可谓是别具只眼,别开生面。北宋中期以来的咏梅,对梅花花期致意颇多,由早春移至严冬,凸显梅花凌寒冒雪,以象征人格坚贞。而理学家则又由梅花冬荣转视为春色,由着意被动耐寒转而强调自觉回春,由推求意志气节转而验视理性觉悟,由意格的孤峭寂寥转化为君子圣贤的仁物平和。这在主观上虽然不免于理学概念化思维的方式和道德名教的目的,但也洋溢着仁者乐物的情感意趣,客观上更是牢牢抓住了梅花为春色先气、阳和新景的物色特征,凸现了梅花芳菲先发、管领春风的自然生机。这一美感在林逋以来的人格寄托中是逐渐淡出的,现在重新得到重视。与以往视梅为春色仅仅着意其时序占早、物色开新、花光鲜妍又有所不同,理学家的着眼点是“物理”,是气机,是“天地初心”、“乾坤消息”,认其为梅花的天理独赋、仁心先知,正所谓“吟客谩能工水月,先儒曾此识乾坤”萧立之《再为梅赋》,《全宋诗》卷三二八七。。同是着眼其辞旧迎新、阳和报春,理学家更侧重于展现一气先颖、生意敷布、化育万物的生机气象:“一气独先天下春,两三花占十分清。冰霜不隔阳和力,半点机缄妙化生。”于石《早梅》,《全宋诗》卷三六七七。“玉箫吹彻北楼寒,野月峥嵘动万山。一夜霜清不成梦,起来春意满人间。”黄铢《梅花》,《全宋诗》卷二三九七。“万物正摇落,梅花独可人。空中三五点,天地便精神。”王柏《题梅》,《鲁斋集》卷三。不是“一枝”,而是“一气”。不是“春色”,而是“阳和”。不是溪头篱角,而是“天下人间”。立足于宇宙本体认识的高度,认识上透进一层,视境感受也极其阔大充沛。梅花展现了阳和开新、生意勃发、气机充盈流布的博大气象。这是一般春色之咏望尘莫及的,更是以往“东风第一枝”指喻金榜高第、“春风得意”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体现的与道为一、道贯古今、德配天地、化成天下的精神抱负(以往德性境界多由花之芬芳来象征,所谓德馨流芳,这里主要是由春气生意来展示道成德化之境)统一于入宋以来即物究理、品格象征的根本趋势,其道义价值之取向、思想境界之阔大,在林逋以来的梅花品格象征中也可谓是更有进地。理学家使梅花上升为崇高又复博大的德性和时运象征,这是理学家的特殊贡献参见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第161-169页。。
上述是宋代的情况,入元后这方面的认识更为流行和深入,可以说成了梅花审美中比较普遍的价值体认。如:“太素钟其质,太和全其气。回生意于万物之始,涵造化于一阳之际。风霜同其缟洁,江山助其灵异。罗浮庾岭,乃其寓也,金鼎玉堂,乃其遇也。东封大夫、淇园君子,乃其平生之契也。宋广平赋、林和靖诗,乌足以仿佛其一二也。独慕夫昔之人,因此以见太极,谓问诸先天之伏羲氏也。”李继本《题郑彦文所藏墨梅》,《一山文集》卷九。“诗书暨春秋,于梅著其实。舍实多言花,后世富篇什。花耿冰雪面,实蕴乾坤仁。独步众芳中,允矣庵中人。勿徒于其花,名媲花御史。实调相君鼎,天下归仁里。”陈栎《题梅庵图》,《定宇集》卷一六。比宋人更进一步的,元人咏梅赋梅中多秉经义加以阐发,如元末明初的谢肃《梅花庄记》:“夫梅有花而有实者也。昔商高宗命说辅德,而比之和羮,斯谓实欤。六朝以来词赋所称,幽芬绝艳,斯谓花欤。且花与实一本而异名也,实以用而可贵,花以色而可尚。尚花今也,贵实古也。古之贵实者既见于经,而今之尚花者其词赋足拟于经乎哉。如其未足以拟乎经,请以经言喻之矣:夫隆冬之月,草木不蕃,而独存生意,粲焉以芳者,非若有恒性乎?静而山溪,喧而城郭,玉堂馆舍无适不宜者,非素其位而行乎?蛮烟瘴雾,雨暗风霾,而纯白之姿迥岀尘表者,非涅而不缁乎?得履之幽贞也,故能独守以正,而不乱于物焉。得贲之白贲也,故能不假文饰而自然光莹焉。盖所谓昭明有融者也,盖所谓皜皜乎不可尚已者也。合众美为全德,其花之圣者乎,而视夫高宗所用之实何愧,是则实犹花也,花犹实也,而名庄之意得矣。”谢肃《密庵集》卷五。虽然观点多仍宋人老调,但拟于经言义理,全面理会和阐释梅花的纯全德性之美,具体细致处值得注意。另元人中有专就经言义理演为《梅花百咏》者,张之翰《题刘洪父〈梅花百咏〉后》:“近世梅诗自逋仙两句以降,大率不过雕花刻蕊而已,未有如刘教谕洪父以太极六经梅等题演为百咏者,究其用意,盖欲内外透彻,彼此混融,梅即道,道即梅。故说性说理处,不患其不幽且深。”张之翰《题刘洪父〈梅花百咏〉后》,《西岩集》卷一八。不仅是文学中,绘画中也出现了《傍梅读易》、《梅花太极》一类题目。如元黄镇成《题〈梅花太极图〉》序:“太极在物物中,不独梅也。而梅开冬熟夏,得六阳之纯气,华得受采之全色,实得曲直之正味,是梅为植物之尤异者,中明绘为十图,以见太极之初终。”卫宗武《秋声集》卷四。在墨梅画法中也出现了以太极阴阳象数来论述画梅取象构图的现象吴太素《松斋梅谱》卷一。。这些都进一步显示了儒家理学思想的深入影响。
在元人作品中,梅花更多地与《易经》、太极、太极图、阴阳八卦等理论学说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既有理学象数的内容,同时也不乏道教、阴阳五行家的术数,梅花成了诸家共用的太极阴阳学说的象征。王义山《寄题黄静斋》:“静中乐处是琴书,此乐输君二美俱。明镜无尘佛关捩,内丹养火夜工夫。梅花窗下参同契,翠草庭前太极图。探得黄庭真诀了,不须更看养生符。”《稼村类稿》卷一。这里所写的梅花太极之类功夫,就不是理学贤人君子的道德境界,而是佛道之士的道术修养。明代出现了几种名叫《梅花数》、《观梅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三“五行”。的卜筮书,“梅花数”也成了阴阳方术的重要派别潘季驯《报获盗犯杨青山疏》,《潘司空奏疏》卷七。。这种情况想必由来已久,元代已经开始。从二程举梅说《易》义论天理,经过理学家的宣传,梅花的独特生机已经成了广泛使用的道术玄理的象征。这是宋元之际梅花审美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