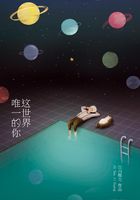引言
《本际经》卷五《证实品》中,仙人孟德然说:“伏闻神尊所说道德尊经,白日升天之道,是无为之上法,名为大乘之经。”老君曰:“道德之要,非中仙所知。子等曈曚下仙,安得闻此?”“吾乃愚人淳淳,不知谁子;直以无状之状,有物混成,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太上以吾狂直恍惚,赐垂委任。”原文分别出自《老子·二十章》:“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淳淳即“沌沌”,形容混沌无知的样子。《老子·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吾受太上重任,方以大乘至法,化度八方人民贵庶,乃至一切神鬼,三涂地狱蝖飞蠕动之类。”扶桑太帝曰:“至如神人(按:此处“神人”当指老君,即老子)所弘大功德,本不简秽贱,唯善是与,然则大无不苞,细无不入,所以神人弘此法,故和光同尘,匠成万物也。下仙虽复垢重,量非大慈所弃。”
在和孟德然的问答中,老君阐释了“道”的内涵,“道本来非是有为无为、亦有为亦无为,非有为非无为之法。经中所说有为无为等,此是圣人权便治病之言,何有空实”?“且为善之内自有多途,或作有见,或作无见。作有见者,便谓道是有为之法。作无见者,便谓道是无为之法。然一切万物,山河石壁,现有形碍,至人体解,犹尚不见是有是无,何况于道而得是有是无耶?道若是有,有则不关于无;道若是无,无则不关于有。如此隔碍,何名为道?乃至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法,是妄生分别。”
《证实品》着重神化了《道德经》和老子,赋予老子、《道德经》、“道”以道教的神学色彩,明确老子是“老君”,乃“道”之子,在神仙谱系中阶位仅次于“太上”;《道德经》是“白日升天之道,无为之上法,名为大乘之经”。
《本际经·证实品》这段文字表明,道教的宗教哲学承袭了道家学说,道教哲学的道体论思想发轫于先秦道家的“道”本体思维传统。
§§§第一节从道家之“道”到道教之“道”
一“道论”与本体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是最早把“道”作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提出并使用的。老子以辩证否定的语言形式对于“道”的本体性存在进行描述的同时,强调说明道不是什么,而不明示道是什么。在《老子》中唯一一处对“道”进行正面描述的是“道者万物之奥”(《老子·六十二章》)。表面上好像具有了“是”的内涵,但宾语的模糊、不确定性,照样抵消了“是什么”的功能。故河上公注:“‘奥’,藏也。道为万物之藏,无所不容也。”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241页,中华书局,1997年。既然无法予以正面的、确切的定义,那么,“道”不属于任何有形、可感知的个别具体事物范畴,而体现了对形而上的普遍性和无形的高度抽象概括。
在老子的视域中,“道”并不只是一个哲学范畴,而指涉了宇宙万物与主观、客观世界的本质;涵盖了包括体道功夫、得道境界和在体道与证道的过程中,对“道”直观体悟的“悟道”呈现。
“道”并非西方哲学本体论所指的,同现象对立、隔绝的实体概念、范畴。“道”是一种体验的实存,任何分析的语言、文字都是对道有限的解读,而无法言诠它的无限意蕴。道家哲学体系中,缺少西方哲学话语权下所谓的外向型的认知思维模式,而主要表现为内省型的意向思维。强调在自我情感体验和直觉观照中与自然冥合,在精神世界的内省中不断完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道教继承了这种如果从西方哲学视域审视,外部整体模糊的直觉思维,既把个体之我当作认识主体又作为认识客体,建立了一套性命双修的宗教“神学”理论。
这种在西方哲学本体论看来可能是非理性、非逻辑的认识方法,姑且称之为内省体验法。但语言、文字也是必不可少的传道媒介,即使“不可说”,其实也是一种无言之说。关键在于“得意忘言”,通过“有限”的载体领悟无限的“道意”。如同顾欢所云:“明道则忘言,存言则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说。”“知者不言,言而不言,实在忘言。言者不知,目击未当,况言议乎?体道绝待、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216页,《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第五十六章注,巴蜀书社,2001年。
然而,在对“道”的诠释过程和方法、手段上,又离不开现代学术通用的哲学诠释话语和参照体系。
黑格尔站在西方哲学的视角审视“道”,认识到“道”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同时也意识到“它的意思是很不明确的。中国人的文字,由于他的文法结构,有许多的困难,特别这些对象,由于它们本身抽象和不确定的性质,更是难于表达”,“因为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联接词,没有格位的变化……所以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24—13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黑格尔对“道”的理解、解释基本采用哲学可以语言、文字定义的方法界定老子之“道论”。所以他最终结论,“在纯粹抽象的本质中,除了只在一个肯定的形式下表示那同一的否定外,即毫无表示。假若哲学不能超出上面那样的表现,哲学仍是停在初级的阶段”。“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
黑格尔对哲学价值的评判一律以西方哲学本体论为标准,首先要求确立从逻辑上规定的范畴,然后形成由范畴的逻辑规定性推论得出的命题而构成的原理。如同黑格尔自己所说:“揭示出理念发展的一种方式,亦即揭示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的、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哲学自身的课题和任务。”同上,第33页。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评论是立足于西方哲学价值本位、本体论立场的典型代表。
海德格尔哲学代表了传统的本体论哲学解体以后西方哲学的新追求,意味着对本体论的超越和克服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4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海德格尔认为,以本质主义“绝对观念”的方法不足以解释道,道不是对象化的绝对,而是存在于人们的体悟与行为活动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道可以是给予一切出路的路,是我们对于理性、思想、意义、逻各斯按其严格的本性所要说出的东西加以思索的能力的源泉。也许富有思想性的言说和种种不可思议中之不可思议者就深藏在‘道路’、道这个词中,只要我们把这些名称恢复到它们所没有说出的地方,只要能这样,允许它们不说出来。也许今日方法之统治作用的神秘能力也是;而且确实是卓著地出于这样的事实;且不论其效果,方法最终只不过是一股伟大而隐蔽着的流中流溢出来的,这股流推动着一切,给一切东西以出路。一切皆道路。”转引自俞宣孟:《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第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被黑格尔排除在外的东方思想以及中国思想,包括禅宗思想,正因为在西方哲学传统之外,在海德格尔看来,距离思想和哲学的源头更近,它们是有希望用来解决以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中的新问题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作为为世界开辟道路之道说的语言,是一切法则中的法则。”“作为自我持留居用着的大道,是一切法则中的法则。”“除此之外无他。”“人们根本上不再只有一种希腊方式运思大道居有。”“甚至(希腊人)自己都从未思及这种语言的存在,甚至赫拉克利特也是如此。”转引自(德)莱因哈德·梅依著,张志强译《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第67—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海德格尔理解和解释的“道”,从中国哲学的视角看来无疑更富于“理性”,甚或可称其为“理解之同情”。
综合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观点,我们既承认老子之“道”所具有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普遍性(本体)这一特点,但“道”又不是完全对象化的绝对,而是同时存在于人们的觉悟与体证的行为创造活动之中需要说明的是,运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模式来诠释中国哲学,这在方法论上无疑将面临来自合法性的挑战。对此欲加辩护,也就自然牵涉到何谓“本体论”,以及中国哲学有无“本体论”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惯用的“本体论”一词,原是“ontology”的译名。这和“哲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等语汇一样,都是始自20世纪中西哲学交流、会通中的“舶来品”。从语言学词汇分析的角度来看,“ontology”主要由“ont”和“logy”两部分语素组成。在希腊文中,前者是系动词的名词形式,也可表示“存在”,相当于英文的“being”;后者作为学科名后缀,与“logos”的意义联系紧密。所以,笼统地讲,“ontology”就是“按照逻辑法则构建的关于存在之为存在(being as being)的学说”。根据侧重点的不同,中文则可以翻译为“本体论”、“存在论”或“万有论”。“ontology”的译名各异,既反映出其作为哲学概念定义的丰富内涵,也引发了中国学术界针对不同理解、解释的众说纷纭。自20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上述译名未能如实反映出原文与系词之间的内在关联理应废弃,“ontology”当改译“是论”为宜。另外,在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的鼻祖当属古希腊的柏拉图。而第一位给本体论下定义的,却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有’以及‘有’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18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从本质上说,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原理系统(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纯粹概念的推论”。显而易见,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殊途且不同归。当然,“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史上自近代以来也发生了多种不同的变化。如: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美国哲学家蒯因理解为何物存在问题的讨论、豪尔(David L.Hall)的本体论则“是对事物最基本的特征的研究”等,他们似乎有以将“存在”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的共同倾向(同上,第21—22页)。与传统的本体论有诸多不同之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界的一些学者也在使用“本体论”。但是,运用西方哲学“本体论”模式,在诠释中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由于不同语境的差异所带来的“水土不服”。或者在引用“本体论”一词之前,没有予以明确的界定,就会造成把中国哲学传统一以贯之的“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车裂”。在中西方各自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内部,以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的分别来定义一门学科,原是合理、充分的,但若将视线转入中西哲学比较领域,那么单纯的形式区分显然不足以解决问题。从研究对象的形式层面来看,西方的“ontology”以系词“是”(being)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作为研究范畴。而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接下)。
(接上)的“本体论”则直接以“性与天道”作为考察对象,两者之间如同南辕北辙。但就其同样追寻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本体根据而言,两者又有其相似之处以及沟通的可能性。
从研究方法的形式层面来看,西方的“ontology”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构建出一套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体系。而中国的“本体论”,则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更多地采用直观归纳方法,试图从生活实践中体悟到、提升出世界的本真状态,两者的研究方法风格迥异。但就其思维习惯摆脱了原始宗教的交感模式、力求发挥理性自身力量以确认世界之真相而言,则又有相同之处。“诸子”虽不讲究形式的逻辑,但却同样遵循理性的原则。本体论问题亦当如是观之,中国哲学虽无形式的本体论体系,但有相似的本体论思维。
二中国哲学语境中的“道”
《易传·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与其说老子之“道论”是哲学的“本体论”,毋宁说是中国哲学特质的“形而上学”。
从中西哲学对“形而上学”不同理解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及老子“道论”的某些特质。首先:作为西方哲学专有名词的翻译术语“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在哲学中其逐渐衍生为一门研究“超越者”、“第一者”、“存在之所以存在”等的专门领域。而在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如影随形,还存在着它的背反——“形而下”,这在西方哲学的视域中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西方的形而上学是一个纯粹哲学概念的世界,是一片超越了“经验”的领域。用语言概念进行的思维活动,一般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逻辑要求的概念必须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确定性、稳定性是其他逻辑形式得以成立的基础。中国的形而上学从未脱离人们对于所能感知到的经验世界的切身体悟,它是通过日常经验的升华,无限接近“道”之境界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体验者个体的性质和体验的深浅程度,缺乏统一衡量的标准,所以也就造成了“道”与“体道”、“悟道”、“证道”、“得道”,同样难以获得普遍一致的评判和表述。再次:西方的形而上学以抽象的范畴为起点,并逐渐推出其他范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却意味着“无形”、“未行”、“无名”、“无体”等。孔颖达说:“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周易正义》卷七,第71页。《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3页,中华书局影印,1979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视域中“道”、“形而上”、“形而下”三者之间联系紧密的关系。《周易》作为老子之学的思想渊源之一,而“《易传·系辞》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论十翼非孔子作》,《古史辨》第三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所以,孔颖达的说法同样适用于理解和解释老子之“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