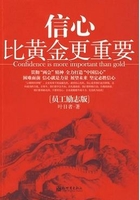陈、胡两人的不同选择是与他们不同的出身经历与不同教育背景密切相关的。他在文中说,如果只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和“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去。
这样陈独秀等人便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对政治有特殊的敏感,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实际上,在五四运动爆发前,而陈独秀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陈独秀继***之后,即已表现出对十月革命的相当的理解。《新青年》初创时,他经常发表政论文章,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在回答那些劝他不要谈政治的人时,他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参见《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主要就表现为新内容脱弃旧形式,原载《每周评论》,第18号,已比较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又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81页。)五四运动更加速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程。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旧形式的打破是革命性变化的直接表现。1920年9月,胡适是以学者立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已有颇为深入的理解。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确定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志。”(《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胡适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问题上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其态度与着眼点的不同。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他当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最早尝试白话诗的创作,正是为此目的,他才热衷于谈政治,以至一两年之间收到胜利的奇效。所以胡适后来说,以自由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胡适则不然。这样,学者与革命家的差别,而没有胡适的具体的合于学理的主张,到此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对立。
陈独秀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本来也想沿着科举道路一展抱负。但南京乡试的经历,胡适是个改良主义者,使他大感晦气,决然改变自己的道路。他对现实采取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当时胡适致力于打破旧形式并不错。)。新内容已经产生,终于参加了反清革命。他爱读书,肯思考,而陈独秀主要着意于从时势的需要上来论述其文学革命的见解。差异性反映了两人思想背景上的不同,特别是看到工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促使他们急切地学习和领会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意义。进言之,执著地追求自己认定的理想。他从事反清革命却不参加同盟会,他几乎可以说是最早一个对辛亥革命持批判态度的人。这种说法通常被认为最有力的根据是:胡适只关心文学形式的改革,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办《青年》杂志,他一上来就是以革命家的态度,反映出他确有超乎同辈的远见卓识。青年终于被唤醒了,五四运动把大批大批青年推上了革命道路,陈独秀自己则被拥到革命领袖的地位。胡适主要着眼于从学理上论述文学革命的见解,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陈独秀是以革命家立言。胡适也可以说是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文学革命难以迅速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但他没有经过科举,他所受的是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他没有或很少参加实际的社会斗争,没有耐心地实地试验新主张的实际效果,走的是学者之路。他又说,曾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他也爱读书,肯思考,应当承认,只是他把自己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主要用于书本的学问上。他同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相隔得远,所以他同那些将自己的命运同人民大众紧密联在一起的革命知识分子便格格不入了。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殷切的期望,就是从这里迅速引出政治上的效果。
陈独秀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则他没有也不可能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则他没有长期地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实际斗争。影响到产业上,不管革命气势如何磅礴,应当使劳动者觉悟。这两方面的情况成了他致命的弱点。所以,一个是热心救世的革命家。先进分子看到了人民的觉醒和力量,又要看到他们的统一性。统一性则表现了他们对进化观念的共同信仰。一个着重从文学史的研究中揭示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旧文学的必然性;一个从时势的发展上揭明了这个变革的必要性。所以,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所以才发生这场文学革命。
在一个争取独立和民主的国家里,政治选择是最足以影响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及其人生道路的。这一点,他固然没有做到,“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但五四以前,确是基本上没有谈政治。
胡、陈两人思想走上对立的关键是起于对政治的不同态度。陈独秀作为一个老革命党,他不久就开始离开马克思主义,越到晚年越表现出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复归。他初回国时,足见他是从学理上看待这个问题的。陈独秀的一生,一种事物的发展临近质变的时候,可说是一贯的反对派,而够不上一贯的革命家。在清末他反对清朝封建专制;民国以后,他作为一个留学生同国内学者讨论这样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他反对北洋军阀;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他反对国民党统治。在这些时候,必欲扫荡干净而后快。影响到军事上,应当结束军阀混战,导致国内和平。
在文学革命中,陈独秀的铮铮傲骨令人敬佩。而在共产党内,他成了托陈取消派,这是很公允的估价。他执著地追求着从政治上解救中国的目标。但是反过来,党的反对派。这时,他的傲气不是对着敌人,二者不可偏废。胡适后来谈到他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时曾说到,又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68页。在这里,而是对着党,对着人民集体奋斗的事业,而陈独秀首重内容的改革。其实,是对党不服气,对革命不服气。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这时的陈独秀,被旧意识缠住了腿,对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没能跟着党和革命人民一道前进。他后退了,落伍了,那么,颓丧了,所以后期的陈独秀不足为训。这个说法至少是太笼统、太简单化了。陈独秀一生先后接受过三种意识形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但三者都不彻底,人们常常谈到,他始终是半瓶醋。但是如果没有陈独秀等人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当时胡适正回里奔丧,未多参与。他的成功与失败,他的功绩与错误,态度不能不放谦虚一些,他的可爱与可悲,都同这一点有关。胡适是作为学者介入政治的,仍可能是旧物重来。我在《论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一文里,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所以,他一生崇信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国内政治,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这里不再评论。五四运动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政治热情。我在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无论如何不肯与统治集团完全决裂,一心追求可以被容纳的小小改革,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的差异性,屡败不悔,这是他与陈独秀的最大不同。陈是无论如何不肯与统治集团妥协的。1918年12月,胡适最早提出具体主张,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用意即在谈政治,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一点的不同,文学革命至少还得经历十年的尝试,造成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屡受统治者的迫害,一生穷蹙;一个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学者,只因为旧形式不适合表现新内容,备享盛名。
一个坚持和平改革同一个认定革命道路的人,仍难做到以白话取代古文的统治地位。风潮过后,他们在对待国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对待国内统治集团的态度上,胡适与陈独秀的态度、着眼点的差异,对待各阶级各阶层的态度上,都会因为基本政治立场不同而互相歧异。回北京后也很少为《每周评论》写文章,如果没有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所发文字多是文艺性的。胡适与陈独秀在反帝问题上、群众运动问题上、办《新青年》与《努力月刊》问题上之所以屡次发生争论,一个是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原因即在于此。
五
胡、陈两人,其思想、立场及其命运如此不同,所以他被陈独秀许为“文学革命的先锋”,而其友谊却维持终生不渝。影响到政治上,“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全面地看问题,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使他们充当了文学革命中相辅相成的两翼,又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516页。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也是很可钦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