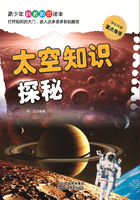蘇氏兄弟不能踐約,可是相關作品卻受到後世歡迎,甚至給予其他詩人深遠的影響。例如,黃庭堅在紹聖二年(1095)作《和答元明黔南贈别》云:
萬里相看忘逆旅,三聲清涙落離觴。朝雲往日攀天夢,夜雨何時對榻涼。急雪脊令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歸舟天際常回首,從此頻書慰斷腸。
通過月亮想到空間相隔的對方,這類作品很多。如劉宋鮑照《翫月城西門廨中》可以説是早期的例子:
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未映東北墀,娟娟似娥眉。黃庭堅本來以蘇軾的高徒聞名於世,所以很有可能受到直接的影響。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
主人公想像與相隔千里的對方共有同一的月亮。還有白居易《自河南經亂,關内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云:
時難年荒世業空,本章與詠月詩進行比較。自古以來人們把對相隔對方的親愛之情寄託於月亮。一看天空的月亮就想像他方的丈夫、朋友或者家人也一定看這個月亮;或者在某些古蹟賞月而追憶曾經在同地賞月的古人。前者對於空間相隔的對方,弟兄羇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由此可知,從相當早的時期起人們就認為“夜雨對牀”是兄弟之間的親愛表現。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因戰亂而與兄妹四散的白居易遙望月亮,就想像現在相隔的兄妹也在各地看明月而懷抱望鄉之情,這正和自己的懷抱一樣。白居易確信彼此懷抱同一的感情,可以説比鮑照詩更强烈意識到彼此間的紐帶。
也有詩人通過月亮想到時間相隔的對方。例如李白詠出了《月下獨酌》等很多與月亮有關的作品,其《夜泊牛渚懷古》云:
作者單位: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
人多以夜雨對牀,為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
李白在牛渚欣賞著月亮而想起古人——曾經在此地賞月的謝尚將軍。晉人袁宏朗誦自己的詩歌時,幸虧遇見謝尚受到他的知遇。李白跟袁宏相比而嘆:自己的才華並不亞於袁宏,可是沒有人像謝尚那樣重視自己。
通過對這兩種模式的分析,可以指出月亮所具有的兩種普遍性。首先,不管在什麽地方都可能享受月光的清景,因此月亮具有空間的普遍性。其次,自太古到遙遠將來持續的存在,也具有時間的普遍性。對於具有空間、時間的普遍性的月亮,古來人們獲得了某些想法:月亮使相離的兩人心情聯繫起來。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
跟普遍存在的月亮比較起來,雨只是限定的現象。下雨的範圍比月亮發光的範圍更狹小,持續時間也比月亮這一個衛星的悠久性更短暫。加之限於雨夜來説,它具有在1-2所舉的特點:天空佈滿烏雲而一片漆黑,只能聽到雨聲的淒涼空間。所以在唐代的“聞雨”詩中,夜雨帶來詩人和外界隔絶的閉鎖感,恰好是跟月亮完全相反的存在。雨本來具有空間、時間的限定性,並且夜雨還有獨自的閉鎖性,換言之雨夜是由限定性與閉鎖性構成的空間。身處其中,如果無人共度,2000年2月)闡明了通過月亮將自己和對方相結合的文學表現。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此外,就會懷抱絶望的孤獨感,如果跟心心相印的對方共享,則釀成極其親密的氣氛。
月亮是普遍性的存在,所以沒有詩人賦予獨特的意義。對此,具有閉鎖性、限定性的夜雨是由於韋應物的私人經驗纔被發現的親密空間,到了蘇氏兄弟纔被賦予了特别意義。兄弟賦予了特定的對方、特定的場景(致仕閒居之後纔能實現的情況)兩個雙重的限定,結果“夜雨對牀”成為特别的紐帶,昇華為兄弟獨特的親密意象。鑒於蘇軾向其他人用“夜雨對牀”時並不用做將來的經驗,並且蘇轍對其他人的贈答詩中沒有“夜雨對牀”的表現,由此可知兄弟“夜雨對牀”本來具有的排他性、限定性。
(二)月亮和“夜雨對牀”的差異之二:是否限於即景的描寫
①《金史》卷六〇《交聘表》上。娥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基於這樣的想法,連綿出現大量因月亮而想到對方的作品。“以月亮為頂點的三角形(月亮——自己——對方)”可由空間軸或時間軸得以構成。詩人視點的基準處於現在,然後自由意識到過去或將來。但是,有的詩儘管沒有描寫現在的情景如何仍然能想像將來的場景。。如上所述,兄弟從未希望在將來與别人實現“夜雨對牀”,對於蘇軾來説“夜雨對牀”本來是特别面向蘇轍的親愛表現,以其限定性來確立兄弟獨特的情境,以長久的時間使其情境倍加堅固,結果獲得了不必真正面對夜雨也能想到將來的新穎境地。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進不知退,踐此禍機。
白居易“夜雨對牀”詩也通過現在的雨想到與對方共有的歡樂。但是有的“夜雨對牀”詩,不必真正面對夜雨,就是説詩中沒有夜雨描寫而仍能懷念對方。在1-1所舉的唐詩中,鄭谷和韋莊都將“夜雨對牀”作為過去的經驗。對於兩人來説,“夜雨對牀”不僅是單純的雨夜情景而且是美好過去的象徵,因此不問現在的情況如何通過懷念相隔的對方就想起來過去的特定情景。
如上所説,與唐代詩人不一樣,蘇氏兄弟將“夜雨對牀”作為理想將來的象徵,所以有的詩實際置身於雨景而懷念他們的約定:如⑥《感舊詩》序寫兄弟在雨夜的懷遠驛讀韋詩而約定將來;⑤《初秋》“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與ⅳ《五月一日》“對牀貪聽連宵雨”也具有通過現在的夜雨聯想到將來的複式構成,可以説現在的夜雨促使兄弟遙想將來。……今人但知為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這是限於蘇軾詩的特徵,3個作品符合條件:一是本文開頭提到的①《辛丑十一月》;一是第2章所舉的《書出局詩》題跋;還有一個是元豐二年(1079)烏臺詩案時,在獄中自度不能避免死去的蘇軾請獄卒秘密地送給蘇轍的訣别詩歌,④《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都可通過賞月來表達思念日本學者興膳宏《唐詩中月亮的三種形象——王維、李賀、李商隱》(《立命館文學》No.563,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其一。當時蘇軾44歲,距約定“夜雨對牀”時已經過了18年的歲月。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第一句雖然説“萬物春”其實沒有描寫具體的場景,從而也無從知道有沒有下雨。
到了南宋“夜雨對牀”似乎被確定為來源於蘇氏兄弟的衆所周知的親愛表現。第六句“他時夜雨”絶不是對將來雨景的單純想像,對於蘇氏兄弟來説,還包含著超越情景本身的意義。在將來的雨夜蘇轍孤獨地聽著雨聲,這跟他們素所描寫的理想將來“夜雨對牀”的情景是完全相反的。蘇軾不顧自己的危險卻悲嘆對方孤獨的將來,在此正體現他們深厚的親愛感情。
蘇氏兄弟“夜雨對牀”的獨特性來源於自己的經驗即在雨夜讀韋詩的行為,心裏已經紮根了,可以説兄弟倆由於原體驗創出了他們“夜雨對牀”的意境。加之,此後遇到的雨中離别(蘇軾詩②、③和蘇轍ⅰ)使他們對於踐“夜雨對牀”之約懷抱著更深刻强烈的願望。這樣,無論現在有沒有雨,獄中的蘇軾從已經不能踐約的境地想像對方將在下雨的晚上孤獨的樣子而悲嘆。重要的是蘇軾所詠的“他時夜雨”只有蘇轍纔能了解其本心,因為蘇軾曾經約定而盼望將來在一起的對方就是蘇轍。壓倒了韋應物的典故,人們認為“夜雨對牀”是蘇氏兄弟的獨創其實詩人們並不經常以“夜雨對牀”為關於兄弟的描寫,例如:陳與義《謹次十七叔去鄭詩韻,二章以寄家叔一章以自詠》其一:“對牀夜雨平生約,話舊應驚歲月遷”;楊萬里《送孫從之司業持節湖南二首》其二:“朝陽鳴鳳只今見,夜雨對牀何日尋”。
四、結束語
當時黃庭堅前往左遷之地黔州(四川)時,其兄長大臨字元明陪弟弟一直同行,黃庭堅把再會之念寄託於“夜雨何時對榻涼”句。但有一個强烈的思念縈迴於蘇軾的心裏:對於已經不能再會的蘇轍殷切的親情
燈燼不挑垂暗蕊,爐灰重撥尚餘薰。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這兩首詩所贈的對方都不是兄弟。雷州别駕(筆者注:即蘇轍)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
然而由於政治形勢的急速轉變,元符三年(1100)蘇軾遇赦渡海北歸並獲得了居住之自由。於是兄弟倆準備踐“夜雨對牀”之約。在尺牘中,蘇轍建議一起定居許昌(河南),蘇軾也高興地同意孔凡禮撰《蘇轍年譜》建中靖國元年二月條:“二十二日,(蘇轍)作簡,託黃寔(字師是)寄與兄軾,勸軾歸潁昌相聚”。蘇軾回信云:“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賚來二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昌,行有日矣。儘管如此,王楙仍不能忽視蘇氏兄弟的深遠影響。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文集》卷六〇《與子由書十首》其八)。蘇軾同意弟弟的提案,卻考慮元祐舊臣還是被排擠的現狀,為了避禍建議住在離京師更遠的常州。可是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蘇軾還沒和蘇轍再會就得病逝世。這樣,實現“夜雨對牀”的機會永遠沒有了。然後蘇轍在許昌過杜門謝客的生活結束一生(政和二年·1112)。蘇軾逝世之後,蘇轍為兄長寫作了幾篇墓碑銘和祭文,其中一篇回憶約定“夜雨對牀”的過去,對即將實現卻最終不能踐約的蘇軾表示深厚的哀弔之情《欒城後集》卷二〇《再祭亡兄端明文》云:“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牀,後勿有違。要之“夜雨對牀”漸漸超越蘇氏兄弟的私人範圍,給予後人深刻的影響和感動。欲復斯言,後者對於時間相隔的對方,而天奪之”。
無容置疑這句是基於蘇氏兄弟的“夜雨對牀”詠出的。高雲鵬《蘇軾詩詞中的月意象研究》(《中國蘇軾研究》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也説:“和其他詩人一樣,一生沉浮宦海、漂泊異鄉的蘇軾也把月意象作為相思、思鄉主題作品的核心意象”。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對這樣的認識南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一〇反駁云:
對比月亮意象,“夜雨對牀”的表達還有另外的特點。詩人詠月亮時,必須首先遇到現在的月亮纔想到對方,就是説為了想到對方不可缺乏月亮的存在。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為然,於朋友亦然。上面所舉的李白詩屬於這類。
蘇氏兄弟二人終生盼望的“夜雨對牀”之約,終究不能實現。兄弟最後詠出的“夜雨對牀”詩均是元祐年間(1086-1093)之作,即在朝受重用的時期。紹聖元年(1094)以後,他們被貶謫到嶺南、海南之間,為了進一步明確兄弟“夜雨對牀”的特點,雖然兄弟跟過去一樣互相傳送詩歌,卻完全沒有“夜雨對牀”的表達。代之而起的是月亮意象的使用。紹聖四年(1097)身處海南的蘇軾送給貶在雷州(廣東)的蘇轍《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集》卷四一),這裏没有提到再会之念卻期待月光结合两人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