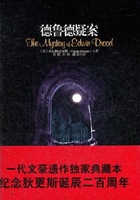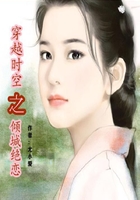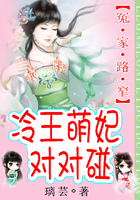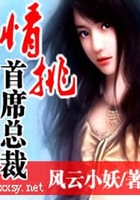引言
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汉代,在西汉时成为专门的学术。汉代经学是整个中国经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宋学而言,蒙文通对汉代经学作了更多的研究,也把汉学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就其重视程度而言,超过宋学。就汉学内部而言,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评价比古文经学更高,亦对今、古文学的流弊提出批评。一般说,与先秦孔孟儒学相比,孔孟思想比汉学更为重要。所以他提出破弃今、古文家法,上追晚周秦儒学之旨。但也不尽然,蒙文通对汉学的评价,也发生着变化,前后不尽一致,或相矛盾,使人不易理解。虽在论经学与诸子学关系时,对西汉今文经学评价较高,有时甚至把它作为东汉以下思想的根本,不仅是子史之中心,而且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认为汉之新儒学所论有优于孟、荀处,但对西汉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董仲舒却评价不高,时时提出批评。这体现出蒙文通经学思想不同于他人的特点,值得认真研究,以发掘、探究其学术之旨。
(一)今文经学
蒙文通把今、古文之分作为汉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舍此则不足以言汉学。他说:“言汉学而不知今古文之别者,不足以语汉学;言今古文而不知归本礼制者,不足以语今古文。”而今、古文区分的依据,蒙文通继承其师廖平,以礼制为本。关于以礼制分判今、古文学这一师说中的重要创见,蒙文通阐述说:“井研廖师,长于《春秋》,善说礼制,一屏琐末之事不屑究,而独探其大源,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认为廖平于今、古文经学的诸多分歧和差异中,独探大源,抓住了今、古二学在礼制上的不同这一基本差异,即今文经学以《王制》为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纲,并肯定廖平著《今古学考》一书,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之论,将其与顾炎武对于古音的研究、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的考辨并列为“三大发明”,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时,乃一屏碎末支离之学不屑究,发愤于《春秋》,遂得悟于礼制,《今古学考》成,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若示诸掌,汉师家法,秩然不紊。盖其识卓,其断审,视刘、宋以降,游谈而不知其要者,固倜乎其有辨也。故其书初出,论者比之亭林顾氏之于古音,潜邱阎氏之于《古文尚书》,为三大发明。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经学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专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则详对经书文字的训诂;西汉今文经学重师法,东汉古文经学重家法等。对此,廖平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今、古学之分,师说、训诂亦其大端。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刘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盖今学力求浅近,如孔安国之‘隶古定’、太史公之易经字是也。古学则好易难字以求古,如《周礼》与《仪礼》古文是也。古学无师承,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本无师说,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师说多得本源实义;训诂则望文生训,铢称寸两,多乖实义。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惠、戴以来,多落小学窠臼。”认为之所以“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是因为西汉今文经学“有授”,所以“师说详明”;而古文经学“出于臆造”,所以“无师说”。与此相关,今文经学力求浅近,以今文隶写古字;而古文经学则由于无师承,其古文又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以说字见长,这即是廖平所分析的今文经学重师说,古文经学重训诂的原因。不特如此,廖平更提出了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这确是他的一大创见。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力将此说发扬推广,扩大其影响。他推阐其师说云:
今古文之争,起于汉代,亦烈于汉代。清世经学,以汉学为徽帜,搜讨师说,寻研家法,遂亦不能不有今古文之辨。……本师井研廖季平先生初治《穀梁》,有见于文句、礼制为治《春秋》两大纲,后乃知《穀梁》之说与《王制》相通,以为《王制》者孔氏删经自订一家之制、一王之法,与曲园俞氏之说出门合辙。然俞氏惟证之《春秋》,廖师则推之一切今文家说而皆准。又推明古文家立说悉用《周官》,《周官》之制,反于《王制》,求之《五经异义》、《白虎通义》而义益显。又知郑康成遍注群经,兼取今古,而家法始乱。推阐至是,然后今古立说异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两汉家法,若振裘之挈领,划若江河,皎若日星。故仪征刘左庵师称廖师为“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洞彻汉师经例,自魏晋以来未之有也”。
指出其师廖平从治《春秋穀梁传》入手,洞见文句、礼制为治《春秋》的两大纲,以后又认识到《穀梁》中所言礼制与《王制》相通,故以为《王制》乃孔子删经损益因革而自订的一家之制、一王之法,此与清经学家俞樾之说有相合之处,但俞樾之说只取证于《春秋》,而廖氏师说则在一切今文家说中都能得到印证。可见廖平师说更胜人一筹。蒙文通并指出:“这不能不承认是近代经学上的重大发现。虽然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改变,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蒙文通对廖平师说的继承和阐发,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廖平经学影响的作用。
在以礼制分今古的基础上,蒙文通对今文经学作了探讨。他说:“盖西汉初年只齐、鲁之争,齐、鲁合而后《王制》出,有今文。刘歆以来始有今古之争,而齐、鲁之争息。”认为西汉初年只有齐学、鲁学之争,齐、鲁学合后《王制》出,而有了今文学。到刘歆出来以后,才开始有今、古文学之争,这时齐学、鲁学之争息。也就是说,在蒙文通看来,组成今文学的齐、鲁之学在西汉初相互争论,以后合而有今文学的出现,而古文学则是在刘歆时才有,有了古文学,才有了今、古文学之间的争论。
蒙文通还以是否得到皇帝的支持作为今文学区别于古文学的一个依据。他说:“便知道皇帝爱的就立在学官。……今文的说法全是随着皇帝为转移。皇帝不爱的书,便不能立博士,博士也就排斥他们。他们的学问只好传授于民间,也不必跟着皇帝说,后来便于博士的学问分成两派,便分了个今文、古文的差别。简切说来,便是跟着皇帝的一派就叫做今文,皇帝不爱的一派便叫古文。”一种学术能否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和支持,这是一个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统治者对学术的取舍取决于该学术满足统治者政治统治的程度以及社会的需要、社会对该学术的接受程度等诸种因素。蒙文通认定今文学“全是随着皇帝为转移”,恐不如此。在汉代今文学中,除有适应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的成分外,也有不少对统治者权力加以限制的成分,对这些学问,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肯定不爱。所以蒙文通以皇帝爱或不爱作为划分今、古文学的一个依据,恐有些简单化。因为即使在古文学里,也有借统治者力量以提高自己地位的内容和因素,为此,他们也为统治者政治治理的合理性作了论证。
以儒学发展的眼光看,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已远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由此对今文学提出批评,把儒学微丧的原因归罪于汉代经学,认为西汉今文经学兴起,使得儒学衰微。他说:“至汉武立学校之官,利禄之路开,章句起而儒者之术一变而为经生之业。……自儒学渐变而为经学,洙泗之业,由发展变而为停滞,由哲学而进于宗教,由文明而进于文化。孟、荀之道熄,而梁邱、夏侯之说张。若以儒言,则今文已远于孟、荀之绪,又况于古文之学哉!自今文之学起而儒以微。”认为梁丘贺、大小夏侯等今文说的兴起,导致了“孟、荀之道熄”,而今文博士官由汉武帝所立,由此开学者利禄之途,使得儒学变为经学,带来了儒学发展的停滞以至衰微。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之弊,正是由汉武帝开启之,造成了“章句滋而大道熄”。他说: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江公不如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张禹先事王阳,后事庸生,采获所安,号《张侯论》。盖皆承浮丽之风,采获牵引,期于饰说应敌,自是章句滋而大道熄也。……浮华无用之言,至是而大炽。刘歆、班固、杨终所讥为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者,皆谓此也。徐防、樊准亦谓其妄生穿凿,竞论浮丽,则至东京而今文之弊极矣。班固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讫于元始百余年,传业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盖利禄之路然也。”其弊皆自武帝启之,必谓汉人之学为皆笃信谨守者,未必然也。
指出西汉今文学家如董仲舒、夏侯建、夏侯胜、张禹等人,其学被立于学官,为博士,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由此而带来了流弊。董仲舒与江公在当时同治《春秋》,因江公口呐,不善辩,武帝使江公与董仲舒议,江公不如董仲舒,故董氏取胜于江公,于是武帝尊董仲舒所治的《公羊》学,而江公所治《穀梁》未被采纳。其实一种学说能否被采纳,主要是看其学说的思想内涵,有无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而并不取决于其是否能言善辩。董仲舒之学以儒家为主,结合阴阳五行说,注重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发挥和宣传《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强调改制、易正朔、作新王,主张行儒术,讲仁政,缓和社会矛盾。这些思想被汉武帝采纳,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然今文学盛行后,盛极而衰,经生训诂解经,走向繁琐,“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班固认为,这是利禄之路使然。又与阴阳、灾异之说和谶纬相结合,并存在着某些对经书的穿凿附会,一度导致经学的混乱,于是有古文经学的出现。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流弊提出批评,认为浮华无用之言,至是而大炽。并引刘歆、班固、杨终等人所言,讥其为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者,并称其是妄生穿凿,竞论浮丽,至东汉后,今文学的流弊发展到极点。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批评,客观的指出了其流弊所在。
除批评今文学的流弊外,到后来蒙文通也肯定了今文经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甚至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这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论及。
(二)古文经学
在西汉末以前,并无所谓今、古文之争的问题。到了西汉末,刘歆才提出“古文”一词。与“今文”相对应,于是有了今、古文经学之争。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汉盛行的古文经学产生于西汉末年,其创始人为刘歆(?—23)。他自称了解《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典的来历,即秘府所藏的古文经典出自于孔壁,由孔安国献于朝廷,藏于秘府,而刘歆校书时发现了它们,将其传出,并了解它们在民间的传授情况。又整理《左传》,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奏请把《周官》列之于经,改为《周礼》,并列为礼经。刘歆于西汉末哀帝时,要求把《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太常博士即今文博士的反对,未被朝廷采纳。后王莽执政时,古文经学得到支持,得立于学官,不久即废。但古文经学在不断流行发展,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杜林、卫宏、郑兴、郑众、贾逵、许慎、马融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古文经学大师。
廖平则认为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认为东汉初以前十四博士皆为今学,同祖《王制》,道一风同,并无古文经学可言;而古文经学所宗的《周礼》专条,全出刘歆之伪。刘歆作伪的目的,在学术上是为了报复经学博士,在政治上则是为迎合王莽篡汉。康有为亦以为古文经学的典籍《周礼》、《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等均是刘歆作伪的伪经,刘歆作伪是为了用经义助王莽新朝篡汉,故将自己批评刘歆的著作名为《新学伪经考》。该书不守经师家法,而以考证、辨伪见长,其见解主要包括:一是认为所有古文经典,甚至古文本身,皆属伪作;二是认为无论古经、古字之伪,皆出于刘歆一人;三是认为刘歆伪学,首推《周官》,盖以“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四是认为刘歆伪作群经,《左传》开其先河,继之以《乐经》、《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费氏易》与《论语》、《孝经》为最晚出,又以古经出于古文,自必先伪造古文。以为古文经学的典籍《周礼》、《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等均是刘歆作伪的伪经,刘歆作伪是为了用经义助王莽新朝篡汉,古文经,则是刘歆为“佐莽篡汉”而作的“伪经”。
近代的今文家都说古文是刘歆伪造的,何至如此!不过古文到了刘歆,他想把古文振兴起来,他借着王莽的势力,把古文经传通通立在博士,征聘天下通知佚经古记的人,前后数千,让他们都住中央廷中去讨论,《莽传》说他“将令正乖谬、壹异同”。是王莽也照石渠的办法做过。他的结果,后人无从知,大概是古文家占胜利。古文与王莽、刘歆的关系不过是如此,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这一部分书,从汉武帝起,已经在经师间讨论了,但是当时何以会完全排斥不用,其中也自有个原故。凡是《周官》、《左传》、《毛诗》、《古文尚书》这部分书,都在河间献王那里。……《佚书》、《佚礼》、《周官》、《左氏》、《雅乐》等,献王一齐都向武帝进献去,武帝把这几种书訾议了一阵子,便一齐藏之内府,不要人讲。刘歆说《佚礼》、《佚书》、《左传》“皆藏于秘府,伏而未发”。马融说《周官》“伏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礼乐志》说《雅乐》“天子下大乐,惟以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