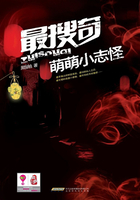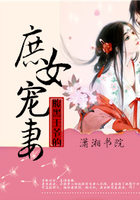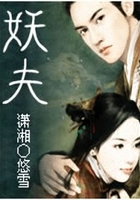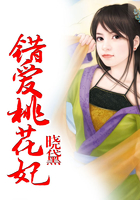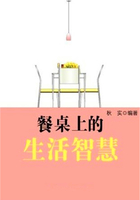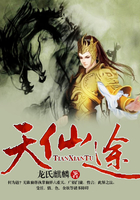所谓“理一分殊”就是一理摄万理,犹如一月之散而表现为江河湖海之万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万理归于一理,犹如江湖河海的万月其本乃是天上的一月。从一个太极散而为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又由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归本于一个太极。这就是“理一分殊”。这个理学名词源于程颐称赞张载《西铭》时的话。程颐称张载这篇作品是“明理一而分殊”,并说“万物皆是一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理”的体现。朱熹对此加以发展,提出了其“理一分殊”思想,认为“理一”是本,因后天所禀受的气有所差异,故万事万物呈现出不同,而有了各自的性,各自的理。这种万殊之性、万殊之理兼绝对、抽象的“天理”与具体的“物之则”的理于一身。朱熹主张通过格物和存敬、切己的工夫来认识万物之理和人伦之理,最终以成圣人。
蒙文通认为,李侗的一本之理与万殊之理皆为性,一本是抽象的“天理”,“分殊”则是日常践履,其理更多的是从伦理意义上说,故其主张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走的是内向型的工夫论;而朱熹则走内外兼修的方法,因为朱熹认为人的认识对象还包括具体事物的物理。蒙文通认为,孟子提出“形色,天性也”,是“有进于子思”,其践形尽则,只是从道德主体上加强道德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忽略了日常的生活实践;李侗看到了现实生活中道德践履的必要性,进而提出“理会分殊”的观点,朱熹则加以发挥,将内心体认工夫与外部的格物工夫相结合,以求达到真正的天人一体。陆象山虽然主张向内用力、切己自反、剥落物欲、改过迁善,实际也是强调从日用中下工夫以成圣,佛家亦强调通过做善事以积德而成佛,因此,蒙文通说:“率性尽性之学,自子思、孟子、延平、程、朱是一致的。象山所谓于人情世事物理上用功,亦是如此。释家说要于事上观,亦是此理。”虽然,子思、孟子讲心不讲“理”,但言性,而性与理相通,故与延平、程、朱讲理是一致的,都是讲尽性。陆象山讲心性一物,心即理,故也是讲性;而佛家的心性之学虽别于儒家,但在强调工夫上则是一致的。因此,蒙文通赞同程朱的“性即理”之说。
理虽有先验性的一面,但理并不是空或无。蒙文通说:“若把理也看成空无,非所敢知也。延平言理会分殊,阳明言感寂,是儒家正义,所谓性也。”他反对道家、佛家认理为空、为无的观点。认为无论是物之理,还是天理,都永不停息,都是通过具体的事事物物、具体的人伦道德行为得以体现。他认为,理与物是形上与形下之别,是抽象与具体的不同,而不是佛家、道家所谓的虚实、有无之异。他认为,把儒家讲的“理”与“空”、“无”等同起来,一切就会成为虚的,而无法认识。南宋理学家李延平提出了“理会分殊”命题,说,“理一”(太极)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并指出万物虽则同具一理,但所禀受之气有“秀”、“偏”之别。明代的王阳明在阐述其致良知说的时候指出,寂然不动是心之体,感而遂通是心之用。因心与理为一,心即理,故其言“寂”、言“感”都是就心而言,就理而言,换句话说,寂感皆理。蒙文通认为,延平说的理与阳明说的理(感、寂)均是具有儒家伦理意义的天理,兼有物理之义和伦理之义,即兼实与虚为一身;而非如佛学、道家的空无之理、空无之性。
2.“本心纯然天理”、理(道)在心中
在理与心的关系中,蒙文通认为“本心纯然天理”,理与心(指本心)均为本体范畴。他赞同理在心中的说法。他说:“在物之理,而气或不循于理,惟心知之,此理在心之说也。”作为物之理、气之则的理,是知觉之心的认识对象。这就是所谓的“理在心”之说,是就认识的主、客体而言的。但蒙文通的“心”还具有本体性含义。他赞成二程对心的描述。二程认为,“人心莫不有知”、“心无形体”、“心无限量”、“心,生道也”,其心既是认识主体,也是宇宙本体。蒙文通说:“心无定所,知则普于一切。以知言,则万物皆在知中,宇宙悉括于知内,物物还他本然之理而知至也。性体明,物各付物,安有不循理者。”心具知觉思虑功能,能够认识物之理,也能认识物之道,即所谓的“理在心”、“道在心”之说;虽然心无形体,但其认知能力却无所不在,故“宇宙万物悉括于知内”。“知”是心之“知”,“知即心也”。“万物皆在知中”,即万物皆在心中。因此,在蒙文通的心与理的关系中,心既是认识主体,也是宇宙本体。要见天理,就要存心,“随时体认天理即存之之事”。
蒙文通也对心与道的关系作了一个说明。在朱熹及陆九渊的哲学里,“道”与“理”都具范畴的同一性,而阳明则简化为“心即道,道即天”、“道即是良知”。蒙文通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心存则道存,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道非亡也,人不省耳”。“心存则手舞足蹈无非天则”。随时使虚灵之心不松懈,一切就合乎理,一切就合于心。这是蒙文通基于心本论,对心与理、心与道关系的阐述。
3.理、气不离
对于理气关系,蒙文通也有大量论述。一方面,蒙文通赞成罗钦顺有关理依于气、理气有别的观点。他说:“罗整庵说: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则不是。此语最精。”罗钦顺不同意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他力主“理只是气之理”、“理”非气外之理,同时指出理、气有差异,“理须就气上认得,然认气为理,便不是”,但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其理气关系说是建立在他的气本论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蒙文通认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合而言之为性。“不可认气为理,但理亦须于气上见。形上形下不可分,合而言之性也。”他认为理、气有别,但又不可分,两者是形上与形下的关系,其中,理为形上之本体,气为形下之物,两者合而言之则为性,换句话说,性是兼互不相离的气与气之理而言,性是合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于一体。“寂者气之静,感者气之动,一感一寂,各有个自然之则,所谓理也。理岂外于气哉?”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表现于气的或静或动,或寂或感,其动静、寂感各有其规律,这些规律就是理,因此,理不外于气,是气之理。“理不离气,但不可着在气上看”。“理只在气上见,但不可执气为理。气无不动,理亦可于动上见,但理自非动非静。”理不离气,但理不是气,两者是形上与形下之关系。
蒙文通认为将理、气、知三位一体,合而言之,称作性。他说:“有物有则,理者气之理,理传于气;气违于理而心自知之,而知传于理;知亦气之知也;三者一而已也,合而言之性也,无极而太极也。”“气也,理也,知也,合而言之性也。”这里的“理”,是事物的普遍法则和规律,它不离于气,通过气来体现,或者说,理寓于气中,即所谓的“传于气”;昭昭明明的心自然能够判断气是循理还是违理,人的主观认识就是通过知传给理的;知亦是精微之气。因为,中国古人认为,气有精微与粗疏之分,其中,粗疏之气构成万物,而精微之气具有知觉性,有时被说成心,有时被说成知,但均为气之灵觉部分。知是心之知,又是气之知,心亦气,故蒙文通认为,气、理、知三者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这里可以看出,蒙文通受气学派的影响很大,不过,还没有达到变理本为气本的程度。
蒙文通对朱子的“理与气既不相离,亦不相杂”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其言美矣”。他说:“以不杂言,则气之万殊而善恶分、万事出,理固未尝与之俱往,是理冥然于物之外。理与物离,则理者惟一顽空之境,不足以应万变而为善恶之衡、是非之准。舍即物穷理以为制事之方,则其道又奚由哉!”其不杂是指本体之理区别于形下之气,但此理离不开(气)物,否则,理就无所依托。“以理、气为离,则理冥然无适于用,不足以应事,自必以‘理、气不离’之说济之。”理、气分二的话,则“理”就成了绝对抽象的理。而宋明儒之所以言理,目的是用来“应事”,成为人的道德准则,指导道德践履。因此,必然以“理、气不离”来补救。
然而,朱子“毕竟偏于理、气离之说也,此朱学末流‘即凡天下之物而穷之’”,是“蔽不可掩”。蒙文通说:“无适而非气,即无适而非理,气机鼓荡流行,皆天理也。气万殊而理亦万殊,无气外之理,亦无理外之气,无往而离理,即无往而非善,此阳明之旨而‘满街尧舜’之说所由生也。”他认为,互相依存的理、气合而言之为性,性为善,天理亦善,而天理无所不在,故“善”人无所不在,自然就是“满街尧舜”了。“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彻:曰格物穷理,曰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二家之说,皆欲以明善恶之源、求是非之准,而其蔽较然若斯,要即源于理、气之说,推而致之,有必至之势。”蒙文通认为,理气不相离与不相杂为一义之两端,偏于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失误。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就是因此而分别走上了即物穷理与满街尧舜两个极端。他指出,“理、气本不相离,而心则有存有失。于心放时而言理、气不杂,则已离理、气为二,反有疑于本体,朱子此处应有商量。理、气二则不得不即物穷理而学以支离。于心之放而犹执理、气不离,则不得不认为满街皆尧、舜,然则百姓不知、庶民去之之谓何?而学以鲁莽。要之,思则得之,思不失其本心,所谓思诚,正尽性践形之要也。”一句话,理不离于气,关键是存心,使昭昭明明之本心不松懈,就能兼顾理气不杂与不离,从而也就避免出现阳明后学和朱子后学的两个弊端。
4.人欲、天理的对立与统一,“人欲即天理”
理欲问题在宋明时期是一主要讨论话题。理学家大多认为,天理、人欲是两相对立的,主张“存天理,去(灭)人欲”。程朱学派的集大成者——朱熹,和气学家张载一样,看到了人之为人的客观物质生理欲求的合理性,说“即使圣人也有此欲”,并把心分为人心与道心,与人欲、天理相对应。人心是道心的一部分,道心主导人心,相应的,人欲是天理的一部分,天理主宰人欲。人欲也有合理的一面,就此而言,可以说人欲即天理;但当人的欲望超过一定的度时,则转化成与天理完全对立的私欲。因此,朱熹所要去的“人欲”,实际上指私欲,指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人欲”。心学派的观点略微不同。阳明坚持程颐的“人心即人欲”之说,而不认为“人心”与“人欲”有区别。按照程、朱之说,虽然对“人心”的解释及评价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人心”与“道心”,其所指是不同的。大致而言,“道心”指义理之心,“人心”指物欲之心。但是按照阳明之说,“人心”与“道心”虽然是对立的,但所指是相同的,即良知而已,只因正与不正而有天理、人欲之别。阳明虽看到了天理、人欲的对立,但更多的时候主张以心来控制人欲。
蒙文通也注意到了人欲与天理的对立。他说:“廓然大公。人己共同之理,所谓公也;人物共通之理,所谓公也。否即人欲也。”“克己复礼。己者,人欲也;克去人欲,还他天理。己与他对,由他本体,我何与焉,所谓未始有回也。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所谓未始有回也。心齐坐忘之学,克己尽之也。”蒙文通认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是公与私、他与己的对立。所谓“坐忘”,是指深入存想意境,浑忘周围环境及自身,即所谓“无天、无地、无人、无我”之意境,也即《庄子》中,颜回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境界。所谓“克己复礼”,指通过克去私欲,使得天理流行,一切皆还他本色,自然也是一种无我、无他、无天、无人的境界了。将儒家的“克己复礼”同道家的“心齐坐忘”相比拟,也是蒙文通兼治儒、释、道,调和三教思想的一个体现。
蒙文通吸收了陆、王的观点,主张由清明之本心来区分天理和人欲。他说:“象山言收拾精神。须收拾整顿一翻,翦除枝叶,心自纯一清明,自然理欲分晓,见可透澈。”陆象山认为,心具有先天的知善知恶的能力,只要有虚灵之心,就自然能分晓万事万物是否合乎天理。也就是说,只要“先立乎其大”,即立其本心,并存其本心,使本心不松懈,就能分辨出那些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妄”、“过或不及”等“人欲”并加以防止。蒙文通认为,最佳方法就是“寡欲”,一切还他本然状态。“知爱知敬是本体,自能孝,自能弟,纯是天理,只要搜求人欲到底。”“养心莫善于寡欲,气清理明,善日充而日长。”有了知爱知敬的本性,有了昭昭明明的本心,在家自然能孝顺父母,爱护兄弟,这是天理,是人之本色。为了还人之本色,就必须存心、养心,令此心不松懈,使自己的欲望不超过一定的度,即所谓的“寡欲”。显然,这里的“寡欲”与佛教所说的“寡欲”迥然不同。这是儒家的“寡欲”,并非要无视人的自然生命需求。
同时,蒙文通又接受了王夫之、陈确等人有关理欲关系的理论,认为“人欲即天理”。王、陈等从理不离气推导出天理不离人欲、无人欲无以见天理等等结论。王夫之说:“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离欲而别为理,其唯释氏为然。”陈确则明确地说:“确尝谓,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也。”“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蒙文通赞同王夫之、陈确等肯定人欲,强调离人欲即无天理的观点,他说:“理者气之理,人欲即天理。庶民去之,固不得以此为理气不杂之证。庶民日用,亦莫非天理;好好色,恶恶臭,何莫非天理;甘食甘饮,亦天理也;呼尔蹴尔则不屑不顾,亦天理也。呼蹴而受之,则欲所不欲,然后非天理。此真太空中一点尘埃,此前此后皆气也,亦理也;诚意则拭此一点尘埃也。养得浩然之气,则此一点尘何由而生。此一点尘自是人欲关头,所谓不动心者即不动此不屑不顾之心耳,养气者即养此不屑不顾之气也。”他认为,理为气之理,天理是人欲的一部分,在一定的范围内,人欲即天理。
蒙文通赞同孟子将性区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说法。孟子认为,“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的性是自然属性,这是人与动物都具有的属性;“仁、义、礼、智”等是社会属性,是人所特有的。蒙文通将“饮食男女”的七情六欲视为天理,而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欲”比作那“一点尘埃”,认为存心即是养气,即是使人欲不超出那个度,变成天理的对立面。他指出,“说人欲即天理,却无害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即是克己复礼。情即性,是从本体说;性其情,无以小害大,是从工夫说。若疑情即性之说,则于本体不澈,若不指出本心,无集义改过之工,以为有身即有道,则是猖狂妄行而不自觉,混人、道为一心,则于本体更混。”蒙文通主张将性与情区分开来,认为性与情是体与用、大与小的关系。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亦与其类似。性、天理是本体,但此本体要通过人欲、情表现出来,故说人欲即天理,情即性;以性来控制、把握情,即是性其情;以天理主导人欲,才能分清人心与道心,才能明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