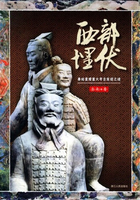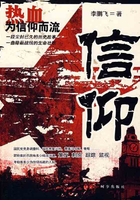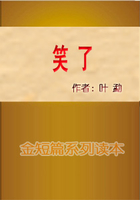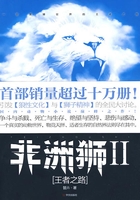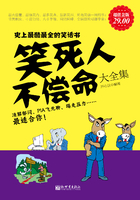引言
蒙文通的理学著作,虽多为读书札记、笺注心得,但从中我们仍可发现他的理学思想脉络。笔者拟透过蒙文通先生读宋明儒书的心得,透过其只言片语,对其理学范畴的涵义作一番探讨。
(一)关于“心”
蒙文通对“心”这一范畴的论述较多,既涉及孟子之“本心”,也谈到了“心”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如:心与性、心与气、心与理、心与知、心与物,等等。
1.心本论的宇宙观
在宇宙观上,蒙文通以孟子的“本心”为本。他说:“夫本心者,道之所由生,舍是心而道乌乎本?此率天下而祸仁义之说也。”孟子以本心明性善,蒙文通把本心作为道产生的根据和根源。他认为,若无本心,儒家的仁义之说就无以依存,万事万物就失去了“统帅”。而本心无所不在,“浑身皆是本心,知爱知敬是本心,手容重,足容恭,亦是本心。非特一身是本心,草木山川亦是本心,才一事一物不当,本心即知之,应即改之” 。本心是体,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皆是本心的体现,为用。故万事万物一旦出现“异常”,本心都能知晓,并加以改正。因为,“知即心也,近而身心,远而人物,其是非得失皆在知中,舍非而从是,在一念耳”。心有知觉、灵明功能,具有先天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四肢百体,莫不有知,而统于一心。心果何在乎?则四肢百体无乎不在。岂惟四肢百体,即万物亦莫不有知,草木竹石各有生意,即其知也”。万物皆有知,万物皆有心,皆是心(知)的体现。故蒙文通说:“心无定所,知则普于一切。以知言,则万物皆在知中,宇宙悉括于知内,物物还他本然之理而知致也。”正由于心具有知觉思虑功能、虚寂灵明功能,所以心虽然没有规定的所在,仍能“容纳”宇宙万物及万物之理。“本心之好恶,即所以为受是辞非之准,而性善之源也”。因此,蒙文通的“心”(指本心)为宇宙本体。
蒙文通将阳明的“良知”说纳入其评述范围。阳明曾有“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阳明以天地万物皆以人的良知为根据,从而建立了良知的至高无上原则。蒙文通认为,阳明的“良知”与本心、意、性等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他说:“孟子本心之说与单言心者自别。良知亦然。本心、良知,即意也。意即性,性无不善,故曰尽性;意无不善,故曰诚意;诚意乃所以正心。”因此,良知、意、本心,也是本体,如性一样,是至善无恶的。
事事依着本心,就能践形尽性,成为圣人。因为本心原来是无私无欲的,原来是无欠无缺的,饿了便会吃饭,渴了便会饮水,冷了便要穿衣;耳朵本来是很灵敏的,眼睛本来是很明亮的,见了恶臭自然厌恶,见了好的东西自然喜欢,在家自然会孝顺老人、爱护兄弟,这是人类的本能,不那样做人是不会心安的。这不是遏抑得住、勉强得来的,是从他本心上自然而然的发出来的。因此,蒙文通说:“只事事依着本心,一直做去,便是践形尽性的圣人。”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通这里强调了“事事”和“一直”两个词语。圣、愚之别也体现在这里。因为,愚夫愚妇和圣人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本能之心,有这个本心。然而,愚夫愚妇之所以愚,就在于:不像圣人那样一丝一毫都依着本心,一点不敢瞒他,不比圣人对他的本心是自满、自足、自慊,没有一毫自歉的,只需不自欺便了。蒙文通说:“这个本心,便是天命之性;事事依着本心去做,便是率性之道。”“心本寂然不动,万象起灭,感而遂通,心之寂然之体,未始有动,视听语默、手舞足蹈,一切自然,无非本色,何曾有圣凡之别。”因为圣凡都具备这个寂然不动之心,即有了这个本体,所以一切都是此心体的流行发用,故无不合理,无不是本色,当然就不存在差别了。但这只是就本体而言。圣、愚都有这个本心,故都可率性,但只有圣人才能事事、时时依着本心,即时时存心,所以只有圣人才是尽性。也就是说,虽然愚夫愚妇与圣人有着同样的本体(即本性、本心),但由于工夫的不同,致使两者在率性的程度上产生差异,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地尽性。
2.心与性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甚至可说是整个儒学讨论的主要话题。在心性相互关系上,有两种情况:心、性一元说和心、性二元说,区别在于是把心性视为一物还是认为心性有别。心、性一元说,指心性为一,心即性,性即心,主体即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即主体,二者没有区别,心性一物,均为宇宙本体。心学派理学家多赞同此说。宋明理学的心性一元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二程开其先,经张栻的过渡,陆九渊、杨简的发展,吴澄的传播,至王阳明成为心性一元说的集大成者。阳明说:“心也、性也、天也,一也。”他强调“心即性,性即理”,反对将心性分二,从而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极致。心、性二元说,指心性有别,不是一物,否定道德理性与主体直接同一,可细分为道德理性客体化和道德理性绝对化两种观点。前者以张载、罗钦顺、吴廷翰等为代表,后者以胡宏、朱熹为代表,性成为超越主、客体之上的绝对观念,代表主体的心和代表客体的气均从属于性。
一方面,蒙文通赞成心、性一元论。他说:“孟子言本心,本心即性,故曰心即性也。”这是对宋明儒的心性一元说的发挥。程颐指出:“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认为心、性与命三位一体,都是“道”的不同称谓,是相通为一的。阳明则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良知说,将良知规定为“心之本体”,规定为“天命之性”,以良知分别联系心、理与性,并相互沟通。这样心范畴所有的内涵,良知范畴也都具有。而意为心中之心,即本心。因此,在阳明处,本心、意、良知、性为一。蒙文通赞同此点,他说:“《大学》言正心,心以主宰言;其言诚意,意者心之中又有心,意即性之发现。放心亦心也,知孟子本心之说与单言心者自别。良知亦然。本心、良知,即意也。意即性,性无不善,故曰尽性;意无不善,故曰诚意;诚意乃所以正心。”蒙文通认为,心有多种,如宋明儒说的人心、道心、本心、放心等等,而《大学》所说的心是主宰之心,意是本心;这个心、这个意,不仅具有一般心所有的认知意义,而且具有本体性含义;本心、意与性是同一的,都属于本体论范畴。故《大学》言正心、诚意,和阳明所言的良知一样,是兼主宰之心与本体之心于一体,是至善无恶的。
另一方面,蒙文通又主张心性有别。他说:“罗整庵:心之灵而非性之理。说得亦好,二者未可偏废。”罗钦顺,是和王阳明同时的明代著名哲学家,他继承张载以气论心性,在气本论的前提下提出“性为阴阳之理”和“心本于气”的思想。他对心性问题极为重视,曾在其著作《困知记》中称“千万言,紧要是发明心性二字”,他以气本论思想批判佛教以心为空寂、以心为物、以心为性的理论,从而抽掉了佛教心本论的基础。他认为陆九渊、杨简、王阳明的主要错误在于“以知觉为性”,即以主观意识为天地之根本。
罗钦顺在指出心性相互联系的同时,强调两者的区别。他说:“除却心即无性,除却性即无心。”作为阴阳之理的性与本于气的心互相依存,不可或缺。但两者又不同。他又说:“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罗钦顺认为,心、性之别在于:心是人的神明之心,性是人之生理之性,心与性既不可分离,又相互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进而以“人心有觉,道体无为”来概括心与性的区别。另外,罗钦顺还认为,性为体,心之明觉为用,即性体心用,他说:“盖心之所以灵者,以有性焉,不谓性即灵也。”既以性作为心之灵产生的原因和根据,又强调性没有灵明知觉的属性,把性与心区别开来。
蒙文通赞成这种罗钦顺的这种区分,他说:“罗整庵别心之灵与性之理,此语亦精。然二者皆我所自有,不可偏重,如以心之灵为非则未是。”他认为,灵明知觉之心与性之理都为人所固有,不能非此是彼,偏重于任何一方。“三十年不少盐酱,只是改过不吝,何尝是无善无恶,这是性,虚灵不昧的心可说是无善无恶,这是心;这里应有分别。”先天的心、性是至善的,而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故心、性既同又异。
由此可见,蒙文通的思想中,既有心性一元的观点,如“心即性也”,同时也认同罗钦顺的心性有别的思想。在心、性相互联系方面,他说:“尽心然后可以知性,性学不是离了心学。”在心、性有别方面,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心者,知而已;性者,在耳之听,在目之视。心之虚寂,性之条理,只体用之别而已。”蒙文通认为,虚寂之心是本体,条理之性是发用。性是“一往而已”,心是“有所不可”,具有判断能力。主体之心可以认识条理之性,这也是蒙文通心本论在心性问题上的一个体现。
宋明儒中,陆、王等心学家在心性关系上,大都主张心即性,均不讲体用二分。陆象山是以心为本,“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王阳明则继承陆象山,讲本心、良知,把万事万物归本于心,“天下无心外之物”。这与朱子以“心统性情”为纲领的心性论、心兼体用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看来,蒙文通虽然坚持了陆王的心本论宇宙观,而在心性、体用的关系上则与陆王有所区别。
3.心(知)、气(物)合一,心主气从
在心气关系上,蒙文通认为心、气是能所关系,虽为两物,却不可分离,即心气非二,心气合一。他说:“气是形而下之器也,物也。气之流行,只是任其流行,有何过不及。知过不及者,心也,须是心常作主。”心、气为两物,形下之气是物,是任其流行,有清浊、动静之分,而认识之心(知)无清浊、动静之别,但具有知觉灵明功能,对气的过或不及等状况悉能知之。即“气之清者知其为清,其浊者知其为浊,于一身之气亦然。气有清浊,而知不可以清浊言;气有动静,而知不可以动静言;气之中节或否,而知无不知”。心之所以能“知”气的清浊、动静、中节与否的状态,关键在于:“气之秩然天则,即心之本体。”这里的“气之秩然天则”,实际上指的是气中合乎规律的部分,或称作气之理。蒙文通是把气之理等同于心之本体。“朱子说:心者气之精爽,甚好。气本是好的,才有不好,心便知之,亦是气自知之。”蒙文通赞成朱熹对心、气关系的说法,这里的“心”,是从认识论上而言的,是认识之心。其实,气本无所谓好坏,如果真说它“好”的话,只是就其清浊而言,只是就心的判断而言。所以,蒙文通说“气有失处,气自知之”,看似有气灵论的倾向,实则可以理解了。他的“气自知之”,可以认为是气之理,即心的知觉。故心、气是相通的。“心气岂为二耶!”
既然心气非二,那如何才能做到合一呢?蒙文通认为,“敬以直内,须是下刀锯鼎镬一翻工夫,心气乃可合一”。“心气合一,是毫发皆要依他太极。象山所谓刀锯鼎镬学问也”。也就是说,心气合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加强自身修养的过程。北宋的程颐曾说“涵养须用敬”,“敬只是持己之道”。南宋的朱熹继承了这一思想,“主敬涵养”,以敬为立身之本。他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他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贯穿于“未发”和“已发”、知和行的全过程。“敬以直内”常常与“义以方外”相对应,后者是强调对外物、他人的态度。这里,蒙文通用象山所说的“刀锯鼎镬学问”说明时时存心的必要,是“毫发皆要依他太极”,“太极本无极,太极性也,无极心也”。性即心,故本心不能有一丝懈怠。
在心、气关系中,“心气合一,只是要以气从心”。 “须是心常作主”。所以,蒙文通讲心气不二、心气合一,说合一亦有主次之分,要以心帅气,使形下之气(物)从属于形上之心。
在心、物关系上,蒙文通认为,心物合一,物在心中。他说:“无极而太极,莫非本体;用则千变万化,而体则虚明无迹。万物莫非此体,与我虚明之体为一,我之虚明即万物之虚明。”无极、太极,即性,即心,皆是本体。此本体包括了虚明无迹的体和千变万化的用两个方面。此虚明之体是形上,千变万化之用是形下。万物是此体,我亦是此体,故我与万物浑然一体,即我之虚明亦万物之虚明。
(二)关于“理”
蒙文通对“理”这一范畴论述较多,既谈到了对“理”本身的理解,也阐述了与相关范畴的关系,如:理与心、理与气、理与欲,等等。
1.“理”是宇宙本体
蒙文通吸收了程朱的天理论思想,认为“理”是宇宙本体。他说:“未有天地之先,理固已在。”“父母未生前,只是天理,人得天理以生,此外更有何事。”这个先于天地、先于父母的“理”具有绝对性和超验性,是生之本,是宇宙的本原。当然,“理”也指事物的规律和普遍法则。“能运水担柴的是这个,但这个却未运水担柴。”“理”具有形上性。蒙文通依据二程“凡事皆有理”、“万理出于一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思想,说:“一身之理,与天地万物本是一源,此身即万物之一,本在浑然寂然一理之中。”人与万物皆承一源,皆共一理,皆是此共理中的一分子。“内而视听形骸,外而山川草木,皆物也。有物有则,所谓自然规律也,即天理也,太极也;生生不已,乾乾不息。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即应各尽其理。时行物生,任其自然,行所无事,而我不与焉。恻隐羞恶,充周流行,而自不容已,所谓虽欲自异于天地不可得也。”蒙文通指出,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均源于一理。这一理是天理,具有超验性和抽象性及绝对性。同时,各物有其理。此理是物之则,是自然规律。物物各有其自然规律,各有其物理,这物物之理又复通为一理,即天理。此“生生不已,乾乾不息”之天理体现于阴阳五气的交相作用中,体现于运动之中,故“静中存天理,动中循天理,此理本无一息之间”,理是本体性范畴。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发挥其师李侗(李延平)的“理会分殊”观,总结出其著名的“理一万殊”思想。蒙文通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延平所谓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理原自一本而万殊,莫非性也。”作为道南一脉的重要人物,李侗讲:“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他的“理会分殊”观点,是主张激发人的智慧和灵性,以明人伦,察天理,使代表儒家精神的“天理”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即注重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践履。蒙文通认为,这是对“孟子所谓践形尽则,失要于明物察伦用工一翻”的弥补。他说:“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是把真常极致之理从事为中体现出来。”程颢由“理会分殊”体贴出了形上的“天理”,而程颐进一步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主张通过“涵养”“存敬”工夫来认识儒家伦理。